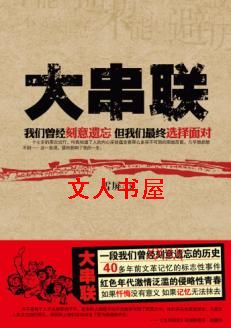红色家族档案-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情地问了我一句:“你爸平时身体好不好?”我说:“有冠心病,但是不严重。”教导员点点头,没再说下去。我也再没问下去,心里一点不祥的预感也没有。
飞机起飞的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点什么。想想前后的事情,多有蹊跷。但是我正处在一个“文革”后的生活上升期,我认为自己应该培养对上升生活中多有变动的习惯,应该有见怪不怪的能力。
一下飞机,我发现来接我的人中有总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我_下明白大事不好!一路上我根本没听清他们都跟我说了什么,只觉得“文革”中都没有塌的天,现在塌下来了。
从1966年3月18日那个血腥的日子起,爸爸就丧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文革”中专案组一直秉承林彪等人意志,贯彻医疗服从专案的原则,爸爸的伤腿一次再次地失掉了治疗的机会。
爸爸在狱中写的政治自传中,有关于这些可怕日子的回忆:
约在(1967年)4月底又通知我写政治自传。我写了。自传写好后,就不断将我从医院中拿出去斗,也不断有审讯。直到9月,将我从医院拿出去一连斗了几天。晚上住的地方蚊子奇多,又不给挂蚊帐,睡不了觉,实在是疲惫不堪。一天晚上通知我回医院,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去休息两天。谁知回到医院第二天就发高烧,重感冒。晚上起来小便时头晕脚软,重重地跌了一跤。看守人员将我拉起来,我觉得脚很痛。第二天医生来搬了两下腿,说没有关系。我说有些痛。医生说跌痛了热敷几天就会好,骨头没有坏。再一天,我的热退了。医生下午还来试了一次表,证明已经没有发烧,于是看守人员就来通知我出院。我想原说把我的脚治好,现在我的脚并没有治好,而且重感冒,腿还在痛。我在医院名义上住了五个月,但有近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住在院外。有一次开刀后不到一个星期,线都未拆,就拿我出去斗。当时我要求至少要拆了线。看守高声说,医生讲可以,你说那些干啥?我又说,这太残酷。看守自然更不满意,又大声吼叫了一通。
出院后又审问,叫我交代历史问题,要我写书面材料。我即写了,除了说明我的认识外,我申明我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交代。
出院后我的腿大痛起来,一动作特别是上下汽车时痛得忍不住,晚上痛得睡不着觉。不仅不能向左侧卧,也不能仰卧,只能勉强向右躺,整个晚上连翻身也不行。去厕所也成了问题。我自己买了一个热水袋,每天热敷几次,皮肤都烫黑了,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以后队土的医生要我自买了一些四环素吃,说吃了就好了。我买了60粒,吃了十天,仍然无效。不久发现腿肿了,送我到附近一个部队的医院去拍了几张爱克斯光片子,大概就发现了是骨折。
11月中旬或下旬,又送我上301医院,一检查是严重的骨折。两个医生似乎还发生了点争论。一个说上次出院时检查可能马虎了。一个说,上次确未发现。告诉我:先要减少疼痛,而且避免接骨开刀采取牵引治疗。他们把我放在一个特制的床上,把腿牵了起来,脚上吊着一块几公斤的铁砣,而且要逐渐加重。因此左腿上的伤口又肿又痛。有时忍不住打一针止痛针。腿牵引起来后,实际上已将人固定在床上,除睡觉外只能用两床被子垫着背坐着。说是要牵引十来个星期再看要不要开刀接骨。可是只牵引了一个星期又把我解下来出去开斗争会。当天晚上送我回医院,可医生几天不来,后来来了,也不讲任何话,不检查,又把腿吊起来了事。
就在这个时候,又要我交代问题,写检查。并警告我说,是时候了,不能再丧失机会,如不采取主动,后果自负。但是当时我只能说真的,不管怎样,我也不能乱说。因此审讯过程相当紧张,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我受了相当大的折磨。这种审问,整天都干。有时要我写材料,早上要,晚上就得写好。一直继续到1968年2月,中间除过年,过春节外很少停过。
1968年2月上旬,医生来将我的牵引架子拆了,对骨折的左腿未再做任何处理。第四天看守又来通知我出院。医生则拿来了几包灰锰氧要我自己洗伤口。我说骨折你们还未治疗,至少应该再检查一下,回答是:以后再说。
原来让我出院还是因为要审讯,要交代“重大历史问题”,并说有人已经检举你了,逃不掉了。并说我在铁的证据面前仍然顽抗到底。我当时表示,我的腿并没有好就把我从医院里赶出来,我没有的我绝不承认,绝不乱说。这个审问有个把月,也是整天干,有时夜晚还干,并几次对我说,你逃得了上午,逃不了下午,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白天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夜战。这个场面你觉得不过瘾,我们还可以加大场面……
就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腿仍然痛得不行。脚的伤口也经常流脓、流水。因此我写了一个报告请求再给我治治脚上的伤口和大腿的骨折,我并请求伤口如果治不好,就把腿锯掉。但我想,如果要治是不会治不好的。
1968年7月的一个下午,审问完我以后通知我说:“毛主席亲自批准你再去住医院。”
第三次住院后又在那里接着审问,情况相当紧张,审问的人很多,有时多达十几人。
7月25日,301医院的有关人员作出了手术方案并写了报告。专案组将报告在8月初呈递给林彪、江青、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等人。8月4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罗瑞卿的动手术的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说,罗瑞卿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搞到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你立即告专案组,动手术的问题推迟到秋凉以后。”吴法宪说:“可是罗瑞卿的手术问题,江青、陈伯达和黄永胜已经同意了啊。”叶群说:“我负责把林彪的意见告江青、陈伯达和黄永胜,你负责告专案组。手术推迟至秋凉以后。”
8月7日,专案组重写的报告上说:“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手术在秋凉以后并没有进行,而是拖到了1969年初。1月25日深夜,在没有进行术前讨论的情况下,参加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又临时换人:以致这些医务人员连病人都没有见过。这次手术截去了爸爸左腿小腿的下三分之一部分。五周以后又将爸爸在医院里跌断的股骨头摘除,使得剩下的残肢失去了和身体的骨性连接,在以后的日子里,连安装假肢都十分困难。而且,这条腿最终成了爸爸无法跨过的死亡线。
爸爸重新工作不久就听医生说可以通过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这样他的左腿功能可以得到很大改善。但是这种手术对于爸爸这样已经70多岁的人来说风险很大。而且当时国内对这种手术还比较陌生,技术不成熟。在我们的劝说之下,爸爸暂不再提。后来,组织上请了两位德国专家来给爸爸安装一个更好、更轻一点假肢的时候,爸爸又旧话重提,得知德国二战后由于战争残疾人很多,这种手术开展得多,所以技术水平较高。两位专家也表示,如果能够施行这个手术,会使爸爸的左腿功能改善很多。
我一直认为,爸爸是个崇尚现代生活的人,他习惯的逻辑方法始终是严格的因果相袭,这导致他太信赖科技手段。否则,他不会在72岁高龄上,把自己的健康希望托付给现代医学,相信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同时,他又是一个稍显陈旧的、至死不渝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健全的自己才是供奉给理想的最好牺牲。不过促使爸爸下定最后决心的还是另外一件在我不在家里的时候发生的大事。
1978年春天,妈妈在例行的健康体检中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连续观察的结果,那个影子长得很快。结合她原来有乳腺癌的病史,医生们的估计是很不乐观的。妈妈关心的事情是先别让爸爸知道。但是那几天,爸爸一开完会就上医院来看妈妈,来了话就特别多,也特别温存。妈妈一下明白爸爸是知道了。他对妈妈说:“动手术,不要犹豫,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医生说动手术才能诊断明确,而且良性的可能性很大。”实际上爸爸心里也没有把握,他对哥哥姐姐们说:“妈妈肺上长了东西要动手术,如果是恶性的,医生说最多还能活五年,这样的话,就是老天太不公啊……”爸爸说这话的时候老泪纵横。
在爸爸的鼓励下,妈妈鼓起了勇气。3月8日这一天,妈妈先去参加了“三八”妇女招待会,然后带上两个第三代,坚坚和毅毅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玩了一个下午。妈妈说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她的心里觉着挺平静。回到家里,她把我们所有人住的房间都看了一遍,就坐上汽车回医院去了。
手术后证实病变是恶性的。哥哥姐姐们认为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不能告诉精神已经处在极度紧张中的爸爸。但是爸爸自然还是知道了一切。是一个去医院看望他的老同志,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说走了嘴。
那位同志离去之后,爸爸和衣倒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说也不动。他要在场的哥哥嫂子回家,他要一个人静一静。哥嫂刚到家,电话铃响起来。原来是警卫员小王发现爸爸在他俩离开之后一直坐在床边垂泪。小王不敢问,又怕出事,所以要哥嫂赶快再去。两人扔下饭碗又往医院跑。当他们气喘吁吁爬上六楼,推开爸爸房门的时候,他们却看到了一幅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情景。
爸爸已经穿好衣服,洗好脸,正坐在桌边吃饭。他神态镇定,和他们离去时已经判若两人。爸爸对哥嫂说:“我不能这个样子,我已经想好,我要出国去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还有多少时间,我要照顾她,要让她过得愉快轻松。”
哥嫂说,爸爸出国治腿的决心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下定的。
妈妈渐渐好起来,在那一段非常痛苦的治疗中妈妈表现得非常勇敢和有耐心。301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公认妈妈是一个最配合治疗的病人。爸爸则积极作着出国治疗的准备,他请有关的同志帮他调查情况,搜集资料,他还向中央写了报告。组织上派了专门的技术小组研究和考察有关问题。在爸爸的积极努力下,事情很快决定下来。
妈妈回忆说:“6月里的一天,我刚刚出院不久,瑞卿就告诉我,出国治腿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而且心里想,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好好跟我商量?前几天提到的时候他还说没有定,也许拖一拖。记得为了这个我还和他吵了几句,可是吵有什么用呢?我知道他定下来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再说,我也习惯了在这种时候听他的。”
这样,1978年7月15日,大病初愈的妈妈跟随急切的、对自己充满美好信心的爸爸离开了北京,飞往那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妈妈并不知道爸爸这个巨大的决心里饱含着对她的深长情意。7月31日,爸爸给在北京的儿女们写信: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动手术了。根据观察可能如愿以偿。虽然要冒一点风险,但大致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们放心。这里的我国大使及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的阶级情谊实在使人感动。……
妈妈写:
今天我从大使馆到医院看爸爸(200多公里,汽车走2点30分)。要他写几个字给你们。他一写就是一大篇。爸爸现在一切情况都正常。有的比在国内还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里少,也容易些。可能与这里气候好有关系。医生经过各方面检查后说,比他们原来想的要好。2日决定动手术。爸爸和妈妈都有信心。因为教授、医生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但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治好。大使馆的同志都对我们很好,你们也放心好了。1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住几天,这样看护爸爸方便些。等动完手术后妈妈再写信给你们……。在外面的爸爸妈妈很想念你们。祝愿你们工作学习得更好,身体健康!等爸爸动完手术后身体更健康,咱们全家就可以更努力、更多地、更愉快地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8月1日妈妈和张彤大使到医院去看爸爸。妈妈带了一把鲜花。她和爸爸在病房里照了一张相。爸爸情绪很好。妈妈一直待到很晚,爸爸催了几次,妈妈仍然舍不得离开。最后爸爸说:“走吧走吧,我已经吃了睡前药,明天还要做手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妈妈说她永远忘不了,爸爸那样笑眯眯地跟她摆摆手,她觉得爸爸心里平静极了,有信心极了。她就比较放心地回到旅馆里去了。这一去,竞成永诀!
第二天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