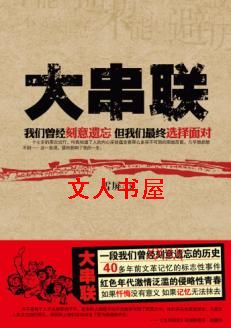红色家族档案-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见客人等等。但是当我们到达福州,见到这些叔叔的时候,从他们的眼神和搀扶爸爸的姿态里,我们看到了战友重逢之后的欣喜和对一个历经磨难仍能保持本色的老战士的崇敬。这种感情自然超越了任何规定的限制。在他们的安排下,爸爸有了一个愉快舒适的休养环境,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身心得到了一次彻底的休息。
这是一段十分美好,令我永世难忘的时光。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认识和观察爸爸,这在我们父女的共同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些日子里,我会常常觉得爸爸离我十分遥远。六年的隔绝造成了一段空白,六年的苦难成为爸爸和所有人之间的一个鸿沟。面对这个身心疲惫的老人,我不得不小心翼翼,百倍经心,生怕在无意之中触动了他内心深处那些巨大伤痛。但是这种状态很快过去了。在那个静谧的,被高大的玉兰树和木棉树遮掩的院子里,在福州汤井巷一号那清香、润湿的空气里,在那些被翠绿的竹林环抱的池塘边,在那些青苔和落叶盖满的石子小路上,我们的心很快都舒展开来。
爸妈和我三个人在那个很大很深的院落里一点也不感到寂寞。我甚至幻想和希望我们会从此被世人遗忘。我们每日早起的互相问候,白昼里无休无止的谈话,晚间依依不舍的道别都充满了那么柔美的含义:深长的爱护、周到的体贴。我原来以为只有陷在热恋中的情人才会如此行事。
一天下午,我在离爸爸窗下不远处闲坐。透过一扇半开玻璃窗的折射,我看到他在房中读报。大约因“文革”耽误了浪漫年华,所以信不信由你,反正那天已经二十有四的我,手里不仅真的拿了一把吉他,而且曼声弹唱,做小女子状。我弹着,唱着,忽然有些不能专注,一抬头,看见爸爸已把报纸放在一边,他的眼睛望着我该在的地方(因为他实际上是无法看到我的),脸上是一副被感动的神情。我弹了许久,也唱了许久,爸爸也就那样子坐了许久,听了许久,一直到夕阳西下。我在心里祈祷时间就此停止,就此停止,让我和爸爸永远停留在这飘逸空灵的一刻吧。我忽然想到,世界上有一种或者很多种我们原来根本不知道或者不理解的美好生活方式,崇尚恬淡、亲情,崇尚内心的平静和与世无争。我怀疑在那一刻,又是我出生时睡过的那个怪箱子在作祟,在操演它的人生在世的幸福极致了。但我知道,这种东西离我们,至少是离爸爸太遥远,我们永远不可能到达那种境界。
爸爸治腿是一件太艰苦的事情。一开始,医生们也没有什么信心。但老爸却满怀希望,并且认真投入,按时治疗,按时服药,对任何医嘱都执行得不打一点折扣,最累人的是要按时锻炼。建国以后,因为毛泽东的工作习惯,爸爸他们这些人都成了晚睡晚起的人。但那段时间,爸爸是我们院子里起得最早的人。我每天都在爸爸练走的声音中醒来,那双拐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声音在我的梦中是柔和而不带有任何血腥气的。院子太大了,打扫起来很困难,很多小路上都长满了草,但爸爸每天练走的路上却寸草不生。看爸爸这样,我经常感到害怕,万一治疗不成功怎么得了!
不过后来我放心了。爸爸越走越好。先是妈妈看出来,后来我看出来,医生们也终于看出来了,因为他们的预言也不像以前那样含糊其辞,这种药物的疗效和这种锻炼方法的好处也被他们总结归纳得十分充分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雨后天晴、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妈妈一左一右陪着爸爸在院子里练走。忽然爸爸停下脚步,对我们说:“今天我要试一试。”我们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见他先把腋下的一只拐杖递给我,又把另一只递给妈妈。我们因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而大惊失色,我看见妈妈抢上去要扶他。就在这时候,爸爸满脸带着笑,清清楚楚地对我和妈妈说:“我站起来了。”我和妈妈都呆住了。待我醒过神儿来,赶紧飞身上楼,把妈妈那架老式德国120相机取来,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一直被我珍藏。至今我仍觉得这张照片上盛满爸爸的欢乐。他气韵生动地站在那里,只要屏息静听,我就听见他高兴地说:“我站起来了。”
在这一段时光里,我亲眼见到我的双亲天天相依相伴,充分享受劫后余生中的生命阳光。妈妈在秦城监狱里因乳腺癌做过一次大手术。出狱后,她曾想对爸爸隐瞒真情。但天天生活在一起,又经常去医院,又要做治疗,怎么瞒得了呢。她终于说出了真情。妈妈从未见过爸爸这样伤心,就是在上海会议期间,爸爸最痛苦的时候,也只是泪流满面。这一次,爸爸是嚎啕痛哭了。爸爸太知道在专案组手里,妈妈得了那么重的病,动了那么大的手术,要忍受多少心灵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而且他总在心里觉得,妈妈坐监狱是因受了他的牵连之故。我由此想到,被爸爸爱是太幸福了。我也由此决心按照这种专一郑重的程度寻找我的爱情。至于找没找到,容我后表。
这时候,虽然爸爸的日常起居已经有了一位姓孙的警卫员同志照顾,但妈妈总想为他多料理一些生活上的事。爸爸总不肯让她动手,觉得她是一个更需要照顾的病人。我还听见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互相询问:昨晚睡得怎样?怎么了?为何这餐吃得这样少?妈妈去折一朵树上的花,爸爸就心惊胆战地叮嘱:“看闪了腰,看扎了眼睛。”妈妈出去回来稍晚,爸爸就会坐立不安。
这些日子里,除了与我们相处,爸爸最高兴的就是皮定均、李志民、廖志高等老同志来访。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当我看见他们一次又一次在手掌上划三点水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又在谈江青那伙人了。有一次,我听到皮叔叔对爸爸说:“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不幸的是,皮叔叔在1976年的一次意外的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这时候,离“四人帮”倒台只有几个月了。爸爸和我们都对皮叔叔的突然离去感到万分痛惜。我忘不了爸爸在皮司令员的灵堂里悲凄的面色。记得我当时因此产生了一种幻觉,完全不像在和平时期告别早逝的长辈,倒像在战场上告别牺牲的战友。爸爸长久地抚摸着覆盖在皮司令员骨灰盒上的党旗不肯离去。我觉得自己是在那一刻懂得了什么叫做战友情。现在皮司令员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每年清明,当我们走进骨灰堂一室时,我们就看见,皮司令员和爸爸一起在向我们微笑。我们要将两束一样的花放在他们面前。如果在我们之前已经有相同的鲜花放在那里了,我们就知道,一定是皮叔叔的夫人或者女儿来过了。
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爸爸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在向毛泽东的遗体告别时,他坚持让人搀扶着,用他刚刚能够站立的双腿走过毛泽东的灵柩。他久久端详这个巨人的遗容,泣不成声。9月18日,毛泽东的葬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爸爸又在那里伤心欲绝地站立了一个多小时。爸爸后来在担任了军委秘书长之后,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还担任了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无论在这个以革命为主题的世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对毛泽东的信任和爱戴从未动摇过,他始终是这个伟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
不久,我们的好日子结束了。我又一次悲观地想到:这种日子本来就不是为我们准备的。
29。仅仅一年
他们进入幸福境地,天上或人间,去过远为幸福的日子……
——《失乐园》463页
1976年,中国人失去的不止是毛泽东。这个旧历龙年,带走了对中国革命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人: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人的集中逝世,使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来得及给它划上句号。他做到的只是使他身后发生的事情又一次具有绝对的戏剧性。
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垮台了。至此,毛泽东在“文革”中依靠和扶植起来的两股政治力量,以林彪为代表的军人集团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文人集团都以失败而告终。邓小平在妥善地替代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之后,成为这份革命遗产的继承人。
爸爸作为被邓小平信任的军队元老,回到军队任职。
1977年8月里的一天,妈妈从报纸上得知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但是去参加会议的爸爸却久久不见回来。妈妈放心不下,就打电话给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爸爸。爸爸在电话里对妈妈说:“治平,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急。事情办完后我就会回去。”
这时候,我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读书。我从广播里知道爸爸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消息。当时我的一位同学一定是见到我有些迷惑,就言简意赅、直入主题地提醒我说:“你爸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我们都以为,爸爸生命中新的一页开始了,我们都没想到,仅仅一年以后,爸爸就离开人世。命运在我们最没有警惕性的时候,跟我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那天我在课堂上就有点坐立不安,我正在为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走神。这件事情是两年以前发生的。
我入学后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但支部说,我应该先入团,再入党。我说我已经25岁,是不是可以不入团,要是符合条件就直接入党吧。回答是还是先入团的好,于是我就耐心而认真地争取先入了团,又交了入党申请书,按照支部书记教导员“和平时期只能小处见精神”的指示,每天坚持打水扫地,每周坚持帮厨并把上街休假的名额尽量让给别人。但教导员的嘱托很快不够用了,因为其时正是1976年的二三月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高潮。据历史材料记载,1976年3月26日,由江青提议,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史无前例地邀请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列席,面对面批判邓小平。列席人员指责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说他“大搞物质刺激,鼓吹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据说,邓小平一直闭目静坐。①
支部和政治局一样要开批判会。显见着我光小处见不了精神,非大处见精神不可了。我拿不定主意,给爸妈写了封信,说自己如果不发言好像过不了关,入党希望就会渺茫,像“文革”前入团的事一样,一拖就是十年。信发出我才发觉,根本等不到爸妈的回信到,我们的批判会就要召开了。我终于决定不放过这次机会,决定像毛泽东一样做一次“违心”的事。奇怪的是从准备批判稿子开始,我就莫名其妙地深陷于角色其中不能自拔。我记得自己先激情满怀地在图书馆内查阅报纸,把“梁效”、“方炬”等人的文章都翻了个遍,然后在自习教室里奋笔疾书。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我完稿的时候,我把钢笔很快意地一丢,很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列宁签署攻打冬宫的命令的姿势。批判会上,我上台发言,听着自己清晰嘹亮的声音在众人头上盘旋,对自己发言的效果毫不怀疑。果然,会后大家公认我的批判稿逻辑缜密,说理服人。散会的时候我听见不止一个人说:“还得数人家一中队的小罗……”这个发言并没有使支部马上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但我相信一定使我在发展对象的名单上提前了不少。两年后我之所以又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上《神经精神疾病学》的时候提到了双重人格,我正在比较我和毛泽东两人的双重人格倾向谁更严重。而且,因为后来邓小平的复出,又因为爸爸因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当上了军委秘书长,我对自己两年前的举动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虽然听说邓小平曾经和毛泽东说过永不翻案的话,说明他也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做的事情就是光彩的。
下课不久,有人叫我到中队办公室去,队长、教导员和副队长都在。他们说:“已经给你买好了回北京的飞机票,明天一早派车送你上机场。”我想起来爸爸曾说过要出国安装假肢的事情,是不是这次想让我回去商量商量?还是已经决定走,反正马上要放暑假了,要我回去送他。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记得教导员还满怀同情地问了我一句:“你爸平时身体好不好?”我说:“有冠心病,但是不严重。”教导员点点头,没再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