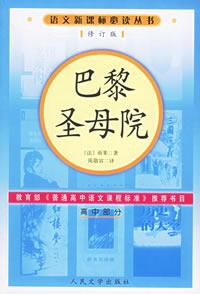作者:[日]川上弘美译者:施小炜 张乐风----------------------------月亮和电池(1)----------------------------正式的称谓应该是松本春纲老师,然而,我却管他叫“老师”。既非“先生”,亦非“夫子”,而是“老师”。在高中,老师教过我国文。然而他既未曾担任过我的班主任,我也不曾特别热心地听过国文课,所以老师并没有留给我太深刻的印象。毕业以后也许久没有再相遇。自从数年前在车站前的一家小酒馆里与老师比邻而坐以来,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老师有了过从往来。老师腰板挺得笔直,几乎呈反弓型,端坐在柜台前的座位上。“金枪鱼纳豆。甜辣藕丝。盐水茭头。”在柜台前尚未坐定,我便张口点起菜来。几乎是同时,邻座一位腰板笔直的老人也开口点菜道∶...
作者:陈昌平一在王喜贵王师傅眼里,小儿子王爱娇就是一个废物。王师傅祖籍山东,世代务农。至少可以追溯到爷爷的爷爷,老王家便人丁兴旺,而且全部是兄妹六个——五个男的一个女的,老幺是个女的——小棉袄。至少从那时候开始,王家的男人和媳妇就像一台性能优异的机器,五男一女的生育传统和性别格局便一直延续下来。即便是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年代,王家的祖先依然顽强而又幸运地保持着这一匪夷所思的传统。到了王师傅这一代,自然还是兄妹六个,五男一女,老幺依然是个女的——小棉袄。这当然是一个奇迹,而且王师傅没有理由和借口破坏这一传统。王师傅排行老大,是兄弟里第一个成家立业的,而且赶上了突飞猛进蒸蒸日上的新社会,所以王师傅结婚时就铆足了劲儿,把机器调理得齿轮飞转马达轰鸣——他要给兄弟们做个榜样。...
从西安回来,我把这个故事讲个别人。别人都于我有同感,很愤怒。可是文章写到这时,我的疑问出来了:管理局禁止老头吹笛好像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老头确有卖艺之嫌。否则,他至少应该让一让再收那20元钱,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收钱;第二,怎么一切都像排练好似的,有惊无险,显然老头充分利用了我们这样游客的猎奇心,同情心和“正义感”;第三,老头好像很怕管理人员,其实他不怕,如果真怕就不会带笛子来,更不会在管理员眼皮底下吹。他原来同管理员玩得是痞子游击战——我反正身无长物,不怕罚,不怕抓。 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是卖艺,有何不可?管理局可以收管理费,老头可以增加收入,游人可以娱乐,皆大欢喜。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此,卖艺这别处可以,在华山不行,因为华山只有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大部分窄的只能勉强通过两人。因此,在游人如织的华山上,如果出现堵塞,是很危险的,华山管理局不让卖艺的这条规定是...
作者:常山居第一章 天灾人祸第一章天灾人祸一九六一年春天比前年春天风少、比去年春天暖和、比往年春天下的雨多。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下,大地上的草儿猛地往上窜。田野的杨柳吸吮几场雨水,吐出了嫩芽、长出了嫩叶。几天过后,那绿绿的树叶被饥肠难奈的人们采摘了个精光,一棵棵树变成光秃秃的树桩。这几年人们过的太艰难了:谷糠、草籽、树叶都变成添饱肚皮的食物。社员说,五八年,风调雨顺,地里丰收,社员没多收;五九年天干地旱,大地欠收,社员没收;六零年,天灾人祸,社员缺吃少花生活更加困苦。……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二十七斤粗细搭配的口粮。社员没有供应。生产队收成好,提留口粮自然就多。生产队欠收,在必须保证统购粮条件下,剩下多少吃多少。然而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只有极少数生产队能够保证社员有充足的生活口粮。而大多数社员只能忍饥挨饿。社员每天下地干活,食不果腹,缺少营养,各种疾病便乘虚而来。五十岁...
一、市长与平民没什么两样 记得2000年在OSU,布什和戈尔都去OSU演讲争取选票。我当时开 车从住处去学校,在快到学校的趴车场的时候,有俩个警察提示我停下车。我停 下观望,只见四辆黑色轿车开了过去,随后俩个警察开摩托走了。一会经过学校 礼堂,才知道布什同志在里面演讲,刚看见的四辆黑色轿车就停在外面。当时我 就想这种不扰民的举动在中国肯定是做不到,一般就要几条街戒严了。2001 年圣诞节张惠妹到硅谷开演唱会,我当然不错过跑去观看。演出还请了SANJ OSE(硅谷的英文城市名)市市长,演出快结束时,张惠妹请市长上台,台上 还有很多观众,市长很自然的就和观众一起跟随张惠妹的歌声又唱又跳。那首歌...
三弟是六岁的时候父亲从临县领回来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很大的眼睛,细细的胳膊,表情怯生生的。怀里抱着一个两尺见方的硕大粗瓷储蓄罐,形状是一只丑陋的猪。 小妹呱呱落地那会儿,我们家凑足了三朵金花。母亲被拉去做了结扎手术后回来就偷偷哭了,她在房里抽噎着对父亲说:“算命的都说你命里注定没有儿子,你还要我生!生那么多娃你养得起吗?” 父亲是个硬汉子,他说家里没有哪代缺过儿子,他不信命,母亲不能再生了他就大老远地跑去找,那年月收养手续不是那么繁杂,花了不多的钱,父亲就有了儿子。父亲抱着三弟喜滋滋的,塞一个大苹果在他手里。 苹果在那时是多稀罕的水果啊,父亲就买了一个!我和大姐冷眼旁观,都觉得这个小杂种是个大威胁,他以后还说不准要跟我们争多少东西呢!...
作者:淡出九峰1生活往往从笑开始变化的,项自链朗朗的笑声过后,他的命运就悄然发生了巨变,这些都始料不及。老婆吴春蕊在房里听到了他久违的笑声,就连忙跑出来开了门,一双眼惊奇地盯着项自链。尽管她的脸上依然挂着八年来惯有的迷人的笑意,项自链还是看出她目光里游荡着的不安和惊讶。项自链平时很少这样独自放声大笑,离家还有百来米路,笑声就破门而入了,带着一股久违的信息。这股信息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在他大学毕业的第四年悄然来到了他的身边,自己都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当了副县长。那年他二十九岁,刚谈上三个月恋爱。当他带着难以自抑的兴奋,想告诉恋人吴春蕊的时候,项自链也象今天一样远远就独自笑开了。当时吴春蕊以为他疯了,她从来没有听过项自链如此狂放的笑声。吴春蕊远远就从单身宿舍里跑出来,直嚷嚷地问他是不是中邪了,要他注意影响,整个校园都让他的笑声喧闹着。项自链还是止不...
作者:(清)刘鹗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莱山。山上有个阁子,名叫蓬莱阁。这阁造得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十分壮丽。西面看城中人户,烟雨万家;东面看海上波涛,峥嵘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挈酒,在阁中住宿,准备次日天来明时,看海中出日。习以为常,这且不表。却说那年有个游客,名叫老残。此人原姓铁,单名一个英字,号补残。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这“残”字做号。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残。不知不觉,这“老残”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原是江南人氏。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所以学也来曾进得一个,教书没人要他,学生意又嫌岁数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拙,不会要钱,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你想,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
《这个特工不杀人I》目录上篇 责任始自梦中 绝地沙漠非常研究 第1章 东方邂逅 (概念女孩 老人 精神 读精神) 第2章 非常任务 (楼兰城下 神秘征用) 第3章 东方邂逅 (互相需要 分工合作 精神的温度) 第4章 非常任务 (I*总部 特殊材料研究组织) 第5章 东方邂逅 (白天的我 接到私侦任务) 第6章 非常任务 (接受使命 准备进入角色) 第7章 东方邂逅 (古姐的猜测 关于概念女孩 杨槐) 第8章 非常任务 (关于胡博士一家 进驻沙漠孤舟) 第9章 东方邂逅 (我的准初恋 关于老人 *神的海蜇) 第10章 非常任务 (孤舟被劫 胡博士消失) 第11章 东方邂逅 (古姐背上的十字架1)...
作者:[法]雨果第 一 卷 一 大 厅距今天348年六个月一十九天,巴黎老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廓里,一大早群钟便敲得震天价响,弄醒了全市居民.可是,1482年1月6日,这一天并非是一个在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一清早便使群钟轰鸣.万民齐动的事情,也是无关紧要,不足记取.既不是庇卡底人或是勃艮第人来攻城,也不是抬着圣物盒的巡列仪,也不是拉阿斯葡萄园的学子起来造反,也不是我们称之为无比威赫之主国王陛下进城,甚至也不是在巴黎司法广场对男女扒手们进行赏心悦目的绞刑,更不是十五世纪司空见惯的身著奇装异服,头饰羽冠的某外国使者,突然而至.最后一支这样的人马,弗朗德勒御使们,抵达巴黎还不到两天,他们是前来为法兰西王储和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缔结婚约的.这叫波旁红衣主教大人伤透脑筋,可为了取悦国王,只好对这群吵吵闹闹.土里土气的弗朗德勒市长们笑脸相迎,而且还在他的波旁府邸里招待他们观看许多精彩的寓意剧.傻剧和闹剧.不料府邸...
作者:[美]本·梅斯里茨第一部分 第1节:性是生理需要空气潮湿闷热,混杂着烟蒂、酒精、廉价香水和死鱼的恶臭。小巷很窄,两侧都是四层楼房,窗户发黑,门窗都装着铁栅栏。人行道的地面裂开了缝,破牛奶箱和皱巴巴的旧杂志扔得到处都是,地上星星点点的水坑反射着屋顶霓虹灯招牌的光芒。在这多得数不清的水坑中间穿行时,约翰·马尔科姆不停地暗自咒骂着。他脚上的古孜牌皮鞋已经黯淡了几分,估计再过一会儿差不多就该报废了。他躬着背,低下头,尽可能走得快一些。其实他巴不得跑起来,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到。头顶上不知哪里有人在大声喊叫,不过说的不是英语。尽管马尔科姆在这里已经待了5年了,但除了英语,他别的什么语言都没学会。...
做销售离当老总,还有多远?(1)十二年前,那是1993年的1月,在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食堂的小包间里,吃饭用的圆桌旁围坐了至少六、七个人,我孤零零地坐在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那时我已经做完了硕士论文,跑出来找工作,面试我的是联想集团的一些负责人。 我至今只记得我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其他的已经因年代久远而模糊不清了。由人事部的负责人开门见山问的头一个也就是我惟一记得的那个问题:“你是清华的硕士,怎么想到要来做销售?”他脑子里似乎替我想了很多其他的出路,怎么不出国?怎么不接着读博士?怎么不留在清华教书?怎么不去研究所做技术研发?怎么不找个机关呆着? 我当时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的确知道的不多,我说:“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各种各样的人。”...
我很少欣赏一个人。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数是活泼,可爱的人,20岁是一个花季中的美丽年龄,可我觉得我的心好像是28岁,28岁这个年龄,人好像老练了许多,就是内心还有太多狂热,表面上也是淡淡的,仿佛已历经沦海桑田一样。所以再看见同龄人崇拜谁就觉得挺可笑,即使真喜欢谁欣赏谁也要绷着脸,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有一个人让我改变了这种想法。 她是一个40岁的女人。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十多岁的孩子,过得有有滋有味。我的好友和她是邻居。她们住的是平房,小城中平房已经不多了,好友马上也要搬到楼房去住了。在她准备搬家的那段日子,我认识了这个女人。 她的丈夫在三年前抛弃了她。这个年月被丈夫抛弃不是什么鲜新事了,她丈夫找了一个小姐,然后跟她离了婚,就这么简单。我们这个小城中这样的事情实在不算什么新闻了,这种事情仿佛太多了。大多数的女人在离婚后都会萎靡不振、哭哭啼啼,继而成为众人可怜的秦...
作者:陆萍情爱黑洞(一)死囚监房。大难临头之际的求生本能,是这样生动地跳荡在黎吻雪那黑森森的瞳仁之中。人性中的许多密码,或许就藏匿在灵魂中的某个黑三角里。当今某些男人的骨子里,已把性欲与爱欲下意识地当作两种敌对的东西,他们尽可能地麻痹自己的感觉,抽逃激情;即借着性的简单的宣泄,来摆脱爱欲的涉入所可能产生的焦虑。死是痛苦的,然而还有比死更为痛苦的东西,那就是等死。——摘自死囚遗笔尽管黎吻雪心中积郁着太多的委屈、太多的哀怨、太多的不平以及太突然的冲动,但是这一切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一场惨案的理由。这是一个隐秘凄绝罪恶而又真实发生着的故事,在生活的地下长河里缓缓流淌。十度春夏秋冬之后,在一个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又必然的时刻——1995年3月8日深夜十二点,故事遽然停格!几乎所有上海观众的目光,都被电视台节目里播出的镜头:"一只包"所惊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