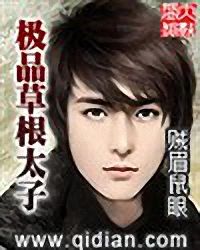草根家事-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考上了上一级学校。而高中呢?我搁浅了,永远的搁浅了!
到了高中,我像一叶扁舟,在风口浪尖上行驶,随时都会倾覆。我的夙愿,也像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都会被巨浪吞噬,最终不还是沉没了吗?这就是我对初中与高中的印象,就是最实在的评价!但是,我留恋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没有他们,我不但“沉没”海底,恐怕我的灵魂也要彻底地沉默了,还会有我现在的“流水人生”吗?(这个纪实文学的题目曾经定位‘流水人生’)。我所以又漂浮上岸,是我高中的同学们,分担了我这首破船被潜流抽打的痛苦,是他们竭力地把我拉起,拽出水面,有抚平伤痕蹒跚上路,不是升学的另一条人生之路。
高二上学期,我就被学校列入“个别生”的黑名单,并在全校生活会上“公审示众”,当时我的心就凉了。试想,有哪个大学愿意要一个个别生入学啊?我不知所措,茫然若失。同桌的程德昌对我的境遇很同情也很着急。他劝我从此往后好好地表现,多在学习上下功夫,学校和班主任对你的印象是会改变的。
对此,我半信半疑。信,他的话有些道理,这也是我的强项,办得到。不信,也有道理,可我怎么好好地表现啊,得付出多大的牺牲才算得上好好地表现啊?我曾幻想过:我能想刘文学那样多好啊,被地主份子杀死了,成了英雄。最好是我能杀死一个反革命,做活着的英雄更好!但这可能吗?思来想去,还是信他的了,只有信,才有一丝希望和可能,才有出路。但是,在信与不信的折磨中,我总是消沉掺和着彷徨。越是彷徨的心态,程德昌越是对我体贴关心,我们就越是密切了。
不想,我们的关系被“激进”的老师发现了,他偷偷找到程德昌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和严肃的指教:你怎么和他形影不离呢?难道你也想当个个别生吗?为了拆散我们的关系,老师把我们的座位分开了。
我好悲哀,我成了什么人了?不可救药的阶级敌人了!
为了不影响他,我们的来往少了,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学习,这都是程德昌的话让我在无望中坚持读完高中的三年学业,没有让光阴白白地流逝。“好好学习”我做到了,但这不叫“天天向上”。最后,我还是在老师毕业鉴定的阴沟里翻了船。唉,三十六计走为上,走上山下乡这条不容我不去选择的道路。
一个学习上的尖子生,一心想升学的人,突然放弃了自己的意愿,所有的同学无不为之震惊,也让刘文孝老师瞠目结舌,因为他分明在我的毕业鉴定中写道:“对参加农业生产没认识”的定论。他也挨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以我最大的牺牲,出了我一口怨气。但是,好多同学怎么也理解不了,想不通我会这么做。他们替我惋惜,甚至是叹息。对于我的“革命行动”,他们是不敢直言相劝的,也怕落个“打击进步”的罪名,落个救人不成自己反到也掉进万丈深渊里。然而,一些胆大包天的学友,还是想方设法要把我拉回高考复习的轨道上来。赵鸿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赵鸿德,是我的老乡,新安堡村人。小学时我们就认识了,但我们不是同班的同学。初中的时候,我是3年2班的,他和郭志彪是3年4班的,是梁文富老师的学生。到了高中,我们有幸分配到了一个班级,3年2班。听说我要上山下乡了,便直截了当地问我:“我的意见还是试一试吧,万一……”没等他说完话,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的心已经死了,你劝我也没有用,我在农村干一年,等有个好鉴定在考吧。”
他不再劝我了,同意了我的“曲线升学”的战略。学校老师给我的鉴定是不能修改的,只能砍去“对参加农业生产没认识”那一条。其余的,老师会出尔反尔吗?当然了,我的“罪恶”也许都会涂抹掉,可是,你还能参加高考吗?你用假“革命行动”来换取“高考”的资格,这可能吗?
无可奈何花落去,赵鸿德对此也由反对到理解,由同情到支持。那年,他考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常来信鼓励我实现自己的梦想与夙愿,还寄过来很多的复习材料。
得到同学们的安慰,我的心境暂时平和了一些。但我对高中时期的老师依然耿耿于怀,对同学们依然恋恋不舍,经管我已经是个农民了。
1 同窗学友(知青年代)(6)
1同窗学友(知青年代)(6)
1964年冬,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西北风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生产队不得不歇工一天。就是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中,我耐不住对高中同学们的思念,徒步20多华里,顶风冒雪去了陶家屯羊草沟大队知识青年点看望我的同学。
羊草沟的知识青年们,是新民市也是沈阳市首批上山下乡的热血青年,大都是我们同届的毕业生,也有部分早期毕业的校友。这其中,有的是放弃高考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同学,有的是高考落榜后自愿下乡的,还有极少一部分是社会青年。我们班到这里“大有作为”的一共有五名同学,他们是:常广荣、刘长发、贾广来、温雅坤、李艳芝。他们的家都在新民市内,生活上都很贫困,毕业后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都成了社会上“流浪”的一族。
羊草沟与我家隔着辽河,在我家的西北方向。这里的知识青年点,座落在半山腰上,几栋砖石结构的平房围成一个四合院。房屋虽然很土,但在那时的农村得算得上宏伟的殿堂了,周围的农舍没有一块砖瓦。
男女知青的宿舍很简陋,同当时高中住宿生的宿舍没有一点区别,清一色的南北大炕,一间宿舍要住上二三十名知青,相当于旧社会的大车店。
那天,我刚一出门,脸就被冻得通红,手就像猫咬似的疼痛。本来就很单薄的棉袄,风一吹就透心的凉。我没有走弯弯曲曲的大道,就走“直线”,奔辽河对岸的山头。“直线”没有路,坎坎坷坷的,雪深没膝,还要小心辽河里的“清沟”。“清沟”就是水流湍急水深莫测的地方,那里冬天是不结冰的,大雪天往往被雪覆盖了,就成了要命的陷阱。凭着我是辽河边长大的孩子,还是有些经验的,就壮着胆子走险路,少些风雪的折磨。
等我出现在同学们面前的时候,霜雪几乎遮住了我整个脸膛,所以他们谁都没认出我来。对于我的来到,他们十分惊愕又非常的惊喜,也很“放心”,都长出了一口气。道理很简单,我经受了那么沉重的打击,还活着,这可能吗?至少认为我会落个半疯半傻。他们拥抱着我,把我推上炕头,围着我嘘寒问暖,生怕我突然在他们的包围中蒸发了似的。我也仔细地端详着他们,个子好像高了一些,脸色肯定黑了许多,说话的语音变得粗了。
刘长发拉紧我的手:“会元啊,我真担心你会闹出什么事来,若不然,你干脆也搬到我们这来算了!”
痛苦归痛苦,失望归失望,思念归思念,关爱归关爱……可是,我曲线升学的目的没有实现,怎么会轻生呢?怎么会和他们走在一起呢?我的升学谋略和他们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赞成,不再挽留我了。
青年点的伙食还算可以,大饼子秫米饭能够填饱肚皮,白菜土豆上顿接着下顿,比高中的伙食多了些油花。看得出,所有知青们那种知足的心情流露得淋漓尽致。是的,快要过年了,一群一伙的同学们正在排练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他们没有谁“想家”。
我也不会想家,风雪还在下个不停,估计生产队明天还要歇工,加上大家的挽留,我住那一夜。
青年点的火炕还是很热乎的,“热”得我翻来覆去地难以入睡,回眸着昨天、回味着今天、也回响着明天……
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我和同学们告辞了,担心生产队“开工”,急着赶路。在我们那,冬天上下班要看汽车的“眼色”行事。汽车,就是沈阳每天两趟到月牙河终点站的班车。月牙河终点站离我们生产队队部200米,早车9点到达时,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家家没有挂钟什么的,就靠汽车计算时间。
同学们执意送我很远,一直送到辽河边,好伤感的,有点像电影《怒潮》的送别。《怒潮》是我们高中时代最流行的故事片,那插曲“送君”也很忧伤。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他们祝福我,也嘱咐我,“好好干,别让我们老是为你担心……”
这次造访羊草沟青年点,我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看书复习的,彻底放弃了再次高考。道理很简单:上边说了,上山下乡不是来镀金的,是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所以,他们没有人敢谈论什么升学深造的话题,都一心一意认认真真地接受“再教育”,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所以没有接受刘长发他们建议我到羊草沟,考虑的就是那里的“再教育”氛围不适合我“曲线升学”。然而,这个天真烂漫的战略思想,很快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攻破了。
风风雨雨,寒来暑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历经十几个春秋的高潮后,这股潮流很快就“倒潮”了。回城,就成了下乡的反弹,贾广来、李艳芝捷足先登。常广荣和温雅坤在羊草沟结婚了、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实实在在地扎根在农村。但是,他们扎的根不深,是“须根系”的根,经不起这股比下乡还要猛烈的回城浪潮的冲击,不久也会成了。回城的时候,常广荣已是羊草沟村的党支部书记了。在以后我们聚会的日子里,我和他开玩笑地说:“你是什么党支部的书记啊,扔下几千个村民不管了,独自回城享清福,算什么共产党员啊,简直就是国民党逃跑到台湾……”
我们班的5名知青,最后一个回城的是刘长发,直到1984年他才回到离别20年的故土,和年迈多病的父母团聚。
“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历史了,对此褒贬不一,更多的人把它叫做灾难,他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切齿的伤痛……吃亏不小。但我觉得,“吃亏是福”!
农村、农民、农业都是苦环境、苦行业、苦差事,无处不苦。苦可以磨练人,让人懂得除了苦任何东西都是难以找到的。现在,有人故意找苦吃,找到了吗?肯吃苦吗?倒是那个社会让你有苦可吃,逼着你吃苦,“吃苦是福”的机遇让你享受了,值得庆幸!大多数曾经下乡的知青,他们都有出色的工作,都有自己的业绩,都是单位的中坚力量。在我们的同学堆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同学相聚,人数最多的时候有17人,那时我们都有些老了,山南海北能见面,还有这么多的人,可谓实在是不容易了。细数自己的子女的学历,得出一个惊人的答案:凡是当年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的孩子都没有上大学的。相反,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这仅仅是偶然吗?当然也不是什么命运轮回。我只能用他们父母意志的“磨砺”和不泯的希望,成就了他们的下一代来解释,反正我是这样的。反正我们是“置死地而后生”的,对自己已经毫不在乎了,所以能豁出自己的命去为子女打拼。
我还记得,那次去羊草沟分手的时候,他们5个人一再地叮嘱我:你和赵鸿德是老乡,他和吕维媛又是我们的同学,有机会回来就互相转告一下,大家聚聚。这件事我做到了,但时间已经过去33年。
1 同窗学友(情意绵绵)(7)
1同窗学友(情意绵绵)(7)
赵鸿德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后来成了技术骨干。吕维媛家住新民镇内,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后业也分配到赵鸿德的单位。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保持着恋爱关系,来到齐齐哈尔后不久就结婚了。
他们没毕业的时候,那年的寒假他们俩曾经来看我,大概是1968年冬。那时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住在两间很小的土草房中,四处漏风,窗台上的水碗都结了冰。屋子里除了一个脸冻得通红的孩子和土炕上的几床被褥之外,剩下的就是两个腌咸菜的罐子,一口水缸。这就是那时我的家,寒酸得让他们难以想象,又无所适从。
他们怕我伤心,勉强吃了午饭回到赵鸿德的家。
我们久别才得以相见,要说的话自然很多。话题中,关于我曲线升学当然是他们最为关切的了。现在,这只是个话题而已,各个大专院校都在停课闹革命的热潮中而沸沸扬扬了,谁知道停课会结束在牛年马月,还有升学的年代吗?再看看我的处境,升学比黄粱一梦还要飘渺。此时此刻,我们都强颜为笑,他们只好故作姿态勉励我:“孩子大了就好了,社会怎么能总是这样啊。”他们只能这样说了,也是他们唯一能做到的。我们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