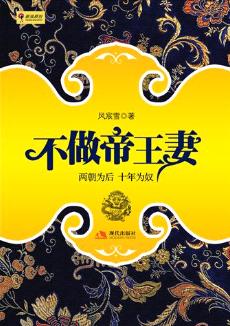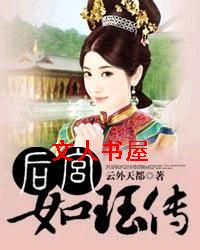江青传-第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春桥经常单独来到锦江饭店俱乐部,跟江青密谈。
最初,张春桥只是作为江青和柯庆施之间联系的桥梁,她尚未发现张春桥特殊的“才干”。正因为这样,江青在上海组织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找的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磺,没有把任务交给这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
江青要在上海抓“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跟柯庆施的联系日趋频繁,跟张春桥也就三天两头见面。不过,此事苦了张春桥,简直是用其所短,避其所长!因为张春桥擅长写文章,“大批判”,舞“棍子”,而对京剧却一窍不通。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说:“我原来从不看戏,只喜欢看书写文章,只进行逻辑思维。”
张春桥却深知,巴结“第一夫人”,乃是官场晋升的一条捷径。只有投其所好,才能使江青欢喜。他只得急就章,从不听京戏的他,不得不借来一大堆京戏唱片,躲在家中“速成”。
柯庆施毕竟是坐镇上海的大员,诸事冗忙,虽说他“亲自抓样板戏”,但只能倚重于张春桥,代他过问。于是,张春桥跟江青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青看中这位山东同乡。正因为这样,请张春桥“挂帅”,主持京剧《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工作。
江青接见《奇袭白虎团》剧组,说了一番意见:
“这个戏反映了朝鲜战场上的真实战斗故事,但艺术概括不算好,生活真实和艺术概括是不同的。艺术概括应比生活更高,要概括当时整个形势和时代精神,艺术创作政治第一。这个戏需要从政治上加强,朝鲜人民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要照顾到两国的关系,我们谦虚一点好。”
张春桥变得颇为忙碌。江青让他“挂帅”改《奇袭白虎团》,又要他“过问”《智取威虎山》剧组,按照毛泽东看戏时说的意见修改。如此这般,连张春桥自己也说:“我成了京剧书记了。”
伸手“抓”《海港》
上海锦江饭店马路对面,是一座棕色面砖的典雅的美国风格建筑。这是闻名于上海的“兰心大戏院”,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建造于一九三○年。在当时,是上海豪华型剧场。解放后,改名上海艺术剧场,仍居于上海一流剧场之列。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海艺术剧场华灯如画,热闹非凡,迎来了一批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还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石西民、王一平等。就连观众,也不是普通的观众,全是上海市局以上的干部。
他们聚集上海艺术剧场,不是开会,却是观看上海淮剧团上演的淮剧新戏《海港的早晨》。淮剧,又名“江淮戏”,流行于苏北、安徽和上海一带。虽说淮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过,毕竟流行区域有限,影响也有限。这天,嘉宾盛赞《海港的早晨》,刘少奇等还和剧团全体人员合影,成了上海淮剧团历史上的难忘的一日,难得的殊荣。
淮剧《海港的早晨》引起刘少奇的注意,是因为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黄埔剧场看过这出戏。周恩来赞扬这出戏,说道:
“感谢你们演了这个好戏,你们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舞台上反映青年问题的戏有《年青的一代》、《社长的女儿》、《千万不要忘记》……说明当前教育青年的重要性。”①
①葛昆元,《江青一伙插手(海港)我见我闻——记上海滩剧团李晓明谈话》,《上海滩》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消息飞快地传入江青耳中。频繁出入于上海的江青,不声不响混在普通观众中,连看了三次淮剧《海港的早晨》!
正忙于“京剧革命”、正忙于树“样板”的江青,看中了《海港的早晨》。要让工农兵占领舞台,她手中正缺乏“工”,而《海港的早晨》恰恰是写码头工人的。
刚刚结束了北京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江青惦记着淮剧《海港的早晨》,忽忽匆匆又赶往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跟上海艺术剧场只一步之遥。
淮剧《海港的早晨》编剧李晓明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突然,有一天团里通知我:下午到锦江小礼堂参加一个座谈会。当时已是八月里,气候相当炎热,我一走进小礼堂就看到有几个人先到了,我便在边上的位子坐下。不一会儿,看见江青在几个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是参加她召开的座谈会。江青同与会者逐一介绍认识后,一坐下便咧嘴笑了笑,一开口就是惊人之语:“我十分高兴,这次来上海发现了一个高精尖的题材,一个国际主义的题材。这就是淮剧《海港的早晨》。”我一听,震惊不小,我的这个青年教育的题材一下子成了高精尖的题材。这时又听到江青说:“在剧场里,我同工人一起看了三遍,工人哭了,我也哭了。”说罢,她还真的用手揉了揉眼睛。接下去,她的话更使我惊讶不已。她说,她是抓革命的,跑了全国许多地方,任务就是看戏,挑选写工农兵的优秀剧目,改编成京剧。写农民的早已选定《龙江颂》,写解放军的也已选定《智取威虎山》,而写工人的选了好久,直到最近才在上海选定了淮剧《海港的早晨》。
她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们,确定改编这个戏,她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其实,所谓调查,只是看了戏后,她到码头上去兜了一圈,向陪同她的第三装卸区主任高尚峰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海港的早晨》在工人中反映如何?第二,剧中青年工人不安心码头工作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实?第三,玻璃纤维事件是否真有其事?在得到高尚峰的肯定回答后,她才拍板而已。
从此,淮剧《海港的早晨》就被江青“抓”去……
这一回,江青指定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挂帅,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负责,组成领导班子,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京剧,编剧为郭炎生,何慢、杨村彬,导演杨村彬。
“上峰”如此看重,编剧们焉能不卖力?才两个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剧本便问世,着手排演,由重祥苓之姐童芷苓及小王桂卿主演。
一九六五年三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石西民请江青审看。江青看罢,竟大为不满,说道:“你们怎么搞的,写了个‘中间人物’,为什么不去写英雄人物?这出戏改坏了,必须重编!”
江青一句话,把京剧《海港的早晨》全盘否定。
第二天,江青调来“京剧书记”张春桥,指定由他挂帅,另组班子,重起炉灶。于是,换了编剧,调来淮剧原编剧李晓明,导演亦换人。江青认为“童芷苓动作太软,演得一点都不像码头工人”,于是从宁夏京剧团调来李丽芳演女主角。
不过,张春桥这“京剧书记”也不好当。怎么改,全要听从江青的旨意。张春桥注意了绕开“中间人物论”的误区,请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审看,剧名改为《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跟《海港》剧组谈话时,又是摇头。江青说,这一回犯了“无冲突论”的错误!
无奈,“京剧书记”遵命,又得僻开“无冲突论”的误区……
如此这般,经过江青“指点”,她在京剧舞台上先后树起了五块“样板”,即《红灯记》、《沙家洪》、《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
另外,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起,“抓”北京、上海两个芭蕾舞剧团,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起,江青到中央乐团,“抓”交响乐《沙家洪》。
这样,江青树起了八块“样板”。①江青博得“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桂冠”,便源于此。
①后来,从一九六七年起,又增加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京剧《杜鹃山》,但人们已习惯于称“八个样板戏”。
由于江青抓“样板戏”作出了“成绩”,她的名字出现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代表的名单之中。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月,当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江青作为人民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她,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
从《人民日报》刊登照片,从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江青日渐“露峥嵘”。这一切,她都在公开地进行着。然而,她频繁地往来于京沪之间,却在暗中进行着极端秘密的政治活动……
第十三章 “文革”序幕
晤会“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你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深圳演出,在深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深圳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四月二十七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六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六月七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六月十一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六月一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六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七月、八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九、十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已经无法再找俞铭横写了。俞铭磺在一九六三年底病危、去世。
江青曾试图在北京找当年向俞平伯挑战的“小人物”写,因为她那时支持过他们。可是,他们竟没有应承下来。
江青再度求助于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便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尖锐地批判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由鲁迅作序),署名“狄克”,此“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笔名。在一九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化名“徐汇”、“吴松”、“常轨”、“子渔”“何泽”、“蒲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
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对金鱼眼睛。其父姚蓬子,也算是一位“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引者注:即周扬)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莲子于一九二七年底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不久叛变,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