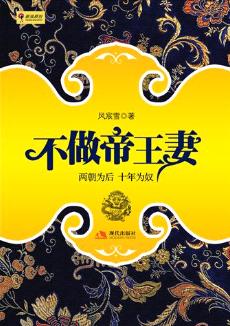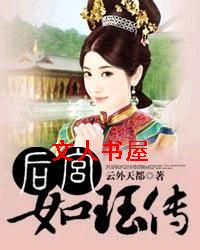江青传-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对人发怒说:“赵燕侠嫌我肮脏!”
即派警卫员要回了毛衣。
此后,赵燕侠被点名批判,赶下舞台,进牛棚,下干校,阿庆嫂的扮演者自然换了别人。①
①翁思再,《阿庆嫂卷进“政治旋涡”》,《新民晚报》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要改《沙家浜》。”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京剧《沙家浜》的名声就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样板”。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两出戏,得力于柯庆施的支持。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曾这样谈及柯庆施: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柯庆施跟“女客人”配合默契。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贯穿这次观摩演出的,便是柯庆施在一九六三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
江青在来沪观摩华东区话剧演出时,又抓了一出新的京剧“样板”——《智取威虎山》。这一回与前两次不同,这块“样板”由上海京剧院排演。
江青一次次对《智取威虎山》剧组下“指示”。她曾说:“《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
然而,当她听见别人对《智取威虎山》颇有微词时,她勃然变色,说了一番声色俱厉的话: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账。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①
①江青,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对《智取威虎山》剧组的讲话。
《智取威虎山》的主角、杨子荣的饰演者童祥苓,经历了类似于赵燕侠的命运。
童祥警当年二十九岁,进入《智取威虎山》剧组,他那一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他的纯熟的演技,把杨子荣演活了,演绝了。
随着《智取威虎山》成为“样板戏”,童祥苓曾“风光”了两年多,名震全国。
一九六六年底,童祥苓忽地从舞台上消失!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写给姐姐童芷苓的一封信,落入造反派手中,一下子把他“揪”了出来。
他是姐姐一手扶植成,步入京剧艺术殿堂的。可是,由于沈醉回忆录中提及一笔,使童芷苓遭殃。沈醉写及,在军统头子戴笠过生日那天,曾叫童芷苓去唱堂会。在那样的年月,戴笠有召,作为一个艺人,童芷苓安敢不去?在“文革”中,这件事被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童芷苓被打成“文化特务”。
童祥苓怎么也想不通,姐姐会是“文化特务”?他给“牛棚”中的姐姐去信安慰。这信被造反派抄走,他也就遭殃了。
于是,他“下台”了。整整两年多没上过舞台。据他回忆,为了姐姐的问题,他写了八十多份检查,还过不了关!
一九六九年,他忽地被起用,重演杨子荣!
他怎么会突然“走运”的呢?那是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要拍成电影。虽然全国各地许多个剧团在排演这出戏,却没有一个演员能像他那样把杨子荣演得出色。江青左思右想,为了保证电影的质量,为了使杨子荣形象生辉,不得已起用童祥苓。
电影拍完了,传来江青的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①
①潘真、徐平,《今日“杨子荣”追踪》,《上海滩》一九九○年二期。
从此,童祥苓又“下台”。直至江青成了“阶下囚”,他这才重新活跃于舞台。
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手中有了三块“样板”——京剧《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江青有了“资本”。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以京剧革命的“旗手”自居。
就在盛大的观摩演出会开幕前一日——六月四日,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了一番和“大写十三年”相悖的话:
“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盛况空前,二十九个剧团、两千多人参加,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三十七个剧目。
齐燕铭主持开幕式,沈雁冰致开幕词,彭真致闭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陆定一作长篇讲话。可以说,主管宣传、文艺方面的头头脑脑都在会上亮相了。
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八月一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把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同样显示了对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重视。
其中的高潮,是六月十七日、二十三日两天,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周恩来在六月二十三日接见了各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
江青在大会上公开露面了。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这是她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进入延安以来,在漫长的二十七年间,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她的这次发表讲话,其意义远比她和毛泽东、苏加诺夫妇的合影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更为重要。
江青的《谈京剧革命》,一派“旗手”口吻: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江青在讲话中,一句也未曾提中共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中共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江青激烈地批评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是“坏戏”,使举座皆惊。
江青还向康生“通报”,由康生出面,在总结大会上,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内中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
张春桥“挂帅”改《奇袭白虎团》
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举行的日子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山东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组与众不同,应江青之邀,进入了中南海。
江青很关心来自她家乡的京剧剧组,观看了《奇袭白虎团》。用她跟剧组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来说:“《奇》剧我第一天看了演出,喜出望外。这个戏准备请主席看,但要修改后才能请主席看。”江青把《奇袭白虎团》剧组接进中南海,就是为了商讨修改事宜。她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她要把《奇袭白虎团》树为“样板”——一旦请毛泽东观看,毛泽东一鼓掌,这个戏马上就可以在全国打响。
在江青会见《奇袭白虎团》剧组时,她的一侧坐着一位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戴一副近视眼镜的上海代表。
怎么忽地把上海代表请来呢?待江青点明之后,《奇袭白虎团》剧组才明白:江青要此人“挂帅”,主持《奇》剧的修改工作。
山东的戏,怎么由上海人来“挂帅”修改?
这位四十七岁的上海代表一开口,哦,原来他并非上海人,却是道地的山东人——他乃山东巨野人氏,只是如今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成了上海代表。
张春桥此人,倒是一块宣传部长的“料子”。笔者一九六三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之后,便多次听过张春桥做报告。他思路清楚,讲话干脆,从不罗嗦,一口气讲两、三小时,滴水不漏。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来到上海,在上海杂志公司当校对员。他给上海各报写文章,和《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笔、山东同乡崔万秋颇熟。前已述及,据沈醉回忆,他在崔万秋家见到过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他也“在崔家见过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不过,张春桥当年是否跟江青有过来往,不得而知。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三、四个月,张春桥也从上海来到延安。后来,他出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而该报社长兼总编则是邓拓。
一九四九年,当红旗在上海城头飘扬,穿着一身草绿军装的张春桥,成为华东新闻出版的副局长。不久,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参与上海机要。一九五五年,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接替陈毅,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这“政治秘书”,听来不过是秘书,却比报社总编辑更为接近权力核心。须知,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年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担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为柯庆施起草种种报告,发言稿,随柯庆施出席种种会议。一九五九年夏,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时,张春桥便随柯庆施出席了会议。后来,张春桥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来沪住进锦江饭店,第一次跟张春桥见面,那是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随同柯庆施来的。见面的地点是锦江饭店俱乐部。此后,张春桥经常单独来到锦江饭店俱乐部,跟江青密谈。
最初,张春桥只是作为江青和柯庆施之间联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