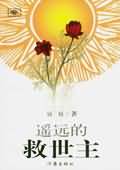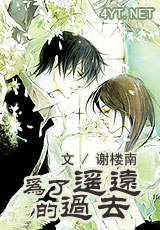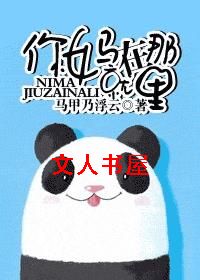那里并不遥远-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房门洞开,白基兴走了进去。他望着空荡荡的房间,不由涌起一阵伤感:十多年了,这里就是住了十多年的家。在这里,他也曾经有过甜蜜与欢乐,憧憬与希望。
然而,那往昔的温柔与欢笑,早已成为过去,几乎被他忘却了,留在他脑子里的,都是那无数的苦恼与悲忿,耻辱与失望。但是,这里毕竟曾经是个家,是他唯一能够免遭侵害的地方,不管他在外面多苦多累,只要一踏入家门,总能感觉到一种庇荫,一丝温情。
白基兴走到临街的窗前,他看着停在门口的汽车。那车上,装着他的“家”:桌子、椅子,床铺、柜子,衣服、被子,脸盆、碗盘……只要用得上的东西,全部都装了上去。只是,他的家当实在少得可怜,半个多的车厢就把他的一切装走了。
白基兴走进厨房。厨房里,已经熄了火的煤球炉孤零零地站在墙脚处,炉身上已经裂开了几道缝,箍扎炉身的铁线锈蚀得快要断开了。他走到炉子前,看着那铁线,回想着当初修理它的情景。如果不是因为山里根本没煤烧,这破炉子他是不会丢弃在这里的。他不由蹲了下去,下意识地伸手在炉子上试着温度,却什么也没感觉到;他又用手摸着炉身,这回终于感觉到了,那里还有一丝残留的余温。他不由用双手扶住炉子,好像生怕它突然倒下,温热散尽似的。
“嘟嘟——”汽车的喇叭突然响了起来。白基兴站了起来,又一次看了看炉子,转身走了出去。
汽车的旁边,驻街道的工宣队黄队长、派出所民警以及街道的几个干部,邻居街坊,还有一些驻足观看热闹的人,见白基兴出来,都把目光投向他。
“还有什么东西?”黄队长看着白基兴问。
“没有了。”白基兴微微地摇了摇头,看了那些人群一眼,默默地走到汽车后面。他见白晓梅与白小松已经坐在车厢里了,便也拉住车门,蹬着车后的铁架想上去。但车厢高了点,他蹬到一半时感到力不从心,眼看就要掉下来,一直关注着他的李顺祥急忙从背后推了他一下,使他上了车。他站在车厢里,感激地望着李顺祥,他想说一句告别的话,但喉咙里却像堵住什么似的发不出声音来。
“坐好了。”黄队长说着,把车厢门关上了。
车厢里顿时陷入一片黑暗,随着一阵“咿咿吱吱”的插拴声,“咔喳”的落锁声,马达的轰鸣声,汽车缓缓地开动了。
从一上车就默默坐着的白小松,站起来走到前面,将车厢上的一个小小的窗子打开。站在那里,可以看到车外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对这辆汽车不屑一顾,各自走自己的路;那些房屋、树木,更显得一片冷漠,从两旁一闪而过。他看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便离开窗口,坐了下来。
汽车微微地颠簸着,速度明显地加快了。白小松突然又想再看看这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又来到车窗口,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空旷的田野,汽车早已开出城了。
他猛地感到心中一沉,便紧紧抓住车窗口,睁大眼睛,可哪里还有半点城市的踪影?
他感到那迎面而来的风吹得眼睛难受,便低下头,重新坐了下来。别了,永别了,我的家乡,我的童年,我的朋友——他在心里默默地告别着。随着汽车的晃动,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也再不去想什么了。
汽车终于停下了,白晓梅到车窗口一看,已经到了青石坑公社革委会的门口。
她知道汽车只能开到这里了,前面的路因为很久没有修,汽车开不进去。不过,她也知道,李卫东他们会来接,而且,她已经看到,前方不远处停着两辆牛车,旁边的那头牛正是队里的大黄牛。
车厢门被打开了,随车前来办理有关交接手续的黄队长朝里面喊了一声:“到了。”然后,他便走进革委会的大门。
白基兴与白晓梅、白小松下了车,在车旁等着。不一会儿,李卫东和张金发及其它几个人从革委会里走出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车上的东西搬到牛车上,捆扎停当。又过了一会儿,黄队长与公社的几个人走出来,与张金发简单地交谈了一下,也向白基兴交代了几句。然后,白基兴一家跟随着牛车,慢慢地向青龙潭大队走去。
在祠堂的边上,有一座破烂不堪的小庙,四四方方不到十平方米,前面既没墙也没门,只剩下一条原来的石台阶。几年前大破“四旧”,小庙是传播封建迷信的场所,理应扫荡,原有的神像壁画被一扫而光。但废物尚可利用,用来关牛是非常合适的,小庙便也因此变成牛的住所。
这次白基兴要来插队,队里再也无法从农民们那里腾出房子了。于是,几天前队里派人对小庙稍加清理,并在前面用谷席竹子挡住,开个小门,另外在旁边又搭了一个小厨房。这样,白基兴的住处算是解决了。
天空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小庙里,摆在桌上的一盏小煤油灯有气无力地燃烧着,它那微弱的光照在这狭小的房间里,使得整个空间显得更为逼仄。
刚刚吃过晚饭的白基兴站在油灯前,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小小的火苗,打不定主意是让它就这么不死不活地烧下去呢,还是把它捻大点?不过,这对他来讲并不重要,只要这灯光能使他看到这个“家”,也就足够了,何况那煤油也要花钱买呢!
他转身面对床铺——刚才来帮忙的知青曾把它戏称为“窝”。对,这就是他的“窝”!他坐在床沿上,突然想试一试“窝”的效果如何,况且他也感到非常的累了,几天来的奔波,使他的体力与精力都用到了极限。他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在头碰到那硬硬的床板的那一瞬间,他的神经像突然绷断了似的,他只感到头脑里“嗡”的一声,变得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了。
恍恍忽忽之中,白基兴感到背后一阵凉,搁在床沿的双腿有点发麻,那游离于躯体之外的魂魄也回来了。他站起来,伸手把油灯的火捻大了点,然后又在床上靠着被子坐了下来。
在依然并不明亮的灯光中,白基兴重新打量起这已经成为“窝”了的家:床铺紧靠后墙,左边挨着衣橱,衣橱的前面摆着桌子,开着的竹门几乎顶住了桌沿,菜橱背靠着前面的谷席,旁边的角落里,几个木箱叠在石块上。环顾整个房间,除了门开的地方和床前桌边那窄窄的空隙,就再也没有落脚的在方了。房间虽然如此的小,可他知道,能有这么的一个住处,已经是够幸运的了。
白基兴的目光缓缓地移到那油灯上的火苗,他的思绪又像那火苗上的一缕轻烟,飞向那并不可知的未来。住的是解决了,但今后吃的穿的用的又怎么办呢?尽管以前在城里的时候,这几个问题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解决过,但毕竟在城里要挣点钱维持生活,总比这里要容易。虽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并不多,但口袋里多少还是有那么的几元钱。可这里明摆着,除了那工分,是很难再有其它的收入,而那工分又是那么不值钱,那今后的日子……?
到今天,白基兴除了这几件啃不动的旧家具,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他的心里不禁感到一阵沉重,也为自己的坎坷经历感到无比的悲哀。他没想到当初自己背井离乡,跨大江,越高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最后的归宿竟是这举目无亲的深山僻野!面对着这昏暗沉闷的房间,他感到心里像是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正在一滴一滴地淌着血。
第七章 泥沙俱下
一大早,祠堂里的知青就都起来了,淘米洗锅,抱柴点火,一片忙碌。两边的过道上,新砌了两个较小的灶,西面的灶前,游清池与张丽萍各站一边,看着坐在小凳子上的游淑惠一点一点地往灶膛里添茅草,却一点也帮不上忙;东面的灶边,石红石兰姐妹俩看着那锅盖边冒出来的汽泡,耐心地等待着;而在祠堂外边的厨房里,吴莲英、王莉莉、侯成宝、马聪明四个人挤在灶边,尽管厨房里没有什么事情非得四个人一起做,煮顿饭一个人就足够了,然而谁也没想离开,默默地等着饭熟;至于李卫东与白晓梅,则早已离开祠堂,到小庙边的厨房烧饭去了。
原来,今天是知青们拆散原先合伙吃饭的格局,重新搭配组合的第一天。本来,李卫东等七个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勉强还过得去。游淑惠一来,当然凑合上去。现在白基兴白小松又来,原有的锅很难煮十个人吃的饭,拆伙分吃便成为一种最简单的解决方式。
但人多并不是拆伙分吃的必然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财产私有这一人性本能对合伙吃饭这种带有利益均沾、有富共享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不满与变革。
由于知青们在农村的生活费用,几乎完全依靠家里供给,因此,伙食条件的好坏,取决于家庭支持的程度。但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一样,那么,从家里带来的吃的东西,必然有多有少。家庭条件差的人自不必说,老是沾别人的光还有什么话好讲?但家庭条件好点的人可就有口难言了!尽管家里源源不断地供给,可这么多张嘴,哪怕你带再多的东西来,用不了两天也就吃光了,吃光了以后照样陪着大家苦熬,长此下去,怎么行得通?
可吃进肚子里容易,要说出口却又觉得在情份上讲不过——同是天涯沦落人,分你一杯羹又怎么样?因此,对于这种不尽人意的状况,得过且过,嘴上不说,其实彼此心中都有个数。
正好,这次多了这么的几个人,趁此机会,好合好散,免得将来扯不清。在有意无意的谈论之中,在闪闪烁烁的言语之间,拆伙的事终于定了下来。
白晓梅由于父亲与弟弟的到来,明摆着再也不可能从城里带东西来了,她实在不好再拖累别人,便先退了出来;李卫东因与她自幼亲如兄妹,也跟着退了出来,与她一家合在一起吃。
游清池与妹妹游淑惠,也另立炉灶。张丽萍与游淑惠同住的这么几天,彼此合得来,便同第二批来的其它人分开了,在此搭上伙。
剩下吴莲英、王莉莉、侯成宝、马聪明,要是再拆开,单枪匹马地去应付那一日三餐,未免费时又费劲,便仍合在一起,原有的厨房就归了他们。另外,石红石兰姐妹俩,也在过道上砌了个灶,自成一伙。
这样,祠堂里面的知青便分成好几伙,各煮各的饭。而且,在昨天的集市上,他们都买了许多的菜回来,准备好好地吃上几天。
饭熟了,菜也熟了,然而,祠堂里面的气氛,却因为这初分开而显得有点生硬。
可也是,昨晚还在一个锅里吃饭,今早却分道扬镳,使得大家心里别有一股滋味。
侯成宝端着一碗饭,边吃边走地来到游清池的灶边。他的目光在与游清池的目光相碰的那一瞬间,像是遇到一股什么力的作用似的,马上折向另一边。他看着放在灶台上的菜,呐呐地问:“煮的什么好菜?”
“能有什么好菜,还不是一样。”游清池讪讪地回答。
“能不能尝尝?”侯成宝显得规规矩矩地问。其实,他的心里对这种沉闷的气氛已经感到很难接受,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把它捅破。
游清池不由感到一阵尴尬——怎么侯成宝一下子变得客套起来了?不过还没等他开口回答,就看见侯成宝正把筷子伸向那盆里的菜。显然,侯成宝正以实际行动来打破这令人难耐的气氛。
“你尽管吃吧,今天的菜多得很。”游清池释然地笑着说。毕竟,分开是不得已的,但也并非不好,只要不因此而把心与心的距离隔得太远,那就行了。
“那我也要尝尝。”马聪明也凑过来,夹起一片菜叶送进嘴里。
“噢,你们都来夹菜,刚分开就想吃别人的?”石兰端着碗走了过来。
“你是不是妒嫉了?”马聪明又夹起一片菜叶,放在石兰的碗里,“这样你就没有话了。”
石兰把那菜叶吃了,笑着说:“怎么,拿别人的东西送人情?那谁不会?淑惠,等下照收他的菜金。”
“那我等一下还她不就行了,我那里可是有一大盆。”马聪明瞪大眼睛,做出一副认真的样子。
“也不要还,也不要收菜金。”游清池拍着马聪明的肩膀,“今天大家都有的吃,所以也用不着客气。只是哪一天免不了三长两短的,大家互相照顾一下,或是有什么好吃的,别忘了叫一声。”
游清池的这些话,也是大家心里想说的。侯成宝像是发誓似地说:“你放心,有什么好事总也算上你一份。不过,今天你这菜还不错,那我就先不客气了。”说着,他又把筷子伸向盆里。
金秋时节,天高气爽。此时,田里的农活已经没有什么好干的了,而山上的茅草却已经长到头了,正等着人们去把它割回来。所以,每年这个时候,队里就要停下十天半个月的工,让大家上山割茅草。
对于这段时间,农民们是非常珍惜的,因为一年的燃料都要在这段时间里备足。
而过了这一段时间�
![[综漫]两百万光年遥远之星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5/502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