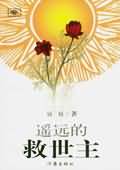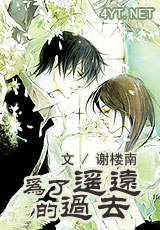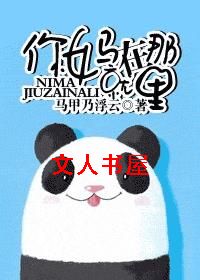那里并不遥远-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迟不愿离去。
收工的人们陆续往回走了,知青们也从那情感的旋涡中走了出来,陆续收拾起各自的东西,跟着往回走。
马聪明又一次望着那茫茫的田野,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暴风雨,你来吧,我们回去了。”
“来吧,快来吧。”侯成宝也接着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第六章 殊途同归
紧张而繁忙的夏收夏种总算结束了。田野里,刚插上不久的稻秧已经返青,一片翠绿。虽然,人们依然早出晚归,但已经不再那么紧张了,农忙过后的一段日子里,人们的心情显得轻松多了。在平和的气氛中,中秋节来到了。
然而,与农村松松散散的情况正相反,又一轮更大范围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在城里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根据政策规定,除极少一部分人可以照顾留在城里外,凡年龄在规定界限内的青年,即使不是三届中学毕业生,也一律到农村插队落户,甚至连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招工进入工厂的人,也被辞退工作,回到原来的学校或街道报名下乡。
另外,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又一组成部分,城市中没有固定工作的人被视为“闲散人员”,也被动员下乡。而那些挂牌的“黑五类分子”,更是这场运动的重点对象,连同家属一起被遗送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
这是一场在上山下乡旗帜下对城市的在扫荡,只要列入名单的人,就无法幸免。
而且,原先在意识形态上泾渭分明,属于不同阶级的人们,不管你是革命的或者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在经历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后,居然殊途同归,一并送往农村。至此,这场以“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为宗旨的运动,其性质已经在逐渐地转化,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惩罚手段,这场运动原先所赋有的革命性也因此而黯然失色。
中秋节刚过,第二批上山下乡的人又来了,这使张金发伤透了脑筋。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自然要坚决执行,可是,其它的问题也许可以逐步解决,就这住的问题最让他头痛:农民们的住房本来有限,但经过一段动员教育,总算腾出了几间房子,可如今一下来了二十多个知青,比原先预计的多了好几个,叫他一时到哪里找房子?望着晒谷场上东一堆西一堆的行李,以及那些眼巴巴地等着他安排住处的人们,他的心里不由地焦急起来。他把张瑞祥叫到一边,悄悄地说:“这么多都在这里也不行。我看,先把那几个女的安排进去,剩下的再想办法。”
“那剩下的怎么办?起码还要再两间才够住。”张瑞祥望着那些在晒谷场上的人,显得有点无奈地说。
张金发想了想,说:“歪狗旁边关牛的那间可以再腾出来,另外的再挤一挤,如果摆得下,一间就多摆一张竹床,先让他们住下再说。”
“那我先叫几个人去清理一下,这里你安排。”张瑞祥说着,走到人群中,叫上几个人走了。
张金发走到那几个聚在一起的女知青前,看了看说:“你们几个跟我走,东西也带上。”
一听要走,女知青们马上忙着拿起自己的东西,一旁的几个农民也帮着把她们的行李拿了走。
“那我们呢?”“我们住哪里?”刚来的几个男知青追着张金发问。
“你们先等一下,我把她们安排好就来。”张金发说完,带着几个女知青朝祠堂走去。
祠堂的两间小厢房里,每间都已摆好两张竹床,一张靠窗,一张靠墙,成丁字形,剩下的就是门开处的一小块地方。西厢房里,游清池正在与他那刚来的妹妹游淑惠一起张挂蚊帐。
原来,按有关规定,对于兄弟姐妹之间已有人先下乡的,后下乡的人可到先下乡的人所在地插队,以互相照顾,叫作“投亲”。所以,游淑惠就“投亲”到这里来了。而且,游清池与张金发事先讲好,安排游淑惠在西厢房住,刚才其它知青还在晒谷场等待安排住处时,游清池与妹妹已经直接将行李搬到这里来了。
张金发带着女知青们来到西厢房门口,对跟在他身后的张丽萍说:“你就住这里吧。”
张丽萍走进房内,把手中提着的网袋放在那空着的竹床上。她看着这小小的房间,有点不知所措。她原本已在工厂当了一年的学徒工,谁知一纸辞退书就把她的所有美梦打碎了,短短的几天时间,就从一个工人变为农民。此时,那巨大的反差还在她的心中上下翻滚着,可那其中的哀怨又有谁能帮她排解呢?她怔怔地站着,不知该做什么。
“你的行李呢?拿来叫我哥也帮你挂好。”已经基本上安排就绪的游淑惠以一种先入为主的姿态,主动而热情地对张丽萍说。
“都在外面。”张丽萍有点释然地说,然后与游淑惠一同走出去。
张金发又走进东厢房,看了看,然后走出来,在人群中找到一个看起来年龄及个子均最小的女知青,走过去问:“你是两姐妹一起来?”
“是。”小女知青有点怯生地回答。
“我们俩是姐妹。”旁边一个年龄稍大点的女知青接着说。
“那你们俩就住这里。”张金发带那姐妹俩走进东厢房,“你们自己先安排好,晚上就到晒谷场吃饭。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先找她们。”他指着站在门外的白晓梅、吴莲英说,然后又带着其它人走了去。
姐妹俩把东西搬进房里,白晓梅、吴莲英便帮着布置整理起来。不一会儿,就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几个人便在竹床上坐了下来。
“你今年几岁了?”吴莲英拉着那叫石兰的小女知青问。
“十六。”石兰回答说。
“十六?”吴莲英看着石兰那还是孩子般尚未发育成熟的身子,不由有点疑惑。
“真的十六了,不信你问我姐姐。”石兰已经不再感到初来的生分了,脸上露出一种纯真的稚气。
“那是虚岁,实际上只有十五。”石兰的姐姐石红在一旁纠正说。
“我说就是嘛,你就没有十六。”吴莲英把石兰搂过来,用一种怜爱的目光仔细地端祥着,“那你还不满十六岁怎么也来插队?”她突然想起什么,又问。
“我……”石兰眼里的稚气倏地消失了,像是受到什么委曲似地抿着嘴。这叫她怎么说呢,如果可以完全任她选择的话,那么,此刻她是应该坐在教室里,与同学们在听老师讲课的。以她的年龄,她应该读书,而且,她也很想读书,从收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起,她就一直在等待着开学的钟声。可是,中学新生还没报名,上山下乡动员却开始了,她的大哥、姐姐均应下乡。
可是,上山下乡的有关政策规定中,却有这么的一条——一个家庭允许留下一个子女在父母身边。父母为了让家里唯一的男孩免下乡,便劝她替哥哥到农村,还叫了其它亲戚来开导她:如果哥哥不下乡,可以在城里安排工作,找到工作挣到钱,家里的收入便增加,也可以支持她与姐姐在农村的费用;如果哥哥下了乡,她去读书,那一家人靠父母的工资,生活就会更困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重男轻女这一被批判过无数次的传统观念在父母的头脑里,以及在亲友的心目中依然根深蒂固。在这么的一种环境中,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又能有多大的主宰呢?
所以,她唯有收起入学通知书,满腹无奈地到街道革命领导小组报了名,同姐姐一起下乡插队,成了最年轻的知青。
晒谷场上的行李渐渐的少了,这使守在一旁的章华荣不由地心慌起来——天已经快黑了,可队长还没安排他住的地方,那今晚睡在哪里呢?尽管在今天来插队的人当中,他算得上见多识广,甚至称得上老油子了,可面对这杂乱无章的场面,又是人生地不熟,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是耐心等待,别无他法。他点燃香烟,蹲在台阶上独自贪婪地吸着,浓烟淡雾中,那烦心的等待被暂时丢在了一边。
长得瘦巴巴的章华荣怎么也没想到,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竟也会被算作“知识青年”。他只不过读了两年书,连自己的名字写起来都感到费劲。在他十岁的那年,父亲因犯罪被判刑,又意外地死在劳改农场,母亲也连气带病死了,他就跟着叔叔过。可他书不好好读,老是逃学,跟着一帮孩子东溜西窜,到处惹事生非,不是打了人家就是被人家打了;学习成绩倒数第一,做出来的作业连自己都不知道写的什么,结果被学校开除出来。
他的叔叔对他也是烦透了,有时气不过,打他一巴掌,结果是连续几天不回家,管也管不住,只好任他去。后来长大了,他也想找点事干,可人家一看他那只长骨不长肉的身子和那一副尖腮细眼的容貌就摇头,一打听以往的情况更是不敢要。几次碰壁,他也就死了心,跟着一帮人偷鸡摸狗,倒买倒卖,倒也自由自在。
谁知这一次上山下乡动员一开始,他的名字就被列在下乡对象的名单上,像是板上的钉,抹也抹不掉。就这么着,他也随着别人来到这里了。
一支烟抽完了,章华荣心里不由又着急起来,便站起来四处张望。这时,张金发与张瑞祥又来到晒谷场,章华荣急忙走上前,掏出香烟给他俩递去:“队长,抽根烟。”他等他俩点上烟了,才又说:“我住哪里呀?”
“等一下,马上给你安排。”张瑞祥指着大个子的黄唯山与长得有点文弱的程强,“你们两个跟我走。”
“那我呢?”章华荣忙拉住张瑞祥问。
“你也一起走。”张瑞祥回答说。
章化荣与程强、黄唯山忙收拾起东西,跟着张瑞祥来到一排低矮的房子前。
这里原先是一座地主的大院,但主房大厅不知什么时候倒塌了,留上几道颓垣断壁;北面西面各有五间小厢房,每间宽度只有二米,长度也不过四米——那是解放前地主给雇工住及堆放杂物的。土改时,这些房子分给了贫雇农,张歪狗分得了北面的三间。公社化后,分得另两间的老雇农死了,张歪狗又把他隔壁的一间当了厨房,最边上的一间便成了队里关牛的地方。刚才,张瑞祥与人忙着清理的就是这间牛屋。
一行人来到这最边上的房门前,打开门,一股霉臭味迎面扑来。章华荣忙掏出烟,先给张瑞祥递上,又很快地将打火机打着,凑到张瑞祥跟前,然后他自己也点上支烟。
房间里没有窗户,几个人站在门口处,更使里面显得昏暗无比,好一会儿,章华荣才看清里面摆着三张竹床,一左一右,后面一张打横。他马上选中了对着门的这一张——这位置比较通风,也亮了点。他迅速地将行李打开,铺在上面,不等程强、黄唯山回过神,这床铺已经归他了。
长相看上去有点憨厚的黄唯山,对睡在哪个铺位根本无所谓,只要能有个地方躺下就行了。他问程强:“你要睡哪一床?”
“我睡后面吧。”程强看着这狭小的房间,无可奈何地说。此刻,即使整个房间都归他,也无法抹去他心里的失望。他的家庭条件在一般人的眼里,是属于上等的:父亲在物资局,掌管着全市的钢材、水泥等紧缺物资,找他批条子的人总也顺带着送点时鲜土特产什么的;母亲在市革委会食堂当主任,花同样的钱肯定吃得比别人要好;住的更不用讲了,既宽敞又明亮。就说这次下乡插队,本来按划片分配,他是分配在更远的地方,可父亲略一开口,马上有人帮他弄来了三级证明——即接收地的县、公社、大队同意来本地插队的证明,结果他就来到这里了。只是,他没想到这里的情况竟是如此的糟糕,居然要睡在刚把牛牵出去的房子里。
程强整理好自己的铺位,重新审视着这已经成为住处的房间:地上铺着鹅卵石,石头与石头之间的泥土黑得像是倒上墨;墙壁上刚抹上的黄泥,留下了他刚才按上去的一排指印;屋顶的椽木瓦片一片乌黑,但从那铺盖疏薄的瓦片缝隙中却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夕阳的余辉正从那些缝隙中钻进来,斑斑点点地投在墙壁上。这样的房子也是人住的?他的眉头不由紧锁了。
大批的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以后,城市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然而,这种平静没多久,遣送“黑五类分子”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工作又使城市再一次波动起来。虽然,这种波动与前不久的狂涛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漂泊在这波动之中的人,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深深感到,他们那脆弱的命运之舟,随时都有可能遇到灭顶之灾。
白基兴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走到楼梯前。尽管他知道楼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再搬了,但是,最后再看一眼“家”的欲望驱使他又一次地走上楼梯。
房门洞开,白基兴走了进去。他望着空荡荡的房间,不由涌起一阵伤感:十多年了,这里就是住了十多年的家。在这里,他也曾经有过甜蜜与欢乐,憧憬与希望。
然而,那往昔的温柔与�
![[综漫]两百万光年遥远之星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5/502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