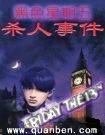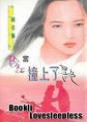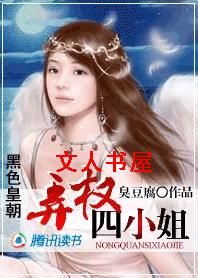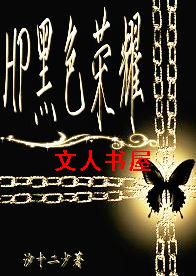黑色念珠-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蛰这个人,极端蔑视礼教,就被逼疯了。罗水泊说得激动了,又站起来踱来踱去,还往夜色迷蒙中的塞纳河里丢了一颗石头。他长长叹息一声又说:“可是,我们还是爱我们的民族!挚热地爱它。这不仅仅因为我生在中国土地上,长在中国土地上,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血肉相依!还有,正是因为这样,历史放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才特别沉重,我们又必须挑起它!”罗水泊讲到这一句话,用力地挥舞着拳头,差点儿没打着我的鼻子,哈!
啊,啊……
一九四九年底,我俩离开了法国,先去了瑞士,又到波兰,经由苏联回到了祖国。
我俩并不怎么喜欢巴黎。这个城市的妩媚不减当年,香榭丽舍大街整洁、静谧,沿街到处是草坪和鲜花。巴黎虽然也经历了战火,常见到一些房屋废墟,可主要建筑物还保存完好,大、小皇宫、拿破仑墓、凯旋门,还有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埃菲尔铁塔,我们常常去游玩。我俩还跟几个中国留学生去过一趟柏林,是搭乘美军的军车去的。柏林可是满目疮痍了,到处都是破烂的瓦砾堆,几乎见不到什么高大建筑物了。但是,我俩却感觉到战后的巴黎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颓唐和萎靡的气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贝当政府腐败无能,战争爆发不到六星期就兵败如山倒,投降了纳粹德国,强大的法兰西帝国一下子崩溃,沦为德国傀儡国。这种历史耻辱深深刺痛了法兰西民族的自尊心,再加上战后的经济不景气,政治局面一片混乱,也更使人丧气。在巴黎,数千人的示威游行天天不断,老百姓人们忍饥挨饿,衣衫褴褛,最注重服装仪表的法国人竟然穿着木板拖鞋上街,由于没有皮革制鞋!
巴黎的气候很奇怪,刚才还是金色阳光照耀着,一会儿又是乌云遮日,下起霏霏细雨。法国人没有打伞的,他们悠然自得在雨里走,干自个儿该干的事。我俩呢,在街上蹈跳着,钻进一家小酒馆,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秃顶老头儿站在柜台前。我俩每人要一杯苦艾酒,坐下慢慢啜着酒,瞧着窗外湿漉漉电线上淌下的水滴,只是怔怔望着,一句话不说,滋味儿是很闲适的。
兀地,闯进一个歪戴船形军帽的美国大兵,冲我俩挥手打个招呼,吊儿郎当地坐下。秃顶老板顿时忙活起来。端来了啤酒和苹果馅饼之类的吃食。美国大兵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喝着啤酒,一会儿,又进来一个瘦削的法国姑娘,脸色苍白,很年轻,用手轻轻拢着淋湿的金发。她走到那个美国兵跟前,问他要香烟。很快,两个人就傍在一起了。姑娘讲着结结巴巴的英语,美国兵说着词序混乱的法文,两人又呱呱笑着。又一会儿,那个法国姑娘被美国兵搂到怀里,他旁若无人伸出一只手在她的蓝色衬衫里任意摸索着,她咯咯地笑出声,好像一口水噎在喉咙里。
我和水泊尴尬地对望一眼,准备起身出去。
我俩刚站起来,美国兵和法国姑娘也互相搂着跌跌撞撞走出小酒馆。临走时,美国兵丢了两张美钞在桌上,向秃顶老板打个响指。
我俩跟秃顶老板结账时,水泊却忍不住说了一句:“唉,你们的姑娘……怎么能这样!”
水泊常常是这样,很天真。但是,这句话实在不该说的。由于文化因素不同,东方人与西方人有一层很深的隔膜,我们当然不应该用自己的道德观去随便批评人家。我赶紧拉了一下他的袖子,他大约也觉出了,脸涨红了。
那位秃顶老板却很冷漠地瞥我俩一眼,问:“你们是日本人?”
“哦,我们是中国人。”
“你们尝过饥饿的滋味儿吗?”
我们俩没有回答,只是窘迫地笑一笑,付了钱,就赶快走出小酒馆了。水泊引出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他自己也觉得可笑。我们都是从穷困的中国出来的,当然都尝过饥饿的滋味儿。症结却并不在这儿,我们企图用中国的道德观去说服法国姑娘吗?告诉她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才叫逗乐呢。
我俩能到欧洲留学,完全是偶然机遇所致。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们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都学法语,也略通英文。忽然,一纸征调令下来,让我们去给美军顾问团当翻译。我们内心很兴奋,巴不得为国效劳呢。天天捧起一部汉英词典,拼命补习英文。当时,一些高年级同学已被征调到孙立人部的美军顾问团里,随军进入印度了。应征那天晚上,宿舍中聚集几个同学,喝一瓶白酒,吃着花生米,卤牛肚等,又点燃一支蜡烛,天南海北聊着,还唱了《满江红》。我们明白自己是翻译,打仗的机会挺少,却仍然渴望上前线,能端起刺刀战斗。其实,我俩随着美军顾问当翻译一年多,根本没有到最前线去过。倒是沾了那些美国人的光,吃了不少牛肉罐头和巧克力。在桂林附近,遇到几次日军飞机轰炸,炸伤了水泊骑的一匹马。与我们在一起的美军上校纳特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伯克利大学研究古汉文的教授,说话常常用古文句式:“君知否?”“余心甚慰”。我们有时也一下子听不懂他那怪腔怪调的古文呢。不过,纳特的法文也很流利,我们更多是用法文交流。平时有大量空余时间,纳特对中国诸子百家中墨子的哲学思想很感兴趣,水泊是世家子弟,几代相传的书香门第,国学根抵也很深,纳特与水泊很投机。抗战胜利后,纳特要回国了,一天晚上,来找我俩,说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在巴黎大学当教授,也是研究东方文化,写信来要他推荐两人去当助教,问我们干不干?还说,去法国的路费都不用我俩掏,就要我俩办好出入境手续和护照。过些日子,恰有一架美军飞机去巴黎,他拜托一位朋友,诡称我们有公事去欧洲即可。这真是从天上掉下一个金元宝,我俩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就赶紧做各种准备,护照与入境签证都是纳特帮忙迅速办好的,我们只是准备一些衣物,匆匆登上飞机。本来,我和水泊都想回一趟老家,拜别父母高堂,由于时间紧迫,也只好作罢。以后,整整半年时间,我们各自的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去了哪儿,为我俩一下子没有任何消息而惊慌,以为我们已战死在疆场了。
这一段经历,那时对于我俩来说,固然是幸运。但是,正如庄子所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解放以后,我俩回国,却又成一个怎么也洗不清的历史疑点,常有人审问我俩,那个美国人纳特为什么会好心眼儿介绍你们去巴黎呢?有谁能证明他的举动不包含任何政治用意呢?又谁能证明你们俩在巴黎大学只是教书和读书,没有为帝国主义特务机构服务呢?唉,我俩真是有口难辨!罗水泊就为此发牢骚,五七年被扣上右派帽子。我呢,战战兢兢地谨慎过日子,也到底在文化大革命时因为“美国特务嫌疑”的帽子被关进牛棚。
在五七干校时,领导分配我俩一起去放鸭子,同出同归,我们又亲密起来了。那时,他的老婆秦少蓁在文化大革命初自杀了,孩子们也与他断绝来往。水泊成了孤零零一人,他似乎满不在乎,空余时间就抓本书看。中国书,外国书,古文书,历史书,经济书,什么书都看。我呢,因为老婆写信要求离婚,心情非常压抑苦闷,晚上提了一瓶二锅头去找他。也没有下酒菜,只是对着瓶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两人不提眼前的事,却津津有味回忆起在欧洲的三年生活。这正如唐代诗人贾岛所写的:“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把并州做故乡。”巴黎大学的校园在一个小城镇,避开了都市的喧嚣,山清水秀与江南景色相近,我俩在担任助教同时还攻读了拉丁语言文学和古希腊史等等。放假了,就到各地游历,去过波尔多、马赛等地。还去过与法国相邻的比利时、荷兰与意大利,我俩是穷学生,当然掏不起钱旅游这些国家。是罗水泊认识了一个专管后勤的美军军官,我们跟着运输军需品的车子去游玩的。水泊这人很聪明,到了哪儿都有办法,那段日子真是色彩斑斓啊!
那天晚上,聊呀聊的,尽情回忆着,我忍不住问他一句:“水泊呀,你说,我俩当年若是不回国,仍是留在国外,又会怎样?”
他脸上红扑扑的,斜睨一眼,洞穿我心思地问:“怎—;—;么,后悔吗?”
我又反问他:“难道你不后悔?”
他把酒瓶一顿,一字一句地说:“我—;—;不后悔。”又引一句屈原的诗说:“虽九死其犹未悔!”
听了这话,我默默无语,一点儿也不奇怪,晓得这是他的心里话。水泊这人,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激烈批判旧伦理道德,认为那些观念是陈腐的,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合理的。可是,他自己身上又有一种“君子之风”,一股很浓厚的古代儒家士大夫的气质。忠义呀,孝顺呀,气节呀,特别是家国观念,其实都深深根植在他思想里。大概,这也是他所说的“双重人格”吧?
前年,我应巴黎大学邀请,又重新到了法国。
已经四十年啦,真是弹指一挥间。我已经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了,水泊兄也已经离开了人世。在飞机座舱里,我猜想,我所去的那座小城镇必定大变模样了,恐怕我已经完全认不出了。它的街道会拓宽,许多建筑物必被拆毁,大约仅只少数值得保护的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物还在。总而言之,我所去寻的,是一个早已消失的历史幻梦。这一切,我应该做好精神准备。
谁知道,恰恰相反。
这座小城镇一点也没有变化,古旧方砖慢地的狭窄街道,仍是凹凸不平。街旁仍是造型很美的旧式小楼,每家都有小院子,里面种满了鲜花,几乎没有建什么新的建筑物,我很快就找到了四十年前和水泊同住的那所公寓小楼,也是完全没有变化,不过由原来院子所种植的丁香花变成了郁金香花,太阳照射的旧围墙爬满了常青藤,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我走到沉重的铁栅栏门前,望着生长了黑绿色青苔的石阶,阳光一片灿烂在石子缀成的甬道上跳跃,我很想推门走进去。
对过也仍是那座天主教堂,很高的尖顶竖着,淡黑的影子荡漾在缀点了野花的绿色草坪上。飘渺的钟声又从教堂里传出来,悠远又肃穆,凝重地回旋在蓝天碧空。
街上几乎一无声息,我瞧见了拐角处的那座小咖啡馆。甚至使我相信,那个红鼻头老头儿掌柜也坐在柜台里,又拿一份报纸在读着。见我进门,一定要问我,水泊怎么没来?因为,我俩总是相伴而行的。
连我自个儿都怀疑了,好像根本就没有经过四十年沧桑。我不过是独自到哪儿去玩了一天,然后,又疲惫地回到这儿。在那座公寓小楼里呢,罗水泊正捧着一本精装书在津津有味读着,见我进去,又必定是连头也不抬。那个胖呼呼的房东老太太拉杜霍正在厨房忙乎晚饭呢,她的丈夫让·;克鲁先生则一本正经坐在餐桌前,彬彬有礼地向我微笑点头。这种生活已经在我的记忆里被分隔得很遥远模糊,它却又下一子缩回来,真切地呈现在我面前。
我回过头,盯着后面不远处那幢茶褐色小楼。
很可能,一会儿,朱丽小姐将从里边走出。她身材颀长,体态轻盈,一头红发向后梳,乳白色皮肤,不像是法国女孩子,更像荷兰姑娘。她长长的睫毛娴雅地垂在漂亮的鹅蛋脸上,随意挥手朝我打个招呼:
“嘿!罗在里面吗?”
她从来是这样称呼我俩的,管我叫宋,管水泊叫罗。她听说水泊还在屋里,轻快地一扭身,匆匆去找罗水泊了。我呢,略带点迷惘和嫉妒地呆望着她的苗条身影。
我们是一个夜总会上认识的。聊一会儿,才知道她就住在我俩的公寓楼的后面,在学校图书馆的打字室当打字员。罗水泊邀请她跳舞,当时有两个乐队轮番演奏,水泊的舞姿很笨拙,老是踩她的脚,转错方向,身体与她保持一尺距离,那模样又狼狈,又激动,还有点儿傻哩傻气的。她穿一件黑丝绒紧身胸衣半掩半裸露着少女的乳房,两眼闪闪发亮地凝视着水泊,不住地说话,咯咯笑。
从夜总会出来,我酸渍渍对水泊说:“嗬,你交上桃花运啦……运气满好呀!”
水泊掩饰地说:“咱俩的运气都好,你知道吗?这姑娘愿意教咱们法文,只收一半费呢。”
对我俩来说,倒真是一件大好事。当时我俩在一个法国小学教师家学法文,他家的距离较远,有三里多路,要走半个钟头。若是由朱丽教我们,既节省了时间,又省了钱,当然好啦!
之后,我们就常常在晚上或是下午,到朱丽家去上课。那幢小楼只住了朱丽和母亲两人。朱丽爸爸在战争中被飞机轰炸时炸死,她的一个哥哥也在前线战死了,惟剩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朱丽的母亲是个性情温厚的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