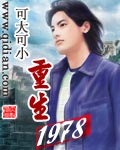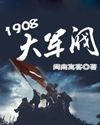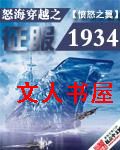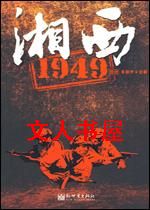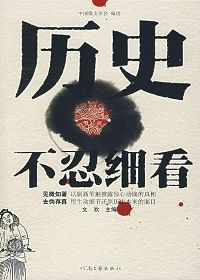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半是忧伤半是潇洒地说“此事古难全”。今天的中国人则用月亮来形容党的政策,说是“初一、十五不一样”。可是无论怎样的“阴晴圆缺”,中国人又有哪一次不是张开双臂来欢迎的?
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已经不大时兴,城里人对这些事情大概是疲倦了,没有再跑到街上来高呼别人教给他们的口号;乡下人整日为了衣食牵肠挂肚,哪里还有敲锣打鼓的闲情。不过,大标语还是盖满了街头,政府机关的大门上张灯结彩,商店把巨幅贺词覆盖在商品之上。那一个早上,中国大陆出版的二百五十三家报纸,一律将鲜红的颜色套在自己的头版上,有的索性还把这象征节日喜庆的色彩染到二版和三版上去。新华社的消息说,北京的“人们精神振奋”。到了第二天,记者们可能是觉得这样的话这些年里已经说了无数次,今天再一次重复已不够味道,所以各地报纸又发布消息,说有十四个省市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在23日连夜开会。记者们异口同声地说:“大家表示,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适应这个转移,跟上这个转移。”随后,大部分省市的领导人沉寂下来,他们中间一些最重要的人物本身就是会议的参加者,亲临现场,自然会将种种内外关节—一看在眼里。他们需要时间向下级通报一些惊人的消息,并且一同来考虑如何应对新的局面。但是,舆论并不会出现空白,各个大报的总编辑早已经运筹帷幄,全部的程序乃是仿照十几年来屡试不爽的办法。到了第三天,该轮到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出来发言。于是,最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就有机会在《光明日报》上表达他的激情。他写道:“盼!平生的盼望!早就盼着这一天!(1978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其余名人雅士也都不甘寂寞,或撰文或演说地讲述他们的“盼望”。甚至佛教界最有名望的班禅大师也介入进来,他用一种大有禅意的话来影射华国锋的理论:“我历来认为,为了永远不穿草鞋暂时穿草鞋是应该的;如果为了穿草鞋而穿草鞋是没有意义的。”(1979年1月1日《中国新闻》。)然后又轮到普通百姓。山西省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蹲在著名的狼窝掌里说:“太符合我们贫下中农的心愿啦!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贫下中农想到一块啦!”(1979年1月8日新华社《新闻稿》。)她还不知道“英明领袖”现在有多尴尬,不过不久就会知道,而且她自己也会饱尝这种尴尬的滋味。那时还没有那种大铁锅似的东西来转播卫星播送的消息,但到了第五天,遥远的丝绸之路上也有“盼”的声音传来。一位叫作肖克忠的铆工将二十年来的政治运动一个一个数了一遍,然后说道:“国家受害了,人民受苦了!我们盼的就是今天,可盼来了。”(197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后来的几个月中,这种情绪迅速弥漫起来,有一句话在上上下下大为流行,这话说三中全会是“第二次解放”了中国。
一步一回头(8)
对于那些终于摆脱屈辱重蹈政治舞台的老人们,说“第二次解放”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多少年来大家第一次发出了由衷的笑声,邓小平也以胜利者的微笑来接受大家的祝贺,不过,他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放下心来的。这倒不是因为他经历的风波太多,以至今天还在担心天有不测风云。他是熟谙政治舆论的行家里手,知道民心的价值。表面的舆论常常不能说明真相。两年又八个月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舆论也是一夜之间铺天盖地,举国高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批邓’进行到底”。这件事给予邓小平的印象太深了。他根本不会相信那是民心。报纸叫作“党的喉舌”,其实党是由人组成,因而报纸只是最有力量的人的喉舌。几天前,他在中央全会上曾尖锐地说,在共产党内,大家只能奉命行事,什么问题也不用思考。不讲原则,说话看“来头”、看“风向”,“随风倒”的现象已经多起来。(参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2页。)过去是随毛泽东的“风”。现在,轮到他邓小平主持大政,他必定也对这种现象抱有高度警惕。问题不在于人们表面上说什么话和敲什么锣,而在于心中所想及弦外之音。
1979年元旦刚过,省委书记们便用自己的言论把报纸的头版占去了大半。农业以及农村的问题乃是必须要说的话题。安徽乡下有些地方本已经悄悄地把田分开,这时候却看到了全会决议上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看来他们的行动大有越轨之嫌,这时候只好先避开短兵相接的搏斗,采取远兜远绕的迂回战术。历时十五天的省委会议宣布了自己的方针:“在建立健全责任制的问题上,思想要再解放一点,办法要再多一些。”它还说:“生产队愿意采用什么办法,应由群众民主讨论决定。”等于是说,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这一条是算数的,但这“不许”、那“不许”可不一定算数。(1979年1月19日《安徽日报》。)青海省的领导一下子没有看出此中奥妙,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省委机关报发表了一篇不痛不痒的社论,说“在我党的历史上,每逢历史性的转变关头,都会伴随着全党的学习运动”(1979年1月5日《青海日报》。)。邻近的甘肃省,报纸也在早几天发表了社论,说政治要保护经济,阶级斗争必须同排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联系起来。(1979年1月2日《甘肃日报》。)###这时还未进京,还在四川省当他的省委第一书记。他虽未像万里那样在农村发起对人民公社的挑战,但他明显地对华国锋的失势与邓小平的崛起感到愉快,而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要在邓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情绪。他在四川省委会议上报告:“从总体上说,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已经扫除。”(1979年2月15日《人民日报》。)这话的大胆之处在于,当公开的舆论还把华国锋看作党的中心时,赵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他扔到一边了。辽宁的任仲夷也是数十位省委书记里面最具反叛精神的人之一,几个月前,当“真理标准”的争论双方还胜负未卜的时候,他最先表示了自己反对“凡是派”的立场,这是中国官场上极少见的勇气,可是这时他还是没有敢直面“包产到户”。他的办法是把精力集中于阐述较少争论的问题,他告诫下级:“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必须抓住一个中心,就是工作着重点的转移”(1979年l月9日《人民日报》。)。这话现在已经不会再有风险,因为即使是华国锋也不会反对这个话题,只不过,华的“转移”与邓的“转移”不是一回事。
看到舆论绕来绕去还是在外围徘徊,《安徽日报》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它发出进一步的暗示,说“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土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块水面没有利用起来,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李克文:《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见1979年1月24日《安徽日报》。)。这里面主张“包产到户”的味道,即使再愚蠢的人也会闻得出来。可是多数省区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太聪明。整整一个月里,没有人出来呼应安徽的声音。到了1月下旬,终于再也不能回避。西部的陕西省打破了沉默,但不是附和安徽的声音,而是相反。23日,陕西省省委会议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刚刚进入政治局的王任重副总理在这次会上讲了同样的话,(1979年1月3日《陕西日报》。)这使得陕西的理直气壮看上去大有来头。江苏省在东部,与陕西有遥遥数千里之隔,现在却决定与陕西异口同声,省委书记许家屯虽然说要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可是又说:“试行责任到组联系产量有奖有赔办法,进行比较,但不要急于全面推开。大农具不能分,更不能包产到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坚决纠正过来。”(1979年2月19日《新华日报》。)这大致是重复了会议的文件。这一来,不少省委书记都记起三中全会上的这一句话,于是全都照方抓药,包括云南、新疆、山西、河北、河南、湖北。这是一种无论什么风吹浪打都不会翻船的办法。看来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的力量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四川这时也许有一点犹豫。私下里,###在省委扩大会议上问,干部最大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大家说,最突出的是“恐右症”。这种思路要是延续下去,四川立刻就是安徽的同盟军了。果然,会议发表的决定给了农民一个前所未有的解放,它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进行试验。”不过,赵还是没有勇气拆除最后的屏障,他重申,“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广东省的习仲勋再次仗义直言,只是略施小计。他们说,只要不分田单干,各种不同的办法都应当允许。(1979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他们的小计谋是故意不提“不许包产到户”。既不禁止,农民也就可以实行;可是他又没有允许,一旦有失,作为一省之领导,还大有退却的余地。另外一些省委书记一定意识到这里面事关重大,所以与其打一场无准备之仗,不如行兵家避实就虚的策略。内蒙古的周惠说,内蒙古的“关键是解决好遗留问题,配备好领导班子”(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山西省还是念念不忘它的大寨,第一书记王谦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1979年1月25日《山西日报》。)湖南的书记毛致用也学着山西的话,一句也不提生产责任制,只是说湖南“要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这个讲话时,竟把这一句话全部删去,令毛书记大为紧张了一阵。(见1979年6月5日《湖南日报》和6月19日《人民日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步一回头(9)
到了2月,表面的热闹已经平息,大家都发现气氛有些沉闷。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心口不一的本领,非到关键时刻,不会把心里话讲到桌面上来。大多数报刊的编辑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用“心有余悸”来描述那个时候的局势。《安徽日报》的文章说:“十分明显,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地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然后作者就鼓动人们去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薛理:《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见1979年2月12日《安徽日报》。)。
不过,真正心口不一的还不是这些心有余悸的人,而是另外一些从来不知“悸”为何物的人。对于他们来说,邓小平的得势是一场灾难。这种情绪虽然从未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却也宣泄得淋漓尽致。有人问:“现在的党中央姓马还是姓刘?”这是把马克思和刘少奇当作“主义”的分界。有人说,“果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不错,修正主义出来了”。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夜里,山西省运城地区党委的大院子里,就贴出来几条标语,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标语的书写者竟是地委机关里的一些干部。湖南省的传言中,有一种说法借用邓小平对“文革”的形容,说三中全会后“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还有人说,“中国将在混乱之中前进,好像电影《逆风千里》一样”。这电影说的是一支军队如何在极为恶劣的气候里与敌人作战的故事,这些人借此来形容新的时代。可见确有不少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不满,等待着再一次“变天”。
事情有些稀奇古怪。沉寂了两年的中国,如今居然在一夜之间就急剧地旋转起来,每一个人又都忍不住要将满腹智慧一吐为快。那一年的年初,似乎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街上拥挤的人群里面,大发议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当作讲坛。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讲坛是由当代中国一群最著名的文人开辟的。
文人们现在要把思想解放的成果再行扩大。他们对“两个凡是”的初次打击居然获胜,这是从未有过的战绩。看来乘胜前进是必要的。l月18日,文人们聚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里几乎所有有点名气的人都来了。这可真是一个理论的春天,只不过,会议的名称有点怪: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议看来具有某些官方色彩。其最初酝酿是在党的政治局中,由叶剑英提议,而由胡耀邦全力推动。但是数百名与会者却是形形色色。这些人满怀豪情整整说了一个春天,直到4月3日才算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