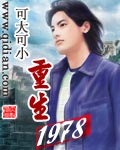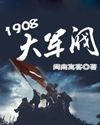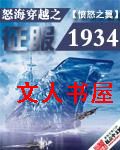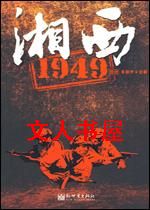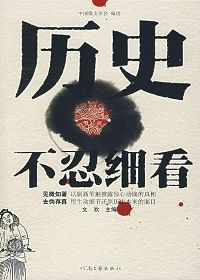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显然是因为实际进程中“包产到户”已难以阻挡,令党中央对这个昔日“最危险的阶级敌人”略加宽容。比如1979年版本中增加“我们狠抓粮食生产是对的,但是忽视和损害了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没有注意生态平衡,这是一个教训”一句,显然是对毛泽东“以粮为纲”的露骨批评。新的版本还将“要继续抓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把这个运动同贯彻执行上述各项政策和措施紧密联系起来,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整段一笔勾销。这就已经明显地暗示,华国锋发动的“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应该结束,因为它与执行新的农业政策已经无法“紧密联系”。最后,它还毫不留情地删去了“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这又等于是宣告毛泽东倡导并由华国锋继承的“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计划已经流产。
一步一回头(5)
但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季里,农业方针的变化在可以操作的步骤上还是含混的,新的决定中仍然带着历史的惯性:不许包产到户,生产队的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粮食关系到备战备荒之宏旨,所以一定要抓得很紧,普及大寨县和执行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农业机械化仍然是农村的首要目标……这一切令人感到既定方针的不可动摇。但是,人们仍然把它视为新时代的起点。后来十几年中,无论赞成还是批评邓小平方针的人,对这个起点的界定倒是一点也不怀疑。看来,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邓小平给予农民的最大好处并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思想观念。农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懂得了把“白猫、黑猫”的理论用以对付阻碍他们行动的教条主义官员。所以虽有“不许包产到户”的禁令,但是那些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都一律从文件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鼓励。“三中全会的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对访问他的一位记者说道。事实的确如此,农民从这个历史性会议上面得到的全部实惠,就是“可以”二字。后来几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
然而有一个重要决定的获得通过,在这个会议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这就是部分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按照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文件,到来年夏季粮食上市时,将把国家收购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还许诺将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的收购价格也作出相应的提高。这一决定的正式通过还要等到1979年的秋季,但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行动实际上自春天就已经开始。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依据中共中央决定中的这一条款,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将提价的时间表由夏季提前至3月。这中间一部分的原因是要将提高价格的行动赶在春耕之前,似提高公社社员的耕作热情以及全年的收成;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一项方针本身没有引起任何异议,所以可以畅通无阻。不过,价格的提高由于各地的自行其事,而令最后的统计发生分歧。中###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叫做《新时期专题纪事》书里说,这一次提高价格的幅度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二,第一批受惠的农产品计有十八种,果真如此,则超过了中央1978年12月会议所认可的幅度。不过,大约十年以后,农业部和统计局联合起来对这时的提价之举作了更详细的调查。结论是提高价格的幅度大体为百分之十八。这一项调查还开列了主要产品的提价幅度:
粮食,百分之二十。油料,百分之二十三。棉花,百分之十五。甘蔗,百分之二十。甜菜,百分之二十五。大麻,百分之二十点三。柑桔,百分之二十六点三。蚕茧,百分之二十点三。蜂蜜,百分之八点二。
猪的运气比蜜蜂和蚕好些,一头一百公斤的毛猪原来只能卖九十八元九角二分,现在则可卖到一百二十五元零六分。
母鸡则更加幸运,因为鸡蛋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最有福气的是羊和牛。羊肉价格提高了至少百分之三十五,而羊绒则提价百分之四十五点一;牛肉的提价幅度高居榜首,为百分之六十。
上一次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为1962年。所以今天乡下二十来岁的青年,根本就不会知道还有提价这回事,尤其不会知道他们手里的东西原来能值更多的钱。二百多官员在一天里一举手,八亿公社社员的收入就在这一年里大约增加了一百零八亿元。当时农产品的出卖所得在他们的全部收入中占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份额,此中又有大约百分之七十出自粮食。这就可以想见,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针,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利益上均给予农民极大的震动。因为他们迄今为止所接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告诉他们如何压制自己内心深处的发财梦想,以及如何为国家作出贡献。他们在人民公社二十多年所做的一切,都具有爱国的性质,诸如“爱国粮”、“爱国棉”、“爱国猪”、“爱国菜”云云。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等于是公开承认他们的产品与金钱的直接关联。这就牵涉到当时农村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农民的劳动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净化,还是为了物质利益?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步一回头(6)
也许是出于这样一种理由,大多数评论者都说此举是一种划时代的变革,其实这也是一种过分的夸张。提高价格与共产党以往的方针来比较,虽然可以说是皇恩浩荡之举,但是平心而论,却并没有在农业方面开辟出新的道路。就制度方面的含义来说,即便它是了不起的一步,也仍然因循着统购统销的既定道路。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没有遭到任何方面的反对,这与“包产到户”所遇到的激烈对抗形成鲜明对照。看来,至少在这一点上,当时我们的国家宁愿以数百亿元来买得旧体制的稳定,而不愿主动采取超越常规的举动。
这中间的含义,一定要和政府奉行了二十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联系起来,才能使人理解。按照既成的制度,农民劳动所得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来控制的。政府一旦规定所需农产品的品种数量及价格,农民即须遵守,无论收成丰歉,都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倘若农民余粮不足,则应以自家预备的口粮先行上缴,然后政府再酌情以国库陈粮返销,补充农家食用。政府将乡下购得的粮食运至城里出售,购买者亦须依照政府规定之数量和价格,同样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这种制度被叫作“统购统销”,其建立,当在1953年的10月。在此之前,农产品营销当中有相当部分由私商操作。从这时起,私商被陆续宣布为非法,而由中央及地方的政府接管农产品的营销。这种管制先是在粮食方面进行,然后是油料、棉花、生猪、烤烟、茶叶之类,到1957年,又包括所有品种的水果和中药。又过了大约三年,这种制度最后完善起来。那正是我们的国家坠入大饥荒的时候,对于农产品的管制达到了最严厉的程度。粮棉油除政府所辖商业部门来经营之外,其他营销者哪怕只交易一斤一两也属非法,这叫做“一类物资”,是为统购;其余农产品大体属于“二类”,为派购。名义上,“派购”产品在交足国家计划征购部分后方可上市,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因农业生产能力极低,而国家的征购数额又极为庞大,所以农民在把自己的收获呈缴国家仓库之后,所余无几,所谓“剩余上市”一说,其实有名无实。所以,虽然名义上统购和派购的产品为二十种,但实际上由国家控制的农产品可以多至二百三十多种,几乎囊括了农民在土地上的全部收获。
对于政府来说,这种制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购买农产品的价格总是低于市场的价格。所以,虽然农业本身税率极低,但是农产品之强制性的低价收购,与工业品之高额售价间的差额,是对于政府的一种补偿。而且,这种差额的日益扩大,可以令政府以隐蔽的方式将财富从乡下集中到城里,为其工业化目标提供资金方面的积累。其具体的步骤,是使城里人获得低价的衣食供给以及低价的工业原料。如此,则又可以在工厂里面实行低工资和低成本的制度,来提高工业的利润和积累。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学家将这种制度所带来的隐蔽价值公开出来,说它大约有六千亿元。这大致相当于同一时期政府用在工业上的投资。
这种制度的秘密一旦大白于天下,其不合理的地方也就暴露无疑。问题在于,它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实行当中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公社本身为生产的组织,又是分配的组织。农民的劳动所得全归公社,个人不能直接占有,就如同他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劳动一样。所以,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保证农民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得以长期进行,而且也可以保证农民无法以减少生产的办法来表达不满。但是,这种制度却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中追求劳动所得的天性。农民利益的被剥夺,造就着农村中广泛的消极怠工以及对土地的不负责任,虽有种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亦不能扭转此种每况愈下的局面。
现在,政府再一次提高收购价格,客观效果是使隐蔽的差额大大缩小,但却并没有对制度本身的弊端加以纠正。比如这种差额在1952年,也即实行统购政策之前的一年,为六十六亿元,到了1978年就多至三百三十七亿元。1979年的提高价格,使其在当年就减少至二百多亿元。如果农民知道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个地方叫做国际市场,那里也有粮食的交换,并且有能力把自己的小麦送到那里去,则他们换回的食盐可以多百分之八十八点六、白糖多百分之五十三、火柴多百分之四十七、化肥多百分之二十二、白布多百分之十一点四、煤油多百分之二。可惜他们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小麦弄到那里去。所以,他们只以为政府在这一年里让他们多得到一百零八亿元的好处,却不知道,政府其实只是从他们的手里少拿走了一百零八亿元。
一步一回头(7)
新一代领导人当然深悉此种制度的奥妙,所以他们面临着历史上的一个大难题:既需不断地弥合这个制度的缺陷,又不能彻底地改变制度本身。此后几年,他们不得不一再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又不能取消城里人所享受的低价食品,以至令提价的方针成为政府财政上的一大负荷。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方针已经无法继续。就制度而言,由政府决定价格的方针本身就埋藏着失败之因,倘若不能最终依靠市场的力量,则政府无论怎样殚精竭虑和让利于民,也断无成功的可能。
12月23日的晚上,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从收音机里知道了邓小平的打算。记者们纷纷跑到街上去收集鼓舞人心的消息。一位记者写道:“23日晚上,广播公报的声音响彻家家户户。”另外一位说:“24日早上,刊载公报的报纸在街头迅速销售一空。”新华社的消息里特别提到,会议已经号召中国人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对于中国来说,否定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重大变故,但是,震动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小。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不加任何思索的状态下,张开双臂接受任何变化。新中国里出生的人合起来差不多已有六亿,这时候全都不满三十岁,略大一点儿的都知道“变天”的概念并非只有气象台的预报员才用得上。只要想想在他们长大成人的这些岁月里面中国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对这种心理感到奇怪。五十年代初期将资本家的工商产业剥夺过来,几十万资本家都成为穷光蛋也不过为一夜间的事,现在的青年那时候还穿着开裆裤呢;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是合作化,他们就看到他们的父辈怎样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的土地充了公;十来岁就看到了“反右派”,几十万知识分子的“百花齐放”,一下子全都成了“大毒草”。这些都没有令他们有一点点惊讶。到了他们上中学的年龄,周围就更加热闹,毛主席的理论层出不穷,一会儿“天下大乱,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一会儿“亡我之心不死”,一会儿“要关心国家大事”,一会儿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会儿“走资派还在走”,一会儿“安定团结”……古代大诗人苏东坡将人世间的种种悲欢离合,用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加以描述,半是忧伤半是潇洒地说“此事古难全”。今天的中国人则用月亮来形容党的政策,说是“初一、十五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