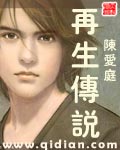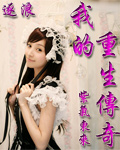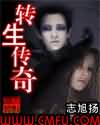��ͽ����-��3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ڰ������صĹ�����轲����ǿ������ص���Ȼ������������������������ʱ���ij��ڣ�����������������������á��ڰ�ͽ��֮ǰ��Լ����˹�����ߵ¡�ɳ�ˣ�˹̹���¡�ղ˹����ɭ���ǵ�������ʩ��������Ҷ��������ù�������¡������ǰ���ʩ�������������µ�ڹ�ͣ������˰�ͽ������Ȥ���ڰ���ʩ����İ汾�У��������ص��������Ȳ���ˮ��֮�ϣ�Ҳ����ˮ��֮�£�ֻ���������ܽ�����ڴ�����ʽ�ϵij�ͻ�������ھ���������ϵĿ�����������ͳһ�����簲ͽ��Ϸ���һ���ֵ��ճ�ʱд�������������֪�����鵽����ʲô���ģ�/��ô�͵�����ȥ��������ĭ�ɣ���������µ����˹������������İ������أ�������ѡ����ǿ������㣬�������Ǹ�������С�����֣�����ͬ����ĸ�ֵܣ�������˼���������Ӵ������۵ġ�����֮�����Ĺ����Ѿ�����ٹ̡����������ע�˰�ͽ����ȫ�����������������ͽ��ʵ��������������������������������˹����������������������д���Լ����Լ���������Լ��ĸ��顣����˵����ͽ��Ϊ���絶�ʵİ������ش��������̨�����������е���̨����ˣ����������غ����㡷�ѹ��ϵ����ʫ������λ�ִ��������ҵĻعˡ���˼�����������ؽ��Ϊһ�塣
�����ھ��У����ǿ����ڰ������غͺ����������ҵ�28�갲ͽ����Ӱ�ӣ����������λͬ����ĸ�����ã������õ���������ͣ�غ����ţ������������е���һ�롣�����������ر�����Ҳ���Ǿ������棬������ȴ���Լ�������������̵���ʶ�����ⲿ���Ŀ�ʼ���֣���������Լ�����Ϊһ��������˵��Ȼ���������ˡ��������˵�����dz�����Լ���˭�Ļ���������һ���棬��������ȴ��Ϊ�Լ���˫���Ը�е����壬����������û����ʶ���Լ���˫���Ը���ͬ����ĸ�ĸ��ȴ��Ȼ��һ������Ů�Ի������ˣ���������һ������̫������ζ��Ů�ˡ��ڰ�ͽ����19����30�������������Ϸ���С˵�У����˹������������ֵ��͵��Ը��ͻ���������㺣����������˵���������������˵ļ�ǿ������η�壬����һ�����㣬/�������ӿ�������˹��е�������˼�롣�����ⲿ���Ŀ�ʼ���֣�������һ���������ɵĸ����������Ȳ���������������飬������ն�������ػؾ�������
�������ҵ�������һ��ǿ�ҵĿ�����/����ʹ����ǰ��������һ���������͵Ŀ�����������Ů��������Ȼ�Ѿ���Խ�������Ա𣬶�����ij�ֲ�ȷ���������Ѱ�ǰ��������Ը�������������Ԫ�ء��ͺ���һ�����������ܹ����������������������ͻ�����ԣ������Dz��ò����ϣ����Ȳ������⡢Ҳ���������������ƵĿ�����������һ����ֶ����ҵ��ˣ�/���ż�ʹ�����Լ���������Ķ�������
��������������һ��ͬʱ������ˮ�к�½�ϵ������ˣ�����Ը�߳����ŵ���̲�ϣ�ȥ������ƽ���ĺ��������ʱ����¹⣬Ҳ��Ը�������Ƶļ�������ǽ������İ�ͽ����Ʒ�У����Ȳ��ǵ�һ����Ҳ�������һ������������˶��ĵĽ�ɫ���Ӱ���������һ��ɫ��1837���Ԣ�Թ��¡������㡷���ٵ�������1858��ġ���������Ů���������ǿ�����һ��ֱ�ӹᴩ�����е������������������������ǿ�����Щ��ɫ�뺺˹������˹�ٰ�����ͽ��������ϵ��������һ���ж������ź�������������㴩������ӿ�ĺ������ʵ�ϣ�������һ���У���ͽ������һ��������ˮ�Ŀ��ˣ����dz�ϲ����Ӿ���������ڵ����ǹ���ĺ�̲�ϣ����������ڴ����ҵ���һ�����ҡ�Ҳ�������ڰ������ǵ�˹�Ƕ��ͱ�˾��˹��̲�����Ǹ籾�����۵�����˹�ٸ�ɳ̲���Ƿ���ij�ϫ���������鲻�Խ���Ͷ���ڲ���֮�У���������˵��������ÿ���Լ��Ӻ����и�������ʱ������һ�������ĸо������ǣ�����Դ���һ����ȫ��ͬ�ĽǶ�ȥ������ǰ�����硣1859��8�£���ͽ������˹�Ƕ��������ڲ����л��������������ں����߶��磬�ھ���������һ�����������泩������֮�������ռ���д�������Ǿ���һ��ˮ½���ܵ����У�һ����ˮ�У�һ����½�ϡ���
�����Ͱ�ͽ��һ������������Ҳ��ˮ�к͵���֮�侭����ĥ�£��ھ��κ������������������Ů�����������ı��ԣ���Ϊ�������������ĵ�һ��վ�������ں�ˮ��½�صĽ���㡣��һ�죬���ĸ�ĸ���ڳ���ʱ�ֳ������㣬����ĸ����³��������䣬���ǣ���ɳ̲��ͣ����һ���ƴ��������˰������ء���������ĸ����˵��������ӵij���Ԥʾ����������һ�������ĺ�Ů����������ѪҺ�У�������ˮ��������ԭʼ����������ɡ���һ���棬�������и�Ů֯�����������˵ȴû���������ջ��������ԣ���ˮ��������������������Ȼ���Ա㿪ʼ�������������ս���ڸ��ĵ�һ�������һ�λ�������г�Ĺ����������У���˵����ɽë�ɭ�֡����䡢��Ů���ԵѺͽ��õ�����������Ҳ���ǵ�����̨���������С��ɫ������Χ���Ű������ص�������������ɺ�ͬ����ĸ�ĺ��������Ƕ�����ͼ���������еİ������ͬʱ����̨�������Ϊ���ҵĺ������������Dz����Ĵ����������������ŭ��ͺ����˻�У�������һ�ж�Ԥʾ��һ����ǿ׳�����㼴�����֣������ģ���Ϊ�������ع�����һ��Ӣ����ʿ��������ϲ����������������е�Ը���Ͱ������롣
�����������뿴����
һ������ͬ����ˣ�2��
�������صı������������ڴ�ѡ��������������Լ����ߡ�������������ͬ����ĸ֮�ֵ�ǰһ�죬����������ʧ�������֮�С��ڴ��У���������������������Ϊ��������һ��ħ�ð�Ĺ���á����Բ����ɶ�Ħ������ʯ���͵����������Ӻ��ʻ�������װ�������������β������һ��ľ��ǹ���Ĵ��ţ�ͨ������Ĺ���������������������ۡ����㻹���������ϣ�������˸��ָ�����˿��;�Ө���Ĵ���ʯ�������ǵ�Ȼ֪���������ף�ⳡΰ��ĺ���֮�����ܿ죬���ǵİ��������˶�����������ز��ñ��Ϊ3�����ӵ�ĸ�ף�����������һ���Դ�½������˫�����Ե��ˣ�������Զ���ֵ�������ȥ��ֱ�������е����һ�졣���ǣ������������ȴ���������ֻ������ݵ����ԣ����ʹ�������ص�δ��Ҳ������������ȫ����Ĵ��ڷ�ʽ��
�����������������鲻�Խ���������Щԭ���Ѿ������Ժ�����顣���е�������һ���ޱ�ǿ�ҵĿ��������ԣ��������ǿ�ʼ�������ļ�ͥ�Լ����Ǵ�δı�������ŵ�ʱ�����������Ƶ����������ֳ��ȵĿ��������Ŀ�������ǿ�ң��������ص�Ψһѡ����ǻص����������Լ��ļң�����½���ϣ�����һ�ο������������Լ�������һ�С������ڰ������ص����У��κ������������ܰ��������������ݵ�����������һ����˹������˹�ٰ�����ͽ����Ʒ�����౯��ɫ����Ů���˹�һ�����������ر�����Ϊ��Զ�ҿɹ���ˡ������еĺ���ʹ��Ҳ��˶���Զ���������е�ʱ�ա�����ת˲��7������൱����½���ϵ�50�ꡣ���ܶ����е��������磬�����㻹����������½���ϴ�1��Сʱ������ȥ�������ʱ����ӵ�е����磬�������������ʱ����ȴ���֣�ĸ����³���Ѿ���������������Ҳ����һ�����ˣ���һ�����ӿ�����С�����֣����ľ��Լ���һ��������������ͬ����ĸ�İ��ˡ���ʱ�˿̣��������ز���ʶ���Լ��Լ�ͥ���õ�Į�ӣ����б����������ϵۣ�������һ��������ں����ʵ�����ͬ����ڣ������ܵõ���ˡ��
���������ڰ������صĹ�������Զû����������Ϊ���������������Լ������ԡ�����Ψһ��·���Ǽ������Լ���·��������������Ը��Ů�ˡ�������������Ů���Ը��ͬ����ĸ֮��һ�����������յ�����ֻ�������������ĵط���ȥѰ���Լ������Ѱ���Լ��Ĺ��ޡ���ԭ���Ұɣ��ϵ�Ү�գ������Ұɣ������������ش����غ����ţ����Ѿ����������ϣ�����»ص������Լ��Ĵ���ȥ�����ǣ�����������ʯ�е����ˣ�����������ȥ�����������Լ������Ĵ�����������֮�������������������������Ľ��磬���ڴ���ͬ�廨�����������˵ı߽磬����һ�д���ͬ������
�����ⲿ���������غ����㡷�Ȳ���ɯʿ����ʽ��Ϸ�磬Ҳ����ϯ��ʽ��Ϸ�磬�����ڵ�2Ļ�У�������ʱ����ֱ���Թ���50�꣬ʮ�����½�ɫͻȻ��������̨�ϣ����ߵ������ַ��ƺ��Եúܴ�����������Щ�����������ֵİ�ͽ��������ʱ����ռ��Ϸ�Ծ�����Ǵ�Ϸ��ĽǶ���������ȷʵ����һ���dz���̵����⡣��Ϊ��������ϵİ��Ŷ��ڱ�����˵�����ݺ���Ա��ȷ��е��ƿ�ʩ�����ǣ���������ǽ�����۹��������ⲿϷ��Ļ�������Ȼ��һ���dz���ɫ����ѧ����������Ϸ����д��һ����������������ļ�ǿŮ�ˣ�������ʱ����������һ�����ε���β����������ͽ���ְ�����˫��������������һ��ͯ�����¡�С���㡷���С������������ϵ������������ǶԹ������������������ⲿϷ�綼����������ĵ�λ����ij�������ϣ��ⲿϷ�绹�����������ŵ��ִ���Ϣ���������˺ܶ��ᳫ��Ů��ŵ��Դǣ����磺��ÿһ��Ů�˵�˼�룬���DZ��������������ϵ���ӥ�����������˵�ѵ�����������ǵ���־ȥ���������ʵ�ϣ��ⲿϷ�粻ֻ������һ������Ů�˶Ա��Ե�����ѪҺ�п���Ļ��桱����Ҳ��ʾ�˰�ȫ������֮��ļ��ѵ��������һ���˵���Ӧ��ѡ������ȹ̵Ĵ�أ�������������������������������أ�
�����ⲿϷ��ĵڶ����ر���Ȥ���������ͽ����������������Ů�Ի������ˡ�����Ҳ���ǰ�������ͬ����ĸ�ĸ�纣����������˴���û����������������ص�������������ǰ��Ļ֮��ͽ���Ͱ��Լ���ע���������Ľ���ת�Ƶ������������ϣ�����Ѫ�����졢�����յ������š������ڹ����ϵ�ת�䡪���������������˵���ǿ��Ů�ˡ�����ͬ���ֳ����ڶ���֮���С˵��ֻ��һ�������֡��ֻ������һ�εķ�ʽ�����ˣ���������Ъ˹�����ζ�������Ȿ��Ŀ�ͷ������ͬ�����Լ�������һ�������������鹹�������˹�ٰ������档�����С˵���м䲿�֣���ͽ��ͬ����ʱ���ϲ�ȡ�˿�Խ��ʮ����ַ��������˹��Ľ�ɫ�ӿ���˹�ٰ�����ת�Ƶ�һ����ǿ��Ů�ˣ�����ð�ͽ�������͵Ľ�ɫ���ڰ��ס������µĽ��������ڿ˷�һ�м������裬ȥ�����ǵ����롣
����������
һ������ͬ����ˣ�3��
�ⲿͬʱ�漰���Խ�ɫ��Ů�Խ�ɫ��Ϸ�磬��Ȼ�ھ����ϹŹ����棬���ڰ�ͽ����19����30�����ѧ��Ʒ�У�ȴ��һ������ڹ�˼���漫Ϊ����Ľ��������������Ϻ��Է�����˱�����������д���ڡ��������غ����㡷�У������ô�����Ϸ��ڶ����ֿ�ͷ�Ĺ���ͻ����ǿ������һ�㡣�ڹ����У��������ȿ�������12���ͷ�Ӣ����һ��ׯ�Ļ��������棬����������Ů���������졣������Ů���У�һ�����Ըš���������ζ������Ů���ϣ�һ��������������Ů��Ŀ��ף�ǰ��Ը��Ϊ���ɸ����κδ��ۣ����������ϲ��ƽ�Ȱ��ݵ������������������������е���ں�������������Ŀ��ֻ�������ö�����ʶ����������˫���Ը��еĺ������⣺���������ͬʱ�����������Ա�����أ���������������Ԥʾ����ȫ��ͬ�ķ�չ�������в�������ʾ����������Ϊ��һ���ˣ����������ڵ��Լ������簲ͽ�����ⲿϷ��������д���������ʾ��һ���������˵ؿ�������ӵ���Լ�û�еĶ�������һ����δ֪�Ĵ��ڵ�ǿ��Ը������ͨ���ڡ��������غ����㡷�����������Ů���ϺͿ���С���£���ͽ��Ϊ����ָ������һ���˽����˺�Ů��˫�Ա��ʵ�;����
�����������ְ������Ա�Ļ���Ҫ�ؽ��Ϊһ�塪������ij�����������ͬʱӵ��������ֳ���ٵĸ��壬Ҳ������ν�������ˡ�������˫�Ի����ͬ��Ĺ۵㣬�����ݵ�Զ��ʱ�ڡ��ݹ�������������ʷ���������ִ���ͬ���˵ĸ�����������һֱ��Ϊһ�����Ա���Խ�ɫ�йص���Ϸ���ںͷ�չ�š���������ɯʿ���Ǻ�Ī���ص���Ʒ����1790�굽1840���ڼ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