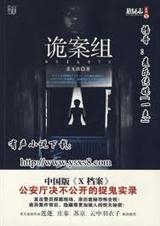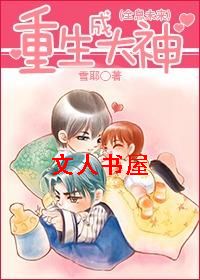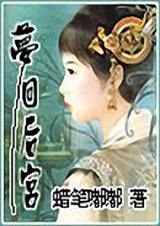故纸眉批(全本)-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糟的一点。”三年后,《国闻周报》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
强大的现代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相当广泛的公众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国民党政府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只知道控制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为的是维护“*”的利益,而不信任民众运动和个人的首创精神,所以它被民众所“厌弃”并最终走向衰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到底,蒋介石及国民党一直就面临权力来源的问题。无论是国民党政权里的众多官僚,还是作为“党魁”的蒋介石本人,他们的权力都不是合法得来的。他们的权力可能是经过战争抢来的,也可能是经过行贿上司买来的,还可能是通过尔虞我诈骗来的,当然更有可能是通过“做了女婿换来的”……但是,就是没有经过真真正正的选举选出来的。没有经过真正民众选票的授权,权力的来路就是不正当的。行使来路不正的权力,类似于小偷使用偷来的器物,总不能理直气壮。从这个意义上讲,承担训政之责的政府和它的官僚们是心虚的。所以他们不敢相信民众的群体活动——只要这民众不是他们组织的,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他们就害怕,他们就要禁止。这里面还暗含着这样一个思路:若不经政府组织的民众群体活动能进行得很好,不但没危害社会,反而大大地造福于社会,那么,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民众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而这正是训政政府及其官僚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民众自治能力的展示恰恰瓦解了训政的基础——须知,民众“愚昧”才需要训政,既然民众已经有足够的自治能力,你为什么不“还政于民”?还“训政”个啥?这样的提问对训政政府来说当然是有着致命的打击的;反过来,若未经政府组织的民众群体活动没搞好,闹出了“乱子”,那也是执行训政之职的官僚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虽然证明了民众还不足以实行宪政,但这同时也说明政府没履行好“训导”之职,属于“训政不力”,管理“不到位”,“相关人士”说不定还要承担责任。所以,综合权衡,不让民众“参政议政”,不让民众进行群体活动,不给民众以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和证明自治能力的机会,便成了训政政府及其官僚们的最佳选择。
信任总是相互的,政府不相信它的民众,民众自然也就不满意这个政府。在宪政之下,公民批评政府是天然的权利;而在训政之下,这是不可以的。政府及其官僚们承担着“训导”国民之责,他们若被批评,那脸面何在?尊严何在?还怎么继续训导下去?更重要的是,这将导致“训导”者和被“训导”者间“师生关系”及相应的道德优越感的置换与错位。而这当然也是训政政府不能容忍的。所以,压制批评、打击不同声音便成了训政政府天经地义的选择。国民党政府对政治上的反对者、爱搞“批评报道”的新闻记者、*的学者和思想家,一律采用收买加暗杀的手段。此外,它还通过“党化新闻”,以“*”的名义操控舆论,在极力为“*”唱赞歌的同时打压那些不肯合作的媒体和文化人,强化党对新闻界的控制。
训政之路(5)
从1927年起,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依靠官方新闻网络,垄断新闻的发布权和评论权,控制全国的舆论,“阐明党义,宣扬国策”,另一方面还制定了许多新闻法规,钳制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在1929年至1934年间,国民党制定的与新闻有关的法规有《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出版法实施细则》、《宣传品审查标准》、《新闻检查标准》、《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自然,这些法规多属新闻“恶法”,专制*色彩极浓。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又制定了许多与新闻相关的法规,如《修正出版法细则》、《抗战时期报社通讯社申请登记及变更登记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修正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原告审查办法》等,1942年7月,国民党还借抗战之际公布了一个《国家总动员法》,其中规定:“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这样,就利用法规进一步钳制了新闻出版自由。
当然,国民党还实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随意扣押书报。1929年,国民党在各地设邮件检查所,实行邮电检查;1931年,在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重要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1934年又专门成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35年又成立了中央新闻检查处,一再强化它的出版审查制度。
按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是实现宪政的一个阶段,可到了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府这里,训政就成了拒绝实行*、拒绝给民众以自由和权利的借口。本来以为是通往宪政的一个路径,现在却成了宪政之路上的一个障碍,训政思想就这样走向了它当初预设目标的反面。
四
顾名思义,宪政就是用宪法来保障公民的个*利并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这是西方宪政的本义。可是,到了中国,在训政政府看来,宪法原有的人文内涵荡然无存,而它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得以突显。宪法成了训政者“训导”国民、凝聚国家力量的一种工具。在西方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产物的宪法和法律,在中国却成了集权主义者手中的一根大棒。挥舞着训政的大旗,高举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棒,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天天地走向了*,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20世纪30年代,由于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十分赞赏纳粹的组织及其活动方法。1935年,蒋介石就曾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蒋总统”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他希望通过法西斯主义来重建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他甚至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在日本军校度过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而日本、意大利、德国则实现了这种理想。所以,他也要把中国引到法西斯之路上去以实现他的社会理想。他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说:“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作出牺牲。”
训政之路(6)
显然,“新生活运动”的价值指向是保守的和反动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彪炳史册,就在于它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努力把个人从中国封建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则是一场被把个人的精神和思想拉回到传统、拉回到集体和政党的束缚中去的新的“愚民”运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高呼打倒孔家店,而对国民实施“训政”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则恢复了尊孔。在中国,尊孔向来都不是简单地尊重教育家孔子的意思。从“领袖”和“政客”嘴里出来的“尊孔”,潜台词其实是“尊我”,是要百姓无条件地放弃个*利,做“牺牲”,以尊重“领袖”、服从组织。
训政需要对国民进行“训导”,而训导就需要有“精神领袖”和“思想导师”。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全国人民实行“训政”,那么,作为国民党“党魁”的蒋介石便天然地成了全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导师”。“精神领袖”和“思想导师”都不是坏身份,有人想当“精神领袖”和“思想导师”也不能说就是坏事,但是,一个手握重权的现代执政党的“党魁”和国家领导人若再将“精神领袖”和“思想导师”的身份统统揽下,那就会有害无益。因为,“政教合一”必然导致权力的绝对膨胀,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
可惜,就像饕餮之徒一样,专制*者对权力也是从来都不知道节制的。主持“训政”的蒋介石既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就说明他已经认定了自己的“圣君”地位和国民的“愚民”身份。这也就陷入“训政”的根本悖谬之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的民众或许真的是“愚民”,但是不要忘了,那些自以为是“圣君”、有资格“训导”国民的人不但不会是真的“圣君”,而且往往是“暴君”,是*者。因为只有专制统治和“暴君”才会跟“愚民”配套。如果政治制度*,国家领袖开明,政策方针得体,那么,“民生”有保障,“民权”深入人心,国民的智力水平当然也会跟进,“愚民”和“刁民”自会大幅减少,而身心健全的公民必然成了民众的主流。所以,总根本上讲,训政思想看似是在民众“愚昧”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可实际上,恰恰是政府的“训政”导致了“愚民”而非“愚民”要求了政府的“训政”。正因如此,训政的实践便总是要导致政治专制和领袖*,而绝对不会是国民参政议政水平的极大提高和和社会*进程的飞速发展。
训政,是一条歧路,通过它,永远无法抵达宪政的彼岸。
五
就像陈炯明早在1922年就对孙中山的训政之说提出批评一样,中国共产党也对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府以“训政”为借口不给人民以自由和*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尤其可贵的是,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理论上指出了以训政为由行专制之实的危害,而且还通过解放区的*实践证明了训政之说的荒谬之处。
中国百姓的文化水平低,不能很好地运用选举权,所以不能对他们实行*,只能训政。这是当年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持的论调。针对这种论调,1946年1月24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的文章进行了批评。这篇文章写道——
训政之路(7)
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选举。如去年12月26日的《和平日报》社论就可作为代表,那社论里说:“……共产党拿‘*’和‘不记名投票’来欺骗人民。谁不知道,中国人民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即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的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样的政府只能叫‘魔术’政府,不能叫‘*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就是‘*’,简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种说法,不仅诬蔑了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选举,还应该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不问可知。
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无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实行*选举的经验便是明证。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解放区是怎样选举的吧: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联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这是很久以前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又曾有过不断的改进和新的创造。过去的办法是由候选人坐在晒场上,每人背后摆一个罐或碗,因事不能到会的候选人仍然给他们空出位子,位子后摆上碗,每只碗上都贴着候选人的名字,选民每人按应选出的人数发豆子数粒,于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选的那个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监选人向大家说明每只碗所代表的候选人……这种方法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