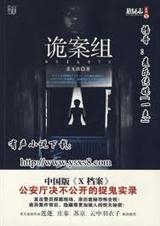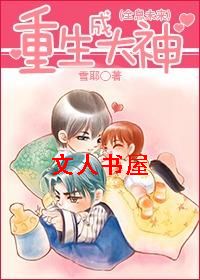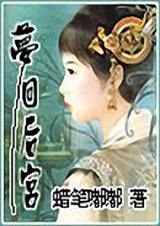故纸眉批(全本)-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宣宗统治的十年加上他老爸仁宗统治的一年被成为“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可是,作为叔叔的朱高煦不知进退,身陷囚室仍然不服气。登基三年后,宣宗带着内侍前去囚室探望自己的叔叔,身为皇帝的侄子对身为囚徒的叔叔嘘寒问暖了一番。这本来是件好事,说明宣宗还没有忘记叔侄亲情。不料,朱高煦却在宣宗起身离开之际使了个绊子——用脚将宣宗勾倒。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宣宗朱瞻基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缸上积炭燃烧,铜缸被烧化了,朱高煦在缸里被活活烧死,尸骨无存。朱高煦的几个儿子也一并被杀死。后世的学者始终弄不明白朱高煦在这个时候还给皇帝使绊子是出于何种心理,更不明白以仁厚著称的宣宗为何对这个绊子如此愤怒——自己的叔叔起兵造反都能饶他不死,为何对他使绊子气愤至极? 。 想看书来
一个绊子引发的血案(2)
我的解读是:历史本来就有它的吊诡之处,它不会按照常人的思维逻辑去按部就班地发展。一个绊子所引起的帝王愤怒,有时就是比千军万马的厮杀还激烈。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就是历史,至少是历史中的一部分。
“剃发易服”与明末思想家
明朝从嘉靖皇帝炼丹到崇祯皇帝上吊的这段历史,读起来实在叫人憋气:皇帝不像皇帝,朝政不像朝政,太监专权,民不聊生。虽然偶尔也出来几个忠臣(像海瑞、袁崇焕及东林党诸位君子),可这些“好人”都郁郁不得志,有的干脆就被残酷地杀害了。我就想,这样的朝廷如果还不灭亡,那简直是天理难容!可是,等我读到明末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有关传记时,又产生了一个困惑:既然晚明如此腐朽、如此不堪,那么这三位思想家为何还要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难道他们还深深地留恋那个腐朽的明朝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岂不是有点“迂”,有点“笨”?
继续阅读,答案逐渐浮出了水面:问题就出在清军入关后提出的“剃发易服”令上。
在清军入关之初,因为晚明政治*,不得民心,北方人几乎没怎么抵抗。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攻占南京后,清廷发布“剃发易服”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这道命令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对不剃发者一律“杀无赦。”人们将此概括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同时还不准汉人继续穿“汉服”,而必须改穿满族服装。
“剃发易服”令的发布遭到了当时汉人的普遍抵制。在今人眼里,剃不剃头、留不留辫子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可在当时,这却是一件关乎“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大事!多尔衮说实行剃发令的目的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实际上,满人先就把这个问题给“政治化”了,他们把是否“剃头易服”看成了是否归顺的象征,“剃头易服”者为顺民,反之则为逆民。可在汉人眼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能说剃就剃?而且,我们的“汉服”也穿了一千多年了,这文化传统怎么能说断就断?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所以,自清廷“剃发易服”令发布之后,汉族地区人心大哗,纷纷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清廷随之进行了残酷*。清军制造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惨剧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究其实质,清廷推行“剃发易服”令直接触动了汉人的文化认同。头式和服装是汉人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也是最直接的文化符号。清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在改朝换代时干涉过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他们要抢的是江山,根本没必要对普通百姓的头发和服饰动手动脚。骁勇的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当然也与汉人迥异,可他们也听任汉人按原来的方式过自己的日子,并未强迫汉人更改发式和服装。与之相比,清廷发布的“剃发易服”令就显得十分粗暴。更重要的是,“剃发易服”令中还暗示着灭亡汉人文化的政治企图。如果接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迫选择,就意味着汉人不但接受了“亡国”的现实,还要默认即将到来的“灭种”的可能。正因如此,“剃发易服”令才在江南遭到了强烈的抵抗,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位思想家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参与“反清复明”运动的。他们之所以参与“反清复明”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留恋腐朽的晚明朝廷,而是表明了他们对清朝初期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的一种反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个绊子引发的血案(3)
“反清复明”的活动最后失败了,但是,我们必须说,“反清复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民本”思想的成熟和飞跃。经历过明清交替的乱世之后,黄宗羲猛烈地抨击“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他明确指出,君主的独断专行是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他深知封建帝制会使中国走进死胡同,所以期盼中国发展成一个由文化精英主持的*社会,从而变封建帝制为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为天下苍生谋福祉远比为一个没落的朝廷殉道要重要得多。黄宗羲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把“万民之忧乐”置于“一姓之兴亡”之上,以天下苍生的视角而不是以帝王、皇族的视角来考察天下的“治”与“乱”,这显然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与黄宗羲对“苍生福祉”的强调相比,顾炎武的思想就更是对君臣伦理*裸的颠覆。他在亡国之余,痛定思痛,发现封建的“君臣之伦”有着极大的欺骗性。他在《日知录》中说:“君臣之分,所系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接着,他又将“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而“亡天下”则是指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被严重破坏,致使民不聊生,民族文化濒临崩溃。因为“亡国”与“亡天下”不同,所以人们对“保国”与“保天下”的态度也应有别。“保国”实际上是在保卫某个封建王朝,责任应该由统治集团承担,即“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普通百姓不必关心;“保天下”是要保卫本民族的民生福祉和文化传承,那就应该每个人都承担责任,即“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的这个思想,后来被梁启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成了今人耳熟能详的句子。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人们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虽也认同,但不会有切肤之痛。如果了解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就会有石破天惊之感——原来这里面饱含着顾炎武的人文情怀和批判精神,堪称思想瑰宝。
王夫之的境界虽在总体上不如顾炎武和黄宗羲高,但他也同样提出了“民族大义”应高于“君臣伦理”的思想。总之,明末的三大思想家都从清廷推行“剃发易服”令的过程中看到了百姓苍生所遭受的苦难。他们参加“反清复明”运动,表面上看是在为明朝唱一曲挽歌,可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深处另有所属。他们早已跳出了“君臣之伦”的窠臼,他们胸怀天下,心系苍生,那种为民请命的精神境界是漆黑历史岁月中的一盏灯火,一直闪烁到今天。
晋商浮沉与票号盛衰
最近几年,以晋商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开始出现,2009年央视的“开年大戏”就是以晋商为题材的连续剧《走西口》。《走西口》里讲述的故事是从晚清开始的。其实,晋商发展的历史远比这要早。早在明代,晋商就以张家口为基地,经过塞北,同东北的满族政权沟通物资,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从那时起,晋商就与满族政权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军入关后,认为“山东是粮运之道,山西是商贾之途,急宜招抚二者……”于是就对晋商网开一面,采取了招抚扶持的政策,这样,晋商和清政府官员之间的往来日益增多,二者迅速勾结在一起。可以说,晋商之所以能坐大,是与其从发展之初就有“官方背景”密不可分的。以日升昌票号为例,它的开封分号的经理,结交开封抚台为兄弟,一下子就把河南全省的财政收入都吸引从日升昌“过局”。还有,对盐业,清政府一直是专控的,只允许两淮商人经营,晋商本没有盐业许可证,但是他们通过贿赂两淮商人,并在两淮商人缺钱时给予慷慨的借贷,一点点地控制了盐业的经营权。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好多。晋商和清政府官员的互相利用无疑是晋商迅速致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明乎此,我们便不难发现,晋商的繁荣和富庶有相当的成份是靠官商勾结的手段得来的。
晋商以“走西口”出名,这一方面归于山西人肯于吃苦、敢于闯荡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有地理环境逼迫的因素。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山西历来属边关地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来往密切,相对而言,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又受战事的影响,文化教育一直不怎么发达。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科考一直是山西人的弱项。刘红庆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屋顶下溜走梦中的平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晋剧中有不少描写为佳人所爱的才子最终考中状元的情节,估计那都不是发生在明清两朝的故事,或者不是山西人的故事。如若是,那也属于我们地方艺人画饼充饥式的*。因为在明清两代全国十八省的举子考试中,山西竟无一人得状元,这比中国姓张的从来没有一个作过皇帝还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这段话透露出的信息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山西省在明清两朝数百年间竟然没有出过一名状元,这和晋商在商业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多么不协调呀!
更可怕的是,在文化教育不发达的同时,晋中土地还不能为百姓提供足够的财富。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记载:“平遥县地贫瘠,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年间的《太谷县志》也对太谷县作了如下描述:“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读书科考不得,而土地又贫瘠,“丰年之谷”尚“不足供两月”,不得已之下,他们只好选择“走西口”。口外,有朝廷的边关驻军,口外,有游牧民族,他们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而口外,还有毛皮、呢绒等内地少有的物产,这些是富贵之家需要的紧俏货。于是,在口里和口外之间,在边关和内地之间,晋商走出了一条通往财富的路。他们冒风寒,历艰险,终于通过“走西口”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关外赚到的钱需要运回山西,在这个过程中,晋商又创建了“票号”。平遥第一家票号(也是全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建立于道光三年,即1823年(一说是在道光四年,即1824年)。在此之前,通过几代人的积累,晋商已经非常富有了,他们的一些大商号在山西设总号,在外地设分号,形成了连锁经营的商业格局,分号与总号、分号与分号以及商号与客户之间的大宗买卖所需的现银解运业务越来越多。这样的现银解运虽然可以雇镖局押运,可是镖局押运很费时间,保镖费用也很大,有时也并不十分安全,商业的发展已经需要一种更高级的金融业务来与之相适应了。而促成这种新的金融形式的殊荣就在落在了晋商雷履泰的身上。
雷履泰原来是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掌柜,西裕成颜料庄总号设在山西平遥,分号在北京。它是一家自产自销、产销兼营的颜料手工作坊。这个颜料庄在清嘉庆年间创立至道光年间已经开办了20多年,成为众多颜料庄中资力雄厚、规模较大的一家。当时山西的平遥、介休、祈县、太谷、榆次等县的商人,也在北京开设各种商店,每逢年终结帐,他们都要往山西老家捎去银两,一般都由镖局押运。这时,有人和北京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商议,不从北京往老家捎银两,而是将现银交给北京西裕成颜料庄,由雷履泰在北京写信给平遥,人们持雷履泰的信至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取现银,这样便省掉了雇保镖的费用。这样的事情起初不过是朋友之间的帮忙,后来要求汇兑的人越来越多,就有求兑者出一部分汇费作报酬。雷履泰感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