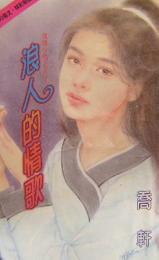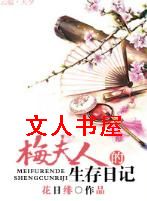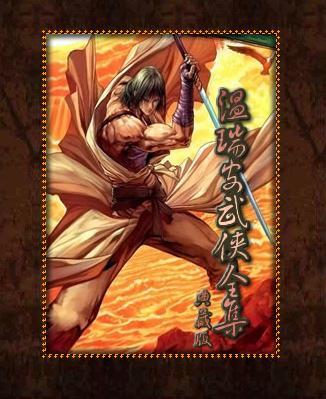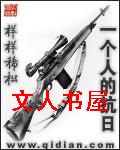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性恋在一般人眼中是一种异常的性倾向。说它异常只是说它有异于常人,并不等于说它是病。从弗洛伊德反对对同性恋的生理解释而强调它后天习得的性质起,到
年美国神经病学会正式将同性恋除名,认为它既然已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已经属于由社会来加以规范的事物而不属于神经病学的研究对象止,人们对于同性恋的研究已经深入到这一现象的各个方面。概括起来,关于同性恋现象的研究有下列各类:
关于
同性恋的历史的研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现代同性恋者争取
关于同性恋本身状况的研究,如他
自身权利的政治运动;
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们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行为规
范等,
关于同性恋形成原因的研究;
关于人们对同性
恋态度的研究,如男女两性是否对它持有不同的观点;
关
于同性恋者同其他人的关系的研究,如同丈夫、妻子、子女的关系等等。
我的这项研究旨在对北京男同性恋社群的状况做一基本描述,其中包括同性恋社群的主要活动方式和场所,同性恋的形成过程及原因,同性恋者的感情生活与性生活,以及他们的婚姻观与价值观,等等。研究在描述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试图对同性恋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某些特异之处进行分析,做出合理的解释。
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本应包括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两个部分,但由于笔者精力及调查线索的限制,只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
文献综述
关于同性恋历史的研究
)在《同性恋权利运动:
社会学者里卡塔
美国历史一个被忽略的领域》一文中回顾了以欧洲为源头的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史,将其概括为以下
从
个阶段:
年:在这个时期,只有零散的个人的尝试,试图
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为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权利作辩护;
数年间是城市男同性恋者“少数派群体意识”的觉醒时期;
年:同性恋者寻找身份认同的时期;
至
年:同性恋者对自己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慨爆发的时期;至
至
年:同性恋运动加强信息交流,注重教育领域的时期;
年代:将民权运动引向同
性恋运动的时期; 年: 开始出现大规模同性恋运动
的时期, 至 年: 同性恋运动与政府通过正式渠
道对话的时期。整个 年代以同性恋运动的联合与成功意识
告终(。里卡塔,年)
艾斯科弗()的研究认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批男性公民参军,女性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致使美国的性别分工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导致了战后的性革命。这一革命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人们已感觉到性规范与性行为之间存在着差异的情况下,金西博士对性规范的批判,以及同性恋者提出解放的要求,第二阶段是回潮期,其特征是在性别分工上鼓吹妇女留在家里或回到家里去,在性关系方面对同性恋实施制裁,及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然而在这个时期有一批知识分子坚持对性压抑的批判,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同性恋亚文化出现于各大城市之中,社会开始容忍同性恋者对性与性别的看法。(艾斯科弗,年)
海伯尔()等人在《粉红三角与黄星纳粹德国对性学的摧残及对同性恋者的迫害》一文中,揭露了纳粹暴行被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论文指出,许多早期的性学研究以及性学这一概念本身是德国犹太人首创的。希特勒摧毁了德国的性研究和性改革运动。在性科学研究的废墟上,纳粹建立起自己以反犹、反女权主义和反同性恋为特征的性意识形态。纳粹档案中存在着大量迫害同性恋者的证据。同性恋者被关进集中营,在囚徒的等级中被排在最底层(海伯尔,年)。劳特曼()的调查发现,纳粹集中营中共有一万名左右同性恋者,他们配带粉红色三角标志(犹太人配带黄星),地位很低,与其他囚徒隔离。与政治犯和犹太人相比,同性恋囚徒被派给的活更重,死亡率更高,幸存率和释放率更低,但其自杀率并不显著。(劳特曼,
年)
关于同性恋自身状况的研究
怀特姆()在对美国、危地马拉、巴西和菲律宾四国的比较研究中得出下列重要结论:
这些社会都
存在同性恋现象;
在这些社会中,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
比例十分接近并保持稳定;
社会规范既不能阻碍也并不助
只要存在一个足够大的人群,就会产生同
长同性恋倾向;
虽然所在的社会不同,同性恋者在行为兴趣
性恋亚文化;
所有的社会都会产生相似的性关
和职业选择上趋于一致;
系连续体,从男同性恋到女同性恋种类齐全。全文的结论为:同性恋不是由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产生的,而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性行为的一种基本形式。(怀特姆,
年)迪克森()以
位双性恋已婚男性为对象进行了比较研究,使两组对象在年龄、婚姻持续时间、社会经济地位上互相匹配。研究结果表明,在性满意程度和婚姻幸福程度上,两组间存在区别。首先,双性恋者经历性快感的频率显著高于异性恋者,(双性恋者每周次,异性恋者
位异性恋已婚男性和
次);其次,虽然两组对象的性满足程度和婚姻幸福程度都相当高,异性恋者的满足程度与幸福程度高于双性恋者这一事实具有统计的显著性。(迪克森,
年)
关于同性恋形成原因的研究范怀克(
,
)等人研究了同性恋、异性恋和双性恋的形成原因,发现在各种因素之中,早年性经验是决定因素,其次为性认同和家庭影响等。(范怀克,
年)这
一结论与某些人以家庭影响为性倾向主因的观点有所不同。西麦里()等人以
至
岁的同性恋者为对象,研究乱伦的经历对形成同性恋倾向的影响。他们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组,第一组为无乱伦经历者,第二组为有在核心家庭中乱伦经历者,第三组为有在扩大家庭中乱伦经历者。研究发现同性恋者中有乱伦经历的比例很大。其中男性多为同性乱伦(父与子、兄弟之间),女性多为异性乱伦(父与女、兄妹之间)。研究对象对核心家庭中的乱伦经历和异性乱伦经历多持否定态度,对同性乱伦和扩大家庭中的乱伦则多持肯定态度(。西麦里,
年)
关于对同性恋的态度的研究凯特()综合研究了
项已发表的研究报告,看男女两性在对同性恋态度上是否有区别。一般认为男性比女性对同性恋更反感。他发现在这
项研究中,样本越大的性别对态度区别的影响就越小;发表日期越晚的性别对态度区别的影响就越大。(凯特,
年)鲍曼(在
名成年异性恋者的研究表明,他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比许多同性恋者和立法者要宽容得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但不反对同性恋,反而赞成取消对同性恋的种种制裁措施。在研究对象中持上述态度的人具有下列特点:年轻、无宗教信仰或只是一般的基督徒而非少数教派的信徒,以及朋友中有同性恋者等等。(鲍曼,
年对
年)拉森()等人的研究则发现,对黑人种族歧视程度较低的人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也较宽容(。拉森,
年)
关于同性恋者家庭关系的研究沃夫()以
对结婚二年以上的双性恋者为对象,研究同性恋(双性恋)者作为丈夫的现象。研究发现此类婚姻双方满意程度较高,性生活活跃,丈夫对妻子说明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此类婚姻的满意程度还与下列因素呈正相关关系:
双方坦诚相见;
友谊;
性生活活跃;
婚前接受医生或心理医生的检查;
宽容的态度;
经济独立(。沃夫,
年)布朗芬()也以双性恋丈夫为题做过研究。他认为这种人并不少,但难以找到他们。他设法找到了
位此类对象,研究他们如何处理异性恋的公开形象与名声很坏的同性恋行为的矛盾,以及欺骗妻子与亲人这种做法的道德问题。研究发现这类研究对象多无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有些男性具有将同性恋和异性恋协调起来,使二者的冲突降到最低限度的能力。(布朗芬,
年)我们对北京男同性恋的研究发现与沃夫的发现形成鲜明对照,同布朗芬的结论倒有相似之处,下节将有详述。
费舍()研究了同性恋者与子女的关系。许多同性恋父母具有子女抚养权并非常担心会丧失这一权利。研究检验了以下三项假设:
子女会由于父母是同性恋者而蒙受侮辱;
子女会由于父母的同性恋倾向产生自身的性角色冲突;
同性恋的家庭环境不如异性恋家庭环境。研究结果否定了这些假设,反而发现同性恋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比一般亲子关系要好,但前提是告诉子女自己是同性恋者。原因在于同性恋者在工作居住等方面受到种种怀疑和歧视的情况下,更加需要子女及其朋友们的了解和支持。(费舍,
年)
基本事实
全景描述:次属群体内的行为方式
众所周知,广大异性恋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
)这两重生活和两种角色。前者如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中的角色;后者如社交生活和市场上买卖双方关系中的角色、医生病人关系中的角色等等。同性恋群体中的首属与次属的两重生活和两种角色与上述关系类似。在这个独特的亚文化群体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一些首属群体生活,扮演着其中的角色,如短期或长期的亲密同性恋伴侣生活,隐秘的同居生活等,而每个人又不同程度地卷入一些次属群体生活,即所谓“社会上的”生活,例如在同性恋的聚会地点与不熟悉的同性恋者聊天、喝酒,甚至发生偶然的性接触,双方互相不通告姓名地址,以后也不会再接触。用同性恋者的话来说,这属于“发泄完就走”一类的行为。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同性恋社群这两个方面的生活。我们认为,首属群体内的行为是比较纯粹的同性恋文化,更能揭示同性恋现象的本质,因此应当是我们研究的重心。
但由于研究是从次属群体行为开始的,也有必要对“社会上的”同性恋次属群体行为作一全面勾勒。
我们的调查对象有的经常出没于北京各同性恋活动场所。由于常到这种场所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自称为“我们社会上的”或“我们常到社会上走动的人”。还有些人不承认自己是“社会上的”,并对“社会上的”那些人的所做所为表示反感,但是这些人不否认自己有时也偶尔在社会上走动。例如,一位偶尔到社会上走动的
多岁的同性恋者说:“我不愿意在人前表露出这种意向。对那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街上招摇的人不喜欢。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觉得我们不够等级,我却觉得他们给我们这种人带来耻辱。他们有他们的等级观,我们有我们的等级观。我见到这样的人就躲得远远的,也不想了解他们。我觉得他们层次低,文化水平低,出身也比较低,俗里俗气的,我不喜欢他们。我认识的人比较正人君子
”但他又自嘲地加了一句,“也许是虚伪吧。”这位同性恋者还提到自己喜欢的一个伴侣,说“他不是社会上的人,他也不喜欢这些人。他不让我问他的姓名地址。他可能有大人物背景”。
由此看来,首先,在“社会上”(即同性恋活动的公共场所)发生的活动,只是同性恋活动的一部分。我们调查对象联系的其他同性恋者有很大一部分从来不在“社会上”走动。其次(但并非比第一点次要),到“社会上”活动的人所属的社会阶层也许不如那些不在“社会上”露面的人地位高。这一点有个很好的解释:因为地位高的人担心失去和能够失去的东西要多些,如名誉、优越的职业地位等。据我们的调查对象说,北京的同性恋文化群体中有不少名人,尤其在文艺界体育界中。他们的身份一旦暴露,则可能失去的东西就远比一个普通职工或无业青年要多。尽管属于同性恋群体的人在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上差异悬殊,他们却有一种独特的等级观与外面的世界(异性恋世界)形成对照。一位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说,“我们这样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从扫大街的到领导干部都有。在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
全北京究竟有多少经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据一位经常出入这种场所的调查对象说,全北京至少有
多个同性恋者他可以达到见面眼熟的程度,仅他居住的
区就有
多名。加上大量从不在社会上活动的同性恋者,人数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