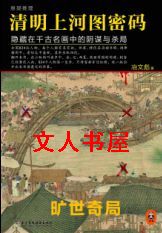清明上河图密码2: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一带几个村落总共有二百多户,多的得了七八十头猪,少的也有二三十头。主户里,田多的上户捉的猪若少了,要略亏一些,田少的下户则能赚一些。没田的客户则意外捞了一大笔。因而,有的人骂,有的人笑,有的连声咂嘴。几个村的里正、耆长中午聚到一起商议,这些猪的主人至今不见来寻猪,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猪踩坏了田地,依理也得赔,不过打起官司来,不知道要拖延多久,而且未见得能赔多少。有了这些猪,赚的不说,就算损,也损得不多。如今趁着没人来找,各家先把这些猪全都杀了,能卖的赶紧卖掉,卖不及的也赶紧藏起来,实在不成用盐腌了慢慢卖。至于田,各家赶紧补种,还来得及。
于是,各家各户都开始杀猪,猪叫声险些把村里的房子震塌。
清明上午,汴京西郊车鱼坊。
数百个鱼商聚在汴河上游岸边,看着太阳渐渐升高,一片焦躁叫骂声。
每天清早天不亮,鱼商们就在这里等候渔船。上游的鱼贩把鱼运到这里,卖给鱼行,鱼行再分卖给各个鱼商,鱼商趁早运进城去赶早市。然而今天,天已大亮,仍不见一只渔船来。
鱼商们把一个人紧紧围住,不停地催问,那个人不停地解释,但到处是叫嚷声,谁说了什么,谁都听不清。
这个人名叫蒋卫,是汴京鱼行主管,今年四十七岁,长得小眼扁嘴,头小身长,人都叫他“蒋鱼头”。他十来岁就在京城贩鱼,已经有三十来年,深得行首倚重,渔行的大小事,大半都是由他出头料理。
近一个月来,蒋鱼头已经被挫磨得肝肺都要燃着,但从没像今天这么糟乱。他嗓子几乎喊哑,却没人听。实在没法,只得用力扒开那群鱼商,骑上驴,逃脱鱼商们的叫嚷拉扯,加紧催驴,进城去找那个惹祸的事主——冯宝。
清明正午,东水门外。
梅船在虹桥下遇险时,祝德实刚走到香染街口。
他是京城炭行的行首,年近六十,中等身材,原先是瘦方脸,由于发福,早已变成了圆脸,颔下稀软一些胡须,样貌亲切,满脸和气。加之极善保养,面色丰润,看过去不到五十岁。
今天清明,几个商界老友约了个郊外酒会,要斗各家厨艺。祝德实让家人精意备办了四样秘制菜肴,排蒸荔枝腰子、莲花鸭、笋焙鹌子、糟脆筋,用一色官窑冰裂纹粉青瓷碟盛放。又挑了几样咸酸劝酒的精细果子,椒梅、香药藤花、砌香樱桃、姜丝梅,一起用彭家温州漆盒装好,让人先送了过去。又带了一套龙泉梅家茶具、几饼龙团胜雪御茶,及席间添换的衣衫巾帕,让两个随从阿铜、阿锡分别提着。
京城各行衣饰都有区别,今天不做生意,祝德实没有穿行服,只戴了顶东门汪家的黑宫纱襆头,穿了件刘皇亲彩帛铺的青绸春衫,系了条钮家的犀角腰带,脚上是季家云梯丝鞋铺的青缎绣履。
他看天气晴好,时候又尚早,想舒展筋骨,便不骑马,信步慢慢向城外走去。才走到香染街口,便见两个人急急走了过来,都穿着炭行的行服,黑绸襆头、黑绸袍,腰系黑绸绦。
一个瘦高,目光暗沉沉的,五十来岁,叫臧齐;另一个粗壮,嘴边一圈硬黑胡茬,三十来岁,叫吴蒙。两人都是大炭商,和祝德实一同主掌京城炭行。
吴蒙还没走近就嚷道:“祝伯,炭仍没送来!”
“哦?宫里的炭呢?没送去?”
“我的存货昨天已经淘腾尽了。拿什么来送宫里?”
“这可怎么好?我那里也没有剩的了,臧兄弟,你那里如何?”
臧齐不爱说话,沉着脸,只摇了摇头。
吴蒙气恨道:“我早说那姓谭的不能信!”
三人正在犯愁,忽听到有人唤道:“三位都在这里?让我好找。”
抬头一看,是内柴炭库的主簿吴黎,四十来岁,面色有些暗郁,穿着件青绸袍子,骑着匹青骢马,刚从东水门外进来。
三人忙一起叉手拜问:“吴主簿!”
吴黎并不下马,沉着脸:“你们倒是清闲,昨天让我候了一整天,没见着一块炭。今天一上午,仍不见人影儿。宫里头滚轱辘一样派人来催,说都要砍桌椅来烧水了。你们的炭看来不打算送了?”
“让吴主簿受累。宫里的炭我们哪里敢欠?只是各家炭场里真的没有存货了。您看臧、吴二位这一头的汗,他们两个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在为这事奔忙。您放心,等炭船一到,我们立刻给您运过去。”祝德实脸上赔着笑,心里却想:催起炭来似火,付起炭钱又如冰。宫里欠了两年多的炭钱至今还没见一文钱。
“又是这话?没有个准时准信,我怎么去回复?”
“我们也没法子,这两天又是寒食清明,水路堵得厉害,难免耽搁一两天。您看,最晚明天,就算炭船没来,我们也想办法把宫里的炭找齐。”
“明天?!你们真要逼宫里烧龙椅?”
“不敢,不敢。说两天,只是不敢把话说死。炭船今天应该就能来了。”
“天黑之前,若还见不到炭,就不是我来叨扰各位了。”
吴黎也不道别,沉着脸,喝马摇缰,径自向城里行去。
三人呆立片刻,祝德实问道:“那姓谭的没找见?”
吴蒙恨道:“若找见就好了!便没这些啰嗦了。姓谭的不见人影,我们不能让那姓冯的也跑了。”
“冯赛倒不至于。”
“不管至不至于,现今只有看紧他!”
祝德实身后拎着茶具的仆人阿锡小心插话:“冯相公刚才似乎骑马出城去了。”
冯赛刚才离炭行三人只有几十步远,街上人多,车轿挡着,彼此都没瞧见。他是汴京城的牙人,专门替人说合生意,买卖双方都离不得他这一行中间引介人。冯赛今年三十二岁,面皮白皙,样貌温雅,自幼读了些书,加之生性随和,目光中自然透着和悦,身上看不到一般牙侩的黠滑气,又极爱整洁,从头到脚,从来都干干净净。连座下那匹白马,每天出门前,也都要让家里仆役阿山仔细梳洗一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做这一行,言为心声,衣为心貌,你多净一分,便是多敬人一分,别人自然也就会多信你一分。
不过,冯赛也深知本分,自己只是一个中人,不能抢了买主或卖家的光,因此虽然买得起,却也从来不穿太过亮眼的锦缎,更不买过于精贵的服饰,只做到让人舒心悦目即可。今天他穿了件素白的越罗春衫,头戴青纱襆头,脚穿着一双黑缎软靴,看着一身春风、满面春意。
他骑着马,引着一位胡商,正要出城去汴河边接货,顺道去看炭船。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身陷泥渊,将历无穷之劫。
他身边这胡商名叫易卜拉,大个子,黄绿的眼仁,高而尖的鼻子,一把浓胡须。朝廷明令,胡商不许私自与人交易,手续办起来十分繁杂,冯赛手头这一向事情又多,本不想接这桩小买卖,但这个胡商打问到冯赛名头,托了鸿胪寺往来国信所的一位主簿出面来请冯赛。国信所主管迎送各国国使藩商,海外生意常年都要借助他们,冯赛自然不好回拒。幸而这个胡商带了一些象牙来。
这胡商做事老到,要买些好瓷、好锦做回货,说买定瓷锦之后,才出手象牙。冯赛不愿多计较,笑着答应了。锦帛他已经牵头买定,瓷器那胡商看了几家,却都不中意。正巧冯赛的一个熟客来信说运了一船龙泉哥窑上品黑瓷,人已在泗州,清明到京。眼下东南水路不畅,名瓷更加难得,胡商听了十分欢喜,带着三个随行仆役,牵了五头骆驼高高兴兴出来。
冯赛骑在马上,一边随口和胡商说着话,一边却想着心事。今天是他的侧室柳碧拂的生日,柳碧拂去年才娶进门,这是第一个生日,又刚怀了身孕,冯赛本想好好办一办,但正室妻子邱菡那里却不好说。为了这事,这几天他一直没敢去柳碧拂房里。昨晚随意提了一句,邱菡只淡淡应了一声,既不热,也不冷。他也就不好再多说。今早起来,冯赛又偷偷跟柳碧拂说,柳碧拂才听了半句,就忙摇头低声说了句“还是别办为好”,随即就躲开了。
今天冯赛本打算带着家眷,去郊外踏青赏花,也算一举两得。可是那闽西瓷商偏偏今天到,还有那桩炭生意也必须今天办妥。看来只能晚上想办法替柳碧拂庆一庆。但如何既不惹邱菡生气、又让柳碧拂欢喜,着实让他犯难。
冯赛一直做的是撮合人的事,十几年磨下来,不论什么人,他相信都能圆活。可轮到家中这一妻一妾,他却有些计拙了。
他笑着摇摇头,正要出东水门,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唤“冯二哥”,回头一看,是旁边曹家酒栈的店主曹三郎,不知为何,苦着个脸。
冯赛便让胡商先行,回马过去,曹三郎张嘴便是一大篇苦水,冯赛耐着性子听了半天,原来是为酒价。
大宋酒政实行“买扑法”,酒曲只许官卖,不许私造。酿酒卖酒则按酒税额,包给富商大贾。商人买断某一市区酒务,便能独家酿造买卖,区内其他酒家只能在他这里买酒。私造酒曲五十斤、私贩酒三石以上,皆处死。
对面的孙羊店是城东南厢最大的酒户,年年都是由他家买扑这一片的酒务。可是今年,东南厢内外的酒务被一个富商高价买扑去了,那富商叫汪石,他并没做过酿酒营生,买扑到这一片酒务后,回头又想转卖给孙老羊。孙老羊自然先是赌气,不肯接手,但毕竟独占惯了的,不愿受别家勒扣,终于还是用高两成的价买了回来。这样,他不得不提高发卖价,东南厢城内外几百家酒肆的酒价就比其他城区高了两成。一角下等小酒,别处卖七十文钱,他们却不得不卖八十五文。
曹三郎苦着脸说:“那个汪石过过手就是几十上百万,我们这些一杯一盏伺候人的,辛苦一场却白辛苦。冯二哥,您说话有分量,‘牙绝一句话,汴京十万银’,又和汪石、孙老羊都亲熟,您看能不能约了酒行行首,跟他们两位说一说?我们生意做不下去,老孙自家也不好过。”
冯赛在汴京商界行走十来年,圈广人熟,渐渐做到头等地位,得了个“牙绝”的名号,又素来看重信义,富商巨贾都买他的账,市井间因此传出“牙绝一句话,汴京十万银”的话头。
冯赛听了笑道:“多谢曹三哥看重。成,我去说说看。不过未必说得通。我有一个月没见汪石了。这两天他该去太府寺交纳利钱,应该要来找我。我若见到他,就约他到孙羊店说一说。对了,曹三哥,我早前引荐那个炭商谭力住在你店里,这两天你可见过他?”
“几天前,谭力还住在这里,寒食前一天打点行李走了。我也正要问这事,他这两天似乎都没给炭行送炭?我店里存的炭眼看就烧光了,今早去炭铺买,炭铺也没存炭了。明天若再不送来,我这里就得断火了。”
“我正要去城外寻谭力,先走一步。”
邱菡透过车厢后壁板的缝隙向外望去,车已拐过了城东南角,沿着护龙河向北缓缓而行。前面就是东水门,难道是去汴河?
邱菡今年二十七岁,嫁给冯赛已经八年。她的容貌虽然只是中等之姿,但皮肤洁白,目光明净,加之仪态端静,望过去自然让人心生敬慕。然而此刻,她的发髻已经凌乱,双手被绑在背后,嘴被布条勒住,一缕鬓发散在脸前,不时随着车厢晃动,遮扰着视线。脸色则由于惊怕,苍白中隐隐发青。
她的两个小女儿也被绑着。珑儿紧紧贴着她,将头倚在她的腰侧,刚才受到惊吓,哭了一阵,但毕竟才三岁,并不懂什么,这会儿已经安宁些了。玲儿坐在对面,今年七岁,已经能明白这处境,一双又黑又亮的眼里满是惊恐。
柳碧拂则隔着珑儿坐在她这一侧,已平静下来,垂眉低眼,呆呆坐着。从侧脸望过去,她虽然也被绑着,却似乎并没有损及她的秀容,眉眼仍旧如同柳叶清露一般,反添了些忧怯,越发惹人爱怜。
只是,她那一副听之任之的模样,让邱菡有些鄙夷。也难怪,她这样的女子,恐怕早就听任惯了的。邱菡看了一眼柳碧拂尚未隆起的腹部,随即转过头,这时哪有余力花心思在她身上?
邱菡望向对面那两个男子。两人分别坐在玲儿两侧,一个高颧骨、薄嘴唇,一双手搭在腿上,暴着青筋,手指不住轮番叩动;另一个扁头扁脸、皮肤黝黑,有些蛮憨,昏蒙蒙一对大眼珠不停地左右转动。两个人衣着样貌看着很普通,像街头寻活的一般力夫杂役,眼神却时刻透着警觉。
两人看邱菡在打量自己,一起回盯向邱菡,邱菡忙低下头,暗暗寻思。丈夫冯赛说今天要带胡商去东水门外汴河接货,这车又正前往东水门,难道是丈夫想替柳碧拂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