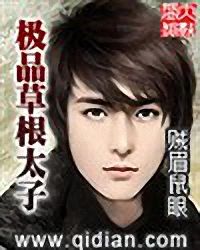草根家事-第6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抠出来,井水就会滞留在井管里,冬天就会把水井冻裂。小女儿抬不动水,她又很认真,就把抠井碗的事交给了她。假如她忘记了,就会有哥哥们的提醒,但要扣她一个劳动分。其他的家务,像洗碗、做饭、圈鸡,都一一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家里的事情井然有序,人人尽职尽责。
每个孩子根据年龄的不同,学习费用也有所差异。在学习费用上花多少钱由自己记在勤俭节约竞赛栏目中,节省下来的钱自然有他们自己支配,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
有了这几项竞赛,他们都很高兴,还互相监督,互相提醒,生怕自己落后了。为了节约用纸,老二李昊的笔记本上的字总是密密麻麻的。演算用的废纸几乎看不到一处空白的地方,白色的纸张成了蓝色的了,好像蓝纸画了几道白印。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吧,三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几乎被他们承包了,我们就会腾出一些时间把劳动投入转化为货币增值。
生产队的分值(10分的价值)越来越低了,靠生产队的劳动来养家糊口,是尽人皆知的天方夜谭。生产队墙上工分表的名字不下七八十人,而真正下地干活的往往不到一半。你看,队长、会计、饲养员、大队的兼职干部、看青的,都到这个墙上记工分。还有被大队和公社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抽调的,什么治安的人保组、武装民兵训练……都在墙上坐享其成,且风雨不误的记工分,满勤。更有和领导沾亲带故的,找个理由就干光记分不干活的差事。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给日本人干事还要“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由此而来。
忙铲忙割的季节,生产队的人手严重不足,就把妇女当成了生力军来使用。孩子的妈妈正是受命于这个危难之时,再次当上了妇女队长,带领几十名男女劳动力下地干活,成了“打头的”。在旧社会,打头的就是领着伙计干活的,新社会把打头的封为组长,社员还是把他叫做打头的。她当了打头的,生产队每一天多给她记一分,一年300多分只不过值一二百块钱,但也是“不小”的收入吧。
眼看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念书的费用也与日俱增,这样混下去无疑是“坐以待毙”。1978年秋,公社领导以照顾干部家属为由,她去社办企业公社的服装厂上班了,每个月可以挣六七十元,一年就能顶上生产队两三年的收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心花怒放,苦累全都抛在了脑后。
我们家离公社25里,她要起大早贪大黑地上下班。风和日丽还可以,顶风冒雪就苦不堪言了。每一天到家后都是一身汗水,但为了挣钱,总比死了猪流泪水要开心,也总比在生产队一年到头只能领回口粮和柴草要好。
服装厂的活计很累,赶上服装急需出厂更要打夜班赶任务,一个星期得有两三天熬夜。那时就不能回家了,只好住在厂子里,十几个人挤在5米长的土炕上,或者到附近的工友家里过那后半夜。这样,没家里的事和孩子就得有我照看了,天各一方,公私不能两全。有时候我也不能回家,下乡蹲点在村上,家基本就唱“空城计”了,扔下3个孩子吃得如何、睡得怎样,你就可想而知了。
1981年,服装厂在“大家拿,拿大家”的人祸中寿终正寝了,她也解除了奔波的劳苦,疲惫之躯还未来得及休整,忧虑之心又沉重了。因为家庭收入的逆转之势就迫在眉睫。就这么一项“额外的收入”,现在又“绝源”了,相当于塞翁失马,但不知道是福是祸……
2 我的一家(夜行百里)(6)
2我的一家(夜行百里)(6)
服装厂倒闭了,欠下一大堆工人的工资,就以成衣按市场零售价顶替,不管你什么适用不适用的。工人只好手拿一大堆服装到集市上去销售,成了服装厂尽心尽力的义务销售员。我家得到的是10来条清一色的蓝色裤子,没有一条适合家里人穿用的,卖又卖不出去,只得将就穿了。父母、我们和兄弟妹妹出出进进全是一个颜色一种制式,犹如某行业的行服了。自己都觉得好笑,还得向不知情的人做个解释,否则就有偷盗之嫌。
没下岗前,她在服装厂负责质量检查和组织生产,队服装生产和管理及工艺流程谙熟,工作上也很投入。现在突然间刹车,有点茫然失措无所事事,更觉得无路可走,整天呆在家里忧心忡忡。
那一天,忽然有一家私营服装厂的老板登门来聘请她做厂长,塞翁失马后果然有了意外的福分。
老板是邻村的,我们认识,他姓宋名佐英,是解放前这里名绅宋钦侯的孙子,排位老三,人称宋老三。
宋氏服装厂鼎盛之际有几十号人从业,乡内外很有些名气。由于缺乏管理人员,效益一直不是很好。公社的服装厂一解体,倒是成全了他和她,就近的技术工人也纷纷投到他的麾下,宋老三的企业正蓄势待发。
她重操旧业,负责企业的生产和产品质量。宋老三出手大方,给她每个月150元的工资,是原来企业的一倍。
宋老三大有其祖父的遗风。他手里有了钱,不思企业的管理与发展,整天和一帮食客泡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猜拳行令,以示仗义,好像自己就是孟尝君。
宋老三最大的特点除了嗜酒,就是嗜书,都如命。他看了很多的书,古今中外无所不及,他看书就像小孩看连环画那样入迷,你抢都抢不下来。有时候他怕别人打扰他看书,竟然爬上房顶看书,一看就是半天,不许别人打扰他。等他看饿了下得房来时,所有生产上的事已经耽搁多时了。该他表态的事,你找不到他;去沈阳本该一天办好的事,他三天也办不完。酒喝足了才想去办事,头又涨腿又软。就这样,大好的时光和机会白白地流失,一次次地一闪而过。不到二年,好端端的企业被他自己泡黄了。欠下工人的工资很少有人去向他讨要,要不来还得惹一肚子的气,只好自认倒霉。
宋老三总算在破产之后给大儿子办完了婚事,老两口子领着女儿和小儿子背井离乡去了新城子区居住。所以这样,一来可以躲债,二也是为一家人谋个生路。这会他倒是勤快了,起早贪黑地卖起了血豆腐,无奈浪子回头为时晚矣。不久,他得了重病不治身亡客死他乡。听到他的噩耗后,我和孩子的妈妈去看望抚慰他的遗孀。她泣不成声,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劝告。
当初,宋老三把生产和质量管理交给了孩子的妈妈,而销售和财务已对外联络交给了一个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个人心计甚多,又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来二去,所有的企业机密,全都被她了如指掌并为己所用。此时的宋老三成了一具枯死的躯壳,她却借机壮大了自己,进而取而代之。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没有死去,而是换了一个姓名,依然走宋老三原来疏通好了的渠道。
宋老三为人豪放豁达更是血性,缺少的是身体力行和任人唯贤。他之死令人怜悯又使人叹息。我们空有辅佐之心同情之意,只是难以越俎代庖,也是鞭长不及马腹。
孩子妈妈再次失业不那么处心积虑了,久经的磨砺使她对就业下岗的轮回已成为司空见惯。几年间,她去过大韩家窝铺的吴家、燕飞里的刘家,为他人作嫁衣裳,倒也没有清闲过。她像个游击队员,神没鬼出的,左邻右舍还以为她在公社的服装厂上班,钱一定没少挣。
1985年,罗家房乡私营企业纷纷停下了脚步开始喘息。这些企业都是靠原来公社趟出来的路子走老关系的。改革开放一活跃,这些关系的链条松动得不能链接在一起了,私营企业局成了无水之源,一天天地枯竭了。
这时,大孩子已经考上了新民省重点高中,其他两个孩子也正沿着这条路向前冲刺。于是,钱又一次对我们警钟长鸣于耳际。
3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更需要钱。我一个月180元的工资怎么能经得起他们的“你争我夺”?我们终于走上了一条异想天开的来钱道——养鹅!
1985年盛夏暴雨连绵,辽河的洪水已淹没了所有的河滩地,水还继续地上涨。既然决定养鹅,就不能再犹豫了,天塌地陷都不会改变,害怕洪水吗?
那天上午9点,辽河又出现一次大的洪峰,我没有理会,带上一些钱独自骑车直奔铁岭。我不知道去铁岭的近路,即使有近路也被洪水阻隔了,只好走大路。走大路要经过新城子和清水台,然后90°大转弯再向北直行,也就是走哈大公路。这条路只听说过但没走过,就边走边问路。中午过后,总算来到了铁岭,单程150华里,还不算在铁岭市内绕来绕去的路程。
到铁岭买鹅?是的,那里有纯种的昌图豁鹅。铁岭的畜牧研究所是昌图豁鹅的提纯繁殖基地。要是在铁岭买不到的话,我就去昌图,狠心了。
还好,经人指点我找到了畜牧研究所,到那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研究所在山上,本来一路疲惫不堪却又要上山,两条腿酸得直打颤。到那才得知,今年最后一批鹅雏还没有孵化出来,但我毕竟赶上了末班车,忘记了劳累。按研究所的规定,当下我交了预付订金,心里踏实多了,没白跑一趟。
本该在铁岭住一个晚上好好地休息一下,一想起辽河发水我还是回去了,立即返回。
回来的路上自己告诉自己,累了就慢些骑。可一上自行车则心不由己了,恨不得一步到家。出了铁岭市区,才觉得饥肠辘辘,只好停下来在路边的小吃部用电便餐。吃过饭,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想起离家至少还有130多里路,没有休息就又路了。
这会则是身不由己了,想快骑也不行了,两条腿比木头还硬,往下一使劲脚和腿还有膝盖无处不酸疼。好不容易过了新城子来到了六王屯,天已经黑了下来。
二妹妹就住在六王屯,我没到六王屯的时候就打算在她家住一宿,实在走不动了。可到了那,我的主意又改变了,转念一想家里大人孩子一定惦记我,涨这么大的水她们能放心吗?掏出烟,抽了一支继续赶路。
过了六王屯,途中有个叫八间房的村子离石佛寺20多里路杳无人烟,一片荒凉。为了预防不测,我下车捡了几块拳头大的石头带上,万一有劫匪也够他招架的。
黑夜和那路一样的宁静,只有自行车和路面摩擦发出“沙沙”的响声,死一样的寂静。天上的星星眨着眼,哆哆嗦嗦的,不是的躲藏。路上没有一个行人,灌木丛古里古怪的,看不清枝叶后面隐藏着什么,全是一个个凸凸凹凹似人非人的轮廓……我不敢想象太多,只是集中目力和听力朝前走。忽地一个小转弯出现,隐隐约约看见了稀稀疏疏的灯光,啊,眼前就是沙岗子了,就是石佛寺东边的沙岗子村,忐忑的心不觉落了地。小时后到姥姥家来玩,就曾经和大舅一起赶着大车来卖香瓜,晚上那里演电影,有买卖做。
真巧了,今天沙岗子也在放电影,可我没有心思去欣赏它,便在人群中挤了出去。
过了石佛寺、马门子,就到了本乡境内的山西孟家,啊,离家不到10里路了。这时,堡子里只能偶尔见到一丝从窗帘的缝隙中露出的灯光来,一忽闪又灭了,大概是上厕所的人开着了,完事又关了。或许是小孩子哭了,大人找些什么东西哄他,孩子睡了,灯就关了。
夜深人静,自行车“刷刷”的响声显得很大。我不爱听这种很是单调的声响,总以为身后有很多骑自行车的人在追赶我。偶尔下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再骑上继续赶路,也看看那几块石头是不是丢了,就放在车子的后货架上,很容易颠跶丢的。不爱听“刷刷”的声音,我就哼唱一些歌曲来掩盖车轮声。
家边上的几个堡子我都很熟悉,唱歌也不会招来麻烦,都知道我是穷光蛋。这样反倒安全,不会吧我误会成有钱的,这也是我经常下乡蹲点的地方,连小孩都认识我。
一阵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到家了,已经是接近半夜了。进了家门,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太累了。草草吃了点东西,倒头便睡。
2 我的一家(历尽艰辛)(7)
2我的一家(历尽艰辛)(7)
从家到铁岭,再加上在市区里绕行的路途,这天我骑车足足走了近400里的路途,创造了我一生“行走”的记录。按预定的日期,十天后再次去铁岭取鹅雏。
我一共预定了60只鹅雏,一个人是很难把它们用自行车运回来的。我不忍心劳累她,毕竟是女人,她不忍心花钱坐火车,只好由她和我一起去了。
记得那是8月11日吧,辽河的洪峰一个接着一个,河水暴涨得很厉害,很少有人出行,都在家里预防洪水可能发生的不测。我对孩子做了一些安排,便按着上次的路线向铁岭进发。这是我那一年三次去铁岭的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