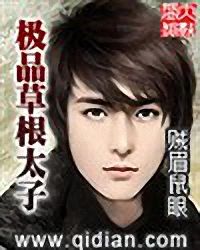草根家事-第6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那么高。后来为了沈山线铁路的安全,大堤不断地南移加高,现在的沈北大堤有10多米高,堤底宽50米,上宽7米多,俨然一个土长城。洪水不再危害铁路了,但河滩地基本上年年遭受水灾,河床年年升高,已经比大堤南高出2米多。
二道堤在沈北大堤北。1951年和1953年涨大水时,水基本上和二道堤一般“高”了,上年纪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洪水。自从修筑了沈北大堤,河滩地就成了“水乡泽国”,至今依然如故,再也没有“十年九涝,不离河套;一年不涝,鸡鹅乱叫(鸡鸭成群丰收景象)”的光景了。
1951年和1953年的两次大水冲毁了沈山铁路,损失惨重,国家从大局着想才修筑了沈北大堤。现今的沿河五个行政村的居民,有90%都是从辽河滩那搬迁过来的。至此,大堤以北的董家窝铺、大小孟家窝铺、郭家窝铺、王家街(读音gai)、邹家街(读音gai)、傅家街(读音gai)、郑河套、黑鱼沟、桑树子、刘家塘……等20几个自然村屯先后消失了(仅罗家房乡沿河地区)。现在的沈北大堤之外的耕地水毁沙盖,几近荒漠。2万多亩耕地没有一棵树木,狼、狐狸、野鸡野兔早已销声匿迹了,就连蛇也很少见到了,还有生机吗?
大堤南的“石佛寺水源地”昼夜不停地抽水,活着的树木都枯死了。1986年起到1998年的13年间,辽河洪水共造成5次绝收,3年欠收过半。1997年,80%的河滩地无人再敢耕种而荒芜,或只种不管理——不施一斤化肥。天灾使家乡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水平得改善很缓慢,甚至是倒退。但是,改革又给家乡人开阔了许多致富之路,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外出打工。德盛堡村不到2000口人,到北京沈阳打工的超过了400人。
“人怕逼,马怕骑”,逐年变坏的生态环境逼迫人走适合自己的路,何必“坐以待毙”啊。我是出来了,但我不是被逼出来的。我永远会留恋这块热土,故乡故人。但心里总有一种不值得留恋的感觉,只有怜悯她的不幸而难以割舍的情愫。
孟家台不靠近辽河,也没有河滩地耕种,李开元那里的日子就比家乡要殷实一些。生产队大帮哄时,人为的灾害却“猛于虎”。上级不顾当时的条件是否具备,硬下刚性指标——变旱田为水田。由于不懂技术,缺少必要的投入,水稻亩产仅仅三四百斤。水田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福音,反倒让那里大受其害了。秋收后,李开元那里不得不把仅有的一点口粮拿到集市上换粗粮,不然就难以维持一年的吃用。二大爷就死在那个“反美不美”的年月,大米梦成了他永久的噩梦。
土地承包后,李开元哥三个的日子得过了。李开元还入了党,成为孟家台村的主任。那年二大娘还健在,正月初一我就和我的大孩子给她拜年去。那时候他们哥三个算是富裕户了,老三还养起了拖拉机。我们两地相距20多里路,家家有了摩托来往就更便捷更频繁了。不过,只从我去了北京,又有10年没有去过孟家台堂弟那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同宗同族的哥们间更是多了一层亲近。1996年吧,李开元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正处在分配的关头,一家人都为找个“婆家”而犯愁。农村的孩子读大学有谁还想回农村?最大的愿望就是远走高飞,离开世代为农的境地。换一下生活方式,是所有乡下人的心态,农村的确太艰苦太闭塞了。李开元找我给他出主意,我责无旁贷,身体力行。很快,他的女儿就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了,一家人皆大欢喜。
他和二大爷是一个性格,不吝惜钱财,只是苦恼“有猪头送不出庙门”。几乎所有大专院校毕业孩子的家长,没有一个不为工作“倾囊相助”的。一个土老冒认识谁啊?于是就有了“升学考儿子,就业靠老子”的公理。靠老子什么?地位、金钱,仅此两样。于是,好多家长没等孩子毕业就四处打探寻求门路。那些有远见的父母,干脆让孩子报考有门路好分配的学校与专业。那时我的三个孩子大学都毕业了,都说我是学生就业与分配问题的专家,许多人都来咨询我。其实,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形式的演变,谁也谁也说不上永远不会失策。但有一点是永远也颠扑不破的,那就是钱!没有钱,再好的理想与夙愿都会荒废,就像辽河滩。
第八章 我的一家 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
第八章我的一家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
亲祖父李春荣我不曾见过。自父亲过继到曲氏奶奶后,提及往事涉及到祖父的称谓时我就叫他三爷,这是我懂事后才知道的。在我的记忆里,曲氏就是我的奶奶,亲奶奶。
奶奶21岁就守寡,她不肯再嫁。祖父去世后,奶奶的娘家曾劝她再嫁,但奶奶坚持守寡。奶奶很“传统”,不愿意领着一个女儿再走进另一家的大门,大概是怕委屈了孩子,还有名声更为重要。
虽然奶奶一家只有娘俩,但在曾祖以下也是一个家族中的支系。曾祖的家业是要平分给他的3个儿子的,足够奶奶和姑姑的日用了,奶奶不能不考虑生活。父亲过继给奶奶后,两家合为一家,奶奶的心敞亮多了,总算有了儿子可以依靠立得住门户了。
我从小就是在奶奶的拉扯下长大的,那时我跟奶奶亲,母亲不在家也不想她。奶奶一辈子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从来不花一分钱,我也不记得她手里有过什么钱。她没享受过一天清福,随父亲东奔西走。父亲在“文革”时遭到打击,她也跟着郁闷,整天的提心吊胆。“文革”还没有结束,奶奶就去世了,那年她才60岁。她去世的时候,正赶上李昊出生不到两天。我整整守候她3天3夜没有合眼,对祖母做最后的陪伴,也陪着她走完最后一段人生之路。
国民党统治时期,父亲被抓了壮丁。奶奶为了赎回他,便单独一人步行70里路去了兴隆店。那是哪有什么可走的公路啊,全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走得两只脚全是血泡。奶奶没少和我说起这件事,忧伤得很,表情中露出不尽的而恐惧。
按说父亲是不该被抓的,在奶奶的名下他是独子。但是,村公所为了卡油,就强行让父亲去当炮灰。他们也看准了奶奶是个妇道人家好欺负,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根本不把“独子”当回事儿。暴政当头、贪官当道,一个弱女子上哪去理论是非?只好咬牙破费了。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不久父亲有摊上了“国兵”的人祸,一去就是二年。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了。父亲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被苏军羁押在佳木斯的一个山沟里。很快,苏军和八路军双方达成了协议,给每个人发放钱粮和通行证,将其全员遣返回乡。
父亲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天寒地冻的阴历十月了。奶奶见他安然地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又是烧香又是磕头的。但看他穿得那么单薄,又是一番落泪。父亲回家前,奶奶天天求仙请神为他祷告,“一日三叩首,早晚一炷香”。
1951和1953年辽河爆发洪水,害惨了奶奶。父亲只管在新安堡护校,把家里全都扔下了,奶奶和母亲没有一点主心骨,几近惊慌。奶奶一定要母亲领着我和妹妹赶快逃避,洪水眼看就要漫堤了,堡子里早已十室九空。
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守候着,守候着房屋、猪鸡、粮食、土豆……大堤决口后,洪水把房子冲到了,守候的东西荡然无存,庆幸的是奶奶死里生还。洪水过后,奶奶没有惋惜和哀叹,好歹一家人都在,五大爷不是死在洪水里了吗。
奶奶什么也舍不得,知道没钱的滋味有多难,对家里的东西宁可舍命也不舍“财”。
曾祖的三个儿子刚分家的时候,奶奶的手里还是很宽裕的,供姑姑念护士学校,在那时实不多见的。奶奶娘家门上有个好耍钱的侄子叫曲则州,输光了就来找奶奶“借钱”。奶奶一边数落他的不是,一边又不得不给他钱。奶奶去世时他来吊唁,说起当年的事很是内疚。他看到奶奶简单棺椁伤心不已,说奶奶给他的钱够买多少比这好的棺木啊。他还说,“老太太一辈子不吃不喝,什么也没有攒下,只攒下一个好名声……”
是的,奶奶为人谦和,从不与谁计较什么,更不会和人争斗。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亏让人无祸事”,现在的话就是“吃亏是福”。可以说,我是在奶奶“吃亏”中长大的。
换句话说,我也是在奶奶的被窝里长大的,在她每天晚上讲故事中长大的。她讲给我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晰,主题都是忍让、公正、诚实,都围绕本分、操守、善良的中心。
奶奶去世后的第三年,父亲才被平反昭雪重新上学校领导的岗位。那年的清明节,父亲亲自把奶奶的坟墓迁到高处,一个来往方便又无妨碍的地方,让她一生不安的灵魂再不受人世间的纷扰。
几十年过去了,安息的奶奶不会重生,但她的往事会经常在我的脑际中再现。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一年开春,我得病了。奶奶为了让我吃下一点东西,就领着我去我们家“来伙”时(大家庭的时候叫来伙)的菜园子挖韭菜。那时的韭菜刚刚露出一个小红尖儿,想要给我做汤喝那得挖多少的韭菜啊。奶奶很耐心,一棵一棵地挖,春风吹出了她的眼泪……
虽然我没有见过奶奶因为伤心而流泪,但我知道她有许多的眼泪都流进了肚子里,苦的、酸的,充满了她的一生。
1我的长辈(家父遗物)(2)
1我的长辈(家父遗物)(2)
父亲在外面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一回到家里就变得少言寡语。更让我至今不能想开的是,他从来就没有抱过我,亲热过我。我和弟弟妹妹们对他很是敬畏,更没有那一个和他撒娇的时候。他和祖母在一起算是同病相怜,都是不完整家庭中的一员而走进一个新组合的家庭中来。
父亲主持家政也是勤俭当头,所以家里没有意见值钱的东西。他爱喝酒,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打上一斤八两就算奢侈了。过年的时候从不买什么鞭炮之类的东西,也不贴对联接神,更不供奉灶王、黄仙狐仙(也叫胡仙)之类的神灵。唯有一年例外,父亲从集市上买回3个二踢脚,还有一条3斤重的大鱼。可惜的是,那条大鱼还没等上除夕的餐桌,就被野猫啃去了一半,也让奶奶心疼了好几年,时不时就叨咕几句。
说实话,父亲从小对我们没有什么理想教育,对我也不报什么期望,任由我们自然成长。他不像现在的家长对子女那么处心积虑,和处处留心。我受到的教育完全来自于祖母,在潜移默化的故事中接受思想启迪。
眼看我高中毕业了,才接到父亲给我的第一封交流思想的家书。其主要内容是:考一下大学,否则参军,要不就参加农业生产……
看得出,他对我升学深造没有一点强烈的愿望。参军谈何容易?他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家庭成分。读过父亲的信,我心里感到很冷。前文说过了,我在学校、社会、家长冰冷的氛围中,只能走通往农业农村农民这一条唯一的路了。那时的父亲41岁,现在看来他太年轻了,把握不住自己孩子的命运。
1977年,父亲的老病复发了,而且比以往都重。那时候我已经到公社上班了,特地请假去为父亲看病。
我和学校的一名老师参扶着他去了新民县传染病医院,上下汽车都很吃力,没有一点力气。那个老师叫吴成义,协助我护理。
到了医院,也办理了很繁杂的住院手续,可刚刚住了一夜父亲就非要出院不可,怎么劝也不听,只好由他了。拒绝继续住院理由是,周围全是病人在这里也是吃药打针,不如回家治疗方便踏实。
父亲得的是肺结核,不算什么疑难杂症,他的想法是对的,很现实。从此,他就一直在家里治疗,那病也好好犯犯没有根除。每到秋末冬初时节,病情就会加剧。一到晚上我就不敢熟睡,总是侧耳听他屋子里的动静。
我们住在前后院,来往也很方便,相距仅仅20米远。夜间只要听到后院门响,我就会一骨碌起来,赶紧去看看又发生了什么事。1986年冬,他的病情加重了,半夜里由乡政府的车把他送到县医院,准备再次住院。可是,这次又和上一次一样,仅仅呆了一宿就讨厌那里的环境了,只好打车回家。他说:“呆在这里,不等我病死,就得窝囊死,还不如回家。”他也可怜我,从挂号排队到诊断,楼上楼下只有我一个人背着他不断地往返,他已经走不动路了。
1988年12月24日中午,父亲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与世长辞了,享年65岁。
在最后的几年里,他还是很欣慰的,只是“有福无寿”。相继,他的大孙子考上了吉林大学、二孙子也念了省重点高中,小孙女年初三也是出类拔萃的尖子生。1987年我翻建了新房,父母他们也扒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