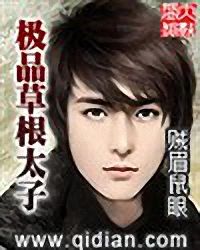草根家事-第6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听女儿说,三大娘虽然是耄耋之年,她的记忆让人吃惊,早年的往事历历在目。三大娘在年轻的时候就博闻强记,也是个很“妖道”的女人。说白了,“妖道”就是很厉害,有点男人霸道的味道。眼下都快百岁的老人了,还时常管教她的子孙,有时候还自己亲自去街上卖菜。
女儿读书期间,每逢开学我都要给三大娘捎去些家乡的特产,她最喜欢吃的是辽河的虾米。虽说是点点心意,却让她乐不可支。女儿去她家时,三大娘总要女儿和她睡在一张床上,说她有回家的感觉。
三大娘的娘家贫寒,她自小就聪明机灵,也能说会道善解人意。大曾祖很是喜欢这个小姑娘,才不把门当户对当回事,娶了她做自己的孙媳妇。我的大娘和婶子们的娘家都是豪门富户,唯有三大娘的娘家贫苦。三大娘在妯娌中是个“到得去”的人,为人处事有条有理,也不卑不亢,没有人瞧不起她,何况妯娌们都是有教养的人啊。
1994年女儿毕业了,最后一次去看望三大娘和她的一家人。后来电话升级了,她们又搬家了,联系也中断了。到现在,一晃又过了14年,但“藕断丝还连”,血浓于水吧。
三曾祖的名讳我记不起来了。对这个支系的人我了解的甚少,只知道解放前他领着两个儿子远走高飞了。有人说三曾祖有先见之明,土改对他没有什么好结果,匆匆处理了家产去了沈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华宝,另一个不清楚。
我曾想过:“文革”过去了,改革开放了,天下太平了,他的子孙为什么不打探一下老家的家族呢?我在沈阳日报、辽宁日报没少发表过文章,用的都是真名实姓,字里行间有我的“家史”、家址、家事,还有我家父的名字……难道他们一次都没有看到吗?或是当了特大的官员有意“避嫌”吗?即使有千万个理由,难道连祖宗也可以忘却吗?
三曾祖这一支系的人,对于我永远是个谜,也是我们李氏家族共同的不解之谜。
四曾祖和四曾母我接触得比较多,多于我的曾祖。四曾祖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了,相貌和我曾祖一样的宽额头。都说人越老越像,此话不假,我二爷、四大爷、六大爷及家父的长相都像四曾祖。
四曾祖的家庭成分自然也是地主了,他只有一儿一女,从大家分得的土地安人口算是最多的了。先年,四曾祖在十佛寺有不错的买卖,人称“李四爷”。伪满和民国那年月的十佛寺是个重镇,沈阳到法库的的公路经过这里,据说是杨宇霆特地为他的家乡法库修筑的。
杨宇霆法库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奉系军阀参谋长,1929年被张学良枪毙于老虎厅。
四曾祖也是很有心计的人,在这里开买卖真的很兴隆。解放后,四曾祖一贫如洗了,靠给别人铲碾子磨维持生计。1960年我们搬回老家时,我还看见了四曾祖背着家什出外做活呢,那是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
四曾祖的女儿嫁给了新城子区烟台窝铺,是我的十姑奶。记得她未嫁人的时候,长得很白皙,总是笑呵呵的,那时我们都住在我的出生地董家窝铺。
四曾祖的儿子李春坡是我的七爷,他叫我的祖母为六嫂。祖母曲氏称七爷是李家第一号败家子,说他是四曾祖娇惯坏了的。
解放前,七爷身为农民却不辨五谷,四曾祖就送他投名师学医,日后也好养活老婆孩子,总不能靠老子养活他一辈子吧。七爷很精明,在名医魏元寿那学业有成,治疗疑难杂症无所不能。可他不专心行医,专和烟鬼们厮混,别人的并没治好,自己倒是落个面黄肌瘦。解放后政府看他在他医术高明的份上,给他个正是医生的名份,后来也因为“吊儿郎当”的工作作风把正式的职业丢了。
他是个地主成分,“文革”期间却能和共产党员的大队长汤玉清扯到一起推杯换盏猜拳行令,这也是他的一绝。那么威严的“大革命”,他因此竟然没被动一根汗毛。没有了正式行医的资格,却有人找上门来给人看病。人家知道他好酒,自然有酒肉伺候,吃了喝了之后,医药费也就全数豁免了。如此仗义怎能养家糊口?只有他自己闹个满嘴流油。到头来,还得80多岁的老父亲背着锤子、凿子养活一家人。等到他的两个儿子大一点了,七爷更有靠了,终年闲逛无所事事,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人称“李春皮”,老顽童、老顽皮一个。
四曾祖老来得子,视七爷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百依百顺。穷人家吃饱大饼子就是福分了,七爷吃四曾祖店铺里的蛋糕还嫌无味,常常咬一口就随手扔掉。四曾祖在石佛寺兴旺的时候,七爷只是个少年,就骑上日本造的“三赖”牌的自行车了。那时的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汽车了,我在1954年才看见公路上有人骑自行车。那时的七爷走到哪,狐朋狗友们就像苍蝇似的跟到哪。饭店吃腻了,汽水喝够了,只有酒水伴他终生。祖母讲,他请人喝汽水,刚打开瓶盖还没等喝一口就扔了,在开另一瓶以显示气派。
60年代初祖母得病了,我去请七爷来给奶奶看病。满以为七爷会上心地看病,哪里料到买药的钱一到他手里就变成酒,吃到他的肚子里,气得祖母大骂他不可救药。
1961年,我和二哥李巨元去团山子给四曾祖他们拜年,那时四曾母早已去世了。那时的四曾祖一家四口人:四曾祖、七爷、还有两个和我几乎同龄的叔叔,一个叫李若恒,一个叫李若强。
给他们拜年我们倒也省事,用不着考虑谁的辈分大小,挨着磕头就是了。在我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四曾祖去世了,扔下三条光棍既主内又主外,稀里糊涂地混社会。七奶在1954年就死去了,医术很高的七爷治不了她的“一般病”,可见他有多么的“粗心”,对家人没有一点责任感。
七爷的不成器,加上成分又高,耽误了两个儿子的婚事。大叔李若恒30多岁才成家,大婶因为不能生育被人家休了,才嫁给大叔。真是苍天有眼啊,大婶到了大叔家,第三年生了个白胖小子,取名李芳元。七爷亲眼见自己有了孙子,也是百感交集。他说这不是我的“阳德”,是四曾祖的积德,兴高采烈了一阵子。李芳元满月的时候,我们在老家的李氏家族都去恭贺四曾祖这条唯一的根苗。因为:那时候的李若强正在监狱里服刑,无期徒刑,“文革”前被捕的,是“故意杀人罪”。
按理说,七爷也该“成熟”了,都有孙子了嘛。他也该因此而振奋一些,多为家境不是太好的子孙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可是,他依旧“恶习”不改,玩世不恭,从不体恤晚辈的疾苦与辛劳。
大叔李若恒是堡子里公认的好人,会做木匠瓦匠活,人也忠厚老实,是个有求必应的善心人。
土地承包到户后,大叔家养了一头毛驴,晚上就拴在靠七爷的房间旁,并嘱咐他夜间精神一点,千万别被人牵去。七爷答应了,可是驴也丢了。
儿子问他晚上没听到什么动静吗?答曰:“听到了!”
“听到了你怎么也不喊我一声啊?”
“他偷他的驴,我睡我的覚,井水不犯河水。”
气得大叔大婶四只眼睛发直,半天说不出话来。
春天里,大叔大婶忙农活去了,央求七爷放放诸,他又答应了。早上猪是放了,晚上猪也死了。原来有人在地头放了农药,就是防备猪鸡祸害地里的青苗,旁边还立了块醒目的牌子。这几个警示字难道七爷不认得?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孙子一天天地大了,大叔给儿子在院子里种一些“甜杆”,是孩子们都喜欢的“甘蔗”,像高粱。大叔再也不敢让七爷放猪了,就求他有空拔拔甜杆里的杂草。七爷“哼”了一声就应承下来。大叔心想,看态度这回挺在意,孙子是他的心肝嘛。到了晚上,大叔大婶大地里回来一看就傻眼了!七爷把所有的甜杆苗拔得一颗没剩,杂草倒是秋毫未犯。
1986年,我家的大儿子李靖考上了吉林大学,过年的时候我领着两个儿子去给七爷一家拜年。这也是“例行公事”,年年如此。今年我异想天开,想用大学生刺激刺激七爷,让他有点进取心,为了将来的孙子。然而,七爷已是病入膏肓了。什么病?老病,散懒颓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七爷人就那样了,心还是很聪明的,他把我的心机看个底朝天。他说:“我祝他们高升高转,我这辈子就这个德行了,天大的能耐也教育不好我了。”
七爷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一日不如一日,大年初一早已日上三竿,他依旧趴在炕上,头不梳脸不洗的。晚上用的屎尿罐子就摆在头顶的地上,炕边就是饺子和碗筷……
第二年四月春光明媚的时节,七爷死了。大叔为他送终,我为他守了两天两夜。以上关于他的“传奇故事”都是大叔讲给我的。
望着躺在地上的七爷,会想起当年“李四爷”的奔波创业,为他守灵的人无不感慨。七爷死后,他的双腿也没有伸直,卷曲着,好像还有他没有走完的路要走。我是本家人,说什么都不为过,没有人挑我的理。我说,七爷是我四曾祖给惯成这样的啊。大叔表示赞成,其他人也都点头。
为七爷送葬的人很多,他为很多人治国病,人情不错。七爷在堡子里不坏,人很和气,所以他还是有值得怀念的地方。
我的五曾祖不曾谋面,听老人说,他的性格有别于其他哥四个,脾气暴躁,得理不让人。但我见过我的五曾母,我叫她五太太,是五曾祖的续弦。五曾母的年龄与我祖母差不多,红黑的面颊,中等的女性身材,很爱说话的。
1967年时,五太太家住新城子区兴隆台乡盘古台村,离我家十几里路,可我们并不知道。那个时候五曾祖早就不在了,她和五曾祖生的两个儿子在沈阳工作。她是地主分子,不便于和儿子在一起,自己独立生活,还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五太太看似年老了,腿脚还是很灵便的,精气神很旺盛。
那年的5月5日我的大儿子出生了,不知道五太太从那得到的消息,他老人家徒步来给孩子“下奶”。他的家族观念很强,不比三曾祖他们。她说我的孩子是李氏家族下一辈第一个孩子,也是第一个男孩,她一定要花钱的。我百般不收,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孝敬过她们,真的不好意思啊。五太太急了,只好收下她的那份爱心和对家人的眷顾。她说她有钱,儿子们给,自己还能挣。
记得五太太给孩子5元钱,那时的5元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婚礼一般才花2元钱。那时我就想说:五太太啊,等孩子能挣钱了,世界上还会有你吗?
对于刚满月的孩子,我的五太太就是他的活祖宗!你得到祖宗的钱了,世界上还会有你这么幸运的人吗?
“文革”结束了,五太太回到她儿子的身边。仅此一面,我再也不晓得她老人家是否还健在?五曾祖这一支系的人从此也杳无音信了,想必他们还在沈阳。但难得一面……
3 我的哥们(死里逃生)(1)
3我的哥们(死里逃生)(1)
3我的哥们
五太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人世间的舞台也是这样不断地拉开序幕,又谢幕,而留下的镜头不断地在人们的记忆中闪回,永远不会泯灭。
我的出生地董家窝铺,也是始祖李岳从山东到关东的立足之地。在东北,好多的村屯都是以“窝铺”来命名的。因为方言不同,“窝铺”也被叫做“窝棚”,是农民看庄稼临时搭建赖以栖身之所。在沈阳新民境界,有“铁道北72窝铺,铁道南72牛录”之说(牛录是满语,也是军政的编制)。由此可见,先祖时代留下的“窝铺”,佐证了闯关东移民的史实,镌刻着老少爷们哥们创业的历程。董家窝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演绎了近150个寒来暑往,结束于1948年或是1949年,在夏季。
董家窝铺紧靠辽河南岸,解放前有码头可通达河北的法库。那时的辽河没有大堤,只有不到一人高的小围堤。辽河发水即使漫堤也不会对沿河地区造成危害,水顺着低洼之处向南的方向扩散到沈阳以北,沿河的庄稼没有大的减产。民国后,为了保护沈山铁路,河堤不断地加高加固并且不断地南移,所以辽河一涨水,董家窝铺就成了水乡泽国。也就是在那个年月,董家窝铺这个村屯只能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历史上的董家窝铺有五大姓氏,我们李家是最大的家族,还有于家、刘家、魏家、董家。因为董家先入为主吧,这里就叫董家窝铺了。
从始祖李岳算起,到我的长孙李临川这一辈,李氏家族在沈阳地区已经有9代人了,前后有近150年的历史了。
董家窝铺地处新民的最东北角,离县城140华里,东与新城子区搭界,北同法库县隔河相望,是个山高皇帝远“三不管”的地方。在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