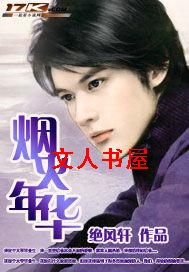九三年-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且不说政治热情,单就建筑而言,这个大厅也令人战栗。人们模糊想起原先的剧场,由花环装饰的包厢、天蓝色和大红色的天花板、多刻面的分枝吊灯、晶莹闪亮的多技烛台、闪色壁饰、窗帘和帷幔上众多的爱神和仙女、表现皇族情爱的各种金色绘画和雕刻,它们曾使这个严厉场所充满了微笑,而现在,四周是僵硬笔直的线条,像钢铁一样冰冷而尖利,仿佛布歇①被大卫②砍了头。
①画家与室内装饰家(一七0三——一七七0),擅长田园或神话题材。
②画家(一七四八——一八二五),国民公会委员,后为拿破仑作画。
(四)
谁看见了大会就不再想到会场。谁看到戏剧就不再想到剧场。没有什么比国民公会更为畸形,也更为崇高的了。英雄成堆,懦夫成群。山上是猛兽,沼泽里是蛇。今天已成为幽灵的那些斗士当年正是在那里争斗和生活的,他们相互摩擦、相互挑衅、相互恫吓。
巨人的名单。
右边是吉伦特派——大批思想家,左边是山岳派——一群角斗土。一边是:布里索,他接管了巴土底狱的钥匙;巴尔巴鲁,他使马赛人对他言听计从;克尔韦莱冈,他手下的布雷斯特管住扎在圣马尔索郊区;让柬内,他树立了代表对将军的霸权;致命的加代,一天晚上他在杜伊勒里宫随皇后看了熟睡的王太子,并亲吻孩子的前额,却让孩子的父亲人头落地;萨尔,他是揭露山岳派与奥地利密切交往的神秘人物;西耶里,右派的疯子,正如库东是左派的双残腿;洛兹·迪贝雷,他被一位记者称作“无赖”,便请记者吃饭,说道:“我知道‘无赖’不过是指‘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拉博·圣埃蒂安,他在一七九0年的年历开头写了这句话:“革命已经结束”;基内特,他是推翻路易十六者中之一位;冉森派教士加缪,他起草了教士公民法,相信副祭帕里的奇迹,在卧室的光墙上钉着七法尺高的基督圣像,每晚在像前下跪;福谢,他是教土,但与卡米耶·戴穆兰一起制造了七月十四日;伊斯纳尔,他的罪行是这句话:“巴黎将被毁”,而当时布伦瑞克正好说:“巴黎将被烧光”;雅科布·迪蓬,他最先喊出:“我是无神论者”,对此罗伯斯比尔回答说:“无神论是贵族政治”;朗儒伊内,一个强硬的、有远见、有头脑的勃良策勇士;迪科,他是布瓦耶-丰弗雷德的欧里阿尔①;勒贝吉,他是巴尔巴鲁的彼拉季斯②,因罗伯斯比尔尚未被送上断头台而辞职;里肖,他反对巴黎各区成为永久性机构;拉祖尔斯,他曾发出致命的名句:“感恩戴德的民族有祸了!”后来又在断头台前改变初衷,对山岳派掷去这句高傲的话:“我们死去是因为人民在沉睡,你们将死去是因为人民将觉醒”;比罗托;他促成了不可侵犯性的废除,因此无意中铸成了铡刀,而且为自己立起了断头台;夏尔·维雅特,他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我不愿意在刀下投票”;卢韦,他是小说《福布拉斯》的作者,后来在罗亚尔宫和洛多伊斯卡一起开书店;梅尔西埃,他写了把黎图景》,呼道:“所有的国王都感到后颈上有一月二十一日③”;马雷克,他担心的是“旧限价的乱党”;记者卡拉,他在断头台上对别子手说:“我真不想死,想看看下文”;维热,他自称是梅延一卢瓦尔第二营的掷弹手,在受到公众席的起哄时喊道:“只要公众席一出声,我们就全体退席,举着军刀向凡尔赛宫进发”;比佐,他后来因饥饿而死;瓦拉泽,他后来自刎而死;孔多塞,他后来因携带诗剧《贺拉斯》而泄露身份,死在改名为平等镇的皇后镇;佩西翁,一七九二年他被群众崇拜,一七九三年被恶狠吞食;此外还有二十多人,如:蓬泰库朗、马尔博兹、利东、圣马丹、迪索尔(他译过尤维纳利斯④的作品并参加过汉诺威战役)、布瓦洛、贝尔特朗、莱斯泰尔一博汉、勒萨日、戈梅尔、加尔迪安、曼维埃尔、迪普朗蒂埃、拉卡兹、昂蒂布尔,在他们前面还有在另一面有:
①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记》中主人公的战友。
②古希腊悲剧中的挚友典型。
③即路易十六被处死的那一天,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④古罗马诗人。
一位巴尔纳夫①式人物,名叫韦尔尼奥。
安托万-路易-菜翁-弗洛雷尔·德·圣茹斯特,他面色苍白,额头很窄,五官端正,眼光神秘,忧郁而深沉,二十三岁;梅尔兰·德·蒂翁维尔,德国人称他“火鬼”;杜埃的梅尔兰,他是制定反嫌疑分子法的罪魁祸首;苏布拉尼,政月一日巴黎人民曾请他任将军;原本堂神甫勒邦,他用洒过圣水的手拿军刀;比若一瓦雷内,他设想过未来的司法,没有法官,只有仲裁人;法布尔·戴格朗蒂,他发明了一项可爱的东西,共和历,就好比鲁热·德·利尔获得非凡的灵感作了《马赛曲》一样,不过这两人都仅此一次;马尼埃尔,他是公社的检察官,曾说:“死一个国王算不得是少了一个人”;古戎,他曾进人特里普施塔特、纽施塔特和施派尔,目睹普军逃窜;拉克鲁瓦,他由律师变成了将军,并在八月十日前六天获圣路易骑士勋章;弗雷龙一泰尔西特②,他是弗雷龙一佐利奥斯③之子;吕尔,国王铁柜的无情搜查者,注定要自取灭亡的共和派,后来当共和国灭亡时,他也自杀;伏谢,他有魔鬼的灵魂和死尸的面孔;康布拉,他是杜敬老爹的朋友,曾对吉奥坦说:“你是斐扬派,可你女儿④是雅各宾派”;雅戈,当有人埋怨他让犯人赤身露体时,他粗暴地回答:“监牢就是石头做的衣服”;雅沃格,他是圣德尼皇陵可怕的掘基人;奥斯兰,这位放逐者在家中私藏了一位被放逐者夏里夫人绑塔博尔,他主持会议时示意公众席喝倒彩;记者罗贝尔,他是凯拉利奥小姐的丈夫,那位小姐写道:“罗伯斯比尔和马拉都不来我家,罗伯斯比尔愿意时会来的,马拉永远不会”;加朗一库隆,当西班牙介入对路易十六的审判时,他高傲地要求大会不要屈尊地宣读一位国王致另一位国王的信油雷瓜尔,他是主教,最初提倡早期基督教,后来在帝制下由共和派变为伯爵;阿马尔,他说:“整个地球都认为路易十六有罪。由谁来裁决呢?别的星球”;鲁耶,一月二十一日他反对在新桥鸣炮,说:“国王掉脑袋应该和别人一样,不声不响”;谢尼埃,他是安德烈的兄弟;瓦迪埃,他也曾把枪放在讲台上;帕尼,他对莫莫罗说:“我希望马拉和罗伯斯比尔在我家餐桌旁拥抱。”
①立宪君主派(一七六一——一七九三),曾颇有影响,后死在断头台上。
②荷马的《伊利昂记》中可笑而懦弱的人物。
③古希腊诡辩家,以批评荷马著称。
④吉奥坦(Guilforin)是法国议员(一七三八一——一八一四),一七八九年国民议会通过了他发明的断头机,以他的名字命名为Guillotine,即他的女儿。
“你住在哪里?”“夏朗东①”“那就不奇怪了”;勒让德尔,他是法国革命的屠夫,就像普赖德曾是英国革命的屠夫一样,他对朗朱伊内喊道:“过来,让我宰了你。”
朗朱伊内回答:“你先得颁布法令,宣布我是牛”;科洛·戴尔布瓦,他是位阴阳怪气的演员,脸上戴着古代的面具,上面有两张嘴,一张说“是”,一张说“不”,一张同意,一张反对,他在南特痛斥卡里埃,在里昂神化夏利埃,将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将马拉送进先贤调;热尼西厄,他要求对凡持有“路易十六被害”纪念章者一律判死刑;莱奥纳尔·布尔东,他是小学教师,曾接待汝拉山的长者②;海员托普桑、律师古比约、商人洛朗·勒库安特、医生迪埃姆、雕塑家塞尔让、画家大卫、亲王约瑟夫早等。此外还有勒库安特被伊拉沃,他要求宣布马拉“患痴呆症”;罗贝尔·兰代,是他创造了这个令人不安的大章鱼:公安委员会是它的头,它的二万一千条肢体覆盖全国,即革命委员会;勒伯夫,关于他吉雷一迪普雷曾在《假革命者的圣诞》中写了这句诗:
勒伯夫③见到勒让德尔便牛吼起来。
还有托马斯·佩思,他是美国人,慈悲为怀;阿纳夏尔西·克洛兹,他是德国人、男爵、百万富翁、无神论者、埃贝尔派的天真汉;勒巴,他是迪普莱的朋友,正直廉洁;罗韦尔,他是罕见的为恶而恶的人,因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确存在,超过人们的想像;夏尔利埃,他要求称呼贵族时用“您”;塔利安,他悲哀而无情,出于爱好而制造了热月九日④;康巴塞雷,他是检察官,后来成为王公;卡里埃,他是检察官,后来成为残暴者;拉普朗什,有一天他喊道:“我要求给警炮以优先权”;蒂里奥,他要求革命法庭的陪审员采用口头表决;瓦兹省的布尔东,他向香邦提出决斗,揭发佩思,又被埃贝尔揭发;法约,他提议向旺代地区“派一支纵火部队”;塔沃,他在四月十三日几乎成为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调解人;维尔尼埃,他要求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首领们去当普通一兵;香贝尔,他在美因茨闭门不出;布尔博特,他在攻占索米尔时坐骑被击毙;甘贝尔托,他指挥瑟堡海防军;雅尔一庞维耶,他指挥拉罗舍尔海防军;
①帕尼管理夏朗东的神经病院。
②伏尔泰曾避难于汝拉山区的费尔尼。
③字意为牛。
④即罗伯斯比尔被逮捕之日。
勒卡尔庞蒂埃,他指挥康卡尔分队;罗贝尔若,拉斯塔特的敌军正设下陷饼等他;马恩省的普里厄尔,他在营地里喊着骑兵上尉无流苏的旧肩章;萨尔特的勒瓦瑟尔,他只用一句话就使圣阿芒营的指挥官赛朗被人杀死;雷维尔雄、摩尔、森特的贝尔纳、夏尔·里夏、勒尼尼奥,在这群人之上是一位米拉博式的人物,名叫丹东。
在这两个阵营之外名立着一位使他们敬畏的人,就是罗伯斯比尔。
(五)
恐怖和畏惧在他们面前弯腰,恐怖可能是高贵的,而畏惧是卑下的。在豪迈气概、英雄主义、牺牲精神、激愤狂热之下,是一大群毫无生气的无名人。坐在会场最低处的叫作平原派,那里的一切都飘浮不定,人们怀疑、犹豫、退却、拖延、窥视,人人自危。
山岳派是精英,吉伦特派也是精英,平原派是群众。平原派的集中代表是西埃耶斯。
西埃耶斯是一位高深但变得空洞的人。他停留在第三等级,未能上升到人民。有些人生来只能半途而废。西埃耶斯称罗伯斯比尔是老虎,罗伯斯比尔称他是鼹鼠。这位玄学家达到的不是智慧,而是谨慎。他是革命的朝臣,而不是革命的仆人。他拿起铁锹和人民一同去马尔斯校场劳动,但与亚力山大·德·博尔阿内套在一辆车上。他建议铁腕政策,但不使用。他对吉伦特派说:“让大炮也站在你们一边吧。”有些思想家是斗士,例如韦尔尼奥身边的孔多塞,丹东身边的卡米耶·戴穆兰,也有些思想家考虑的是生存,例如西埃耶斯身边的人。
最慷慨的酿酒槽里也有酒渣。在平原派下面还有沼泽派。可怕的停滞下面是利己主义。胆小鬼在默默的战栗中等待。这是再悲惨不过的了。忍辱含垢,忍气吞声,用奴颜盖住怒容。他们在厚颜无耻地畏惧,什么怯弱行为都做得出来。他们喜欢吉伦特派,却挑选了山岳派;他们决定了结局。他们朝成功者倾斜,将路易十六交给韦尔尼奥,将韦尔尼奥交给丹东,将丹东交给罗伯斯比尔,将罗伯斯比尔交给塔利安。他们将活着的马拉示众,将死去的马拉奉若神明。他们支持一切直到某一天推翻一切。他们最善于将摇摇欲坠的东西最后推倒。在他们看来,你根基深厚,他们才为你服务,你若摇摇欲坠,那就是对他们的背叛。他们是多数,他们是力量,他们是恐惧,由此产生公然的卑鄙行径。
由此产生了五月三十一日、芽月十一日、热月九日①这些由巨人结织,由侏儒解结的悲剧。
①分别指反吉伦特派的“行动日”、丹东被清洗、罗伯斯比尔被逮捕。
(六)
与这些充满热情的人在一起的是一些充满幻想的人。这里有各种形式的乌托邦:赞成断头台的好战形式与废除死刑的天真形式,它对帝王是幽灵,对人民是天使。有些头脑在战斗,有些头脑在酝酿。有人想的是战争,有人想的是和平。卡尔诺的大脑就想出了十四支军队,让·德布雷的大脑就想出了大同世界民主联盟。在这些狂热的雄辩之中,在这些响亮的吼声中,有一些含蕴丰富的沉默。拉卡纳尔沉默,但在脑中策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