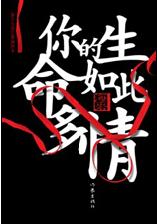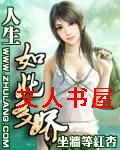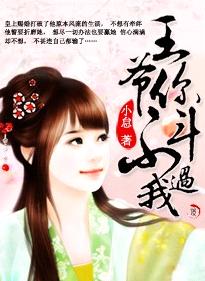不过如此-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78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
中国湖北武汉,老天和朴实的胡厚培一家开了个玩笑,老胡家这天迎来了呱呱坠地的儿子胡忆舟,却被诊断为唐氏综合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先天愚型。
舟舟的纯净(19)
舟舟常出去走动。公交车司机、售票员、附近商场的营业员都认识舟舟。舟舟不缺吃不缺喝。吃完喝完,舟舟模仿模特走一圈猫步,逗大家一笑。
舟舟喜欢音乐团排练和演出,喜欢拿一根筷子模仿乐团指挥。
乐团里的小提琴手刁岩发现了,他想,或许音乐可以开启舟舟的智力。
刁岩开始有意培养他,很长一段时间,舟舟不回家,住在刁岩那里。
舟舟终于登台演出了,穿着燕尾服,扎着领带,神气活现他指挥专业团队演出《拉德斯基进行曲》。动作潇洒、刚劲、富有节奏,一曲完毕,场内掌声雷动。
一位到乐团访问的德国指挥家看到了这一幕,老人很激动,他把自己的指挥棒送给了舟舟。
人们陶醉在神话中,此时的胡厚培却显得异常冷静和清醒、他说,舟舟会什么指挥,那是艺术家们配合他,哄地玩。一语道破天机。
这个爱心故事被湖北电视台张以庆编导全程拍摄,纪录片《舟舟的世界》打动了无数的观众。
2000年的春节,策划海啸、虎迪决定请舟舟全家和乐团进入《实话实说》演播室,重新讲述和演绎这个动人故事。
舟舟来了,噘着嘴,因为刁岩叔叔送他的呼机在旅途中丢了。
舟舟一个劲地说,烦死了。虎迪灵机一动,这不正是接近舟舟的好机会吗?
听了虎迪的话,我们买了一个彩色的寻呼机,买了舟舟最爱吃的鸡腿和可乐送上门去。果然,寻呼机一下响,舟舟就抱着我说,你真是好人,我喜欢你。
这一幕在节目录制结束时再次出现,舟舟抱着我说,你真是个好人。
舟舟不掺假,把我们也衬托得很纯净。实际上人们人之间交往就这么简单,都直来直去,能免去很多麻烦。舟舟的爱和僧是摆在桌面上的,不用你花心思主揣度。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弯弯绕还要留一手,一来二去,大家绞尽脑汁,头上生出不必要的条发。
春节期间,屏幕上挤满了色彩缤纷的晚会。这样一个非黄金时间播出的节目,还惹恼了一位天津的大爷。他在信上说,大过节的,播这个干啥,这不是一少部分人吗?
大爷,您听听辜鸿铭先生的说法。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或许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理应属于弱势群体,与这群人惺惺借惺惺。在我看来,许多方面,他们其实更健全,更强壮。
人生变化无常。孱弱,通常是暂时的孱弱,健壮,大体上也是一时的健壮,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一时一事去自卑和高傲。
在我们离开世界之时,有人喜欢分一分,有逝世,去世,死了,完了之分。
而我们没离开的时候则都是一种状态,活着。
民以食为天(20)
关于吃,民间有两条标准,吃饱吃好。吃饱在前,吃好在后。
由于工作忙,我回家看母亲的时间并不多,一进门,母亲洗手入厨房,忙碌起来。端上桌,看着我狼吞虎咽,母亲躲在一边垂泪。桌上摆的菜像双簧演员唱的那样: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
我最喜欢吃的只有两样东西:白菜,粉条。
许多朋友冬天都惦记着去我家弄一顿酸菜炖粉亲。热气腾腾,锅一开,雾气直抵屋顶。东西没进嘴,还不知咸淡,气氛已经先挑起来了。
其实,就目前家里经济条件而言,弄个百鸡宴不成问题,但,属于我的餐桌为何这样清淡?母亲一语道破:这孩子的胃,是困难时期打的底。
穷有穷的吃法。
按理说,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摆脱困境。况且,我还花去一年时间长牙,不至于食不果腹了。长大后,我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我的姐姐、哥哥经受了饥饿,在吃上是不挑不捡。尤其是大哥可怜,基本上荤腥不沾。大年三十,全家聚餐,餐桌上美味佳肴,大哥依然是一碟咸菜,半个咸鸭蛋。衬托得侄子、外甥们吃相可憎,像一群饿狼。
而我的吃高雅不起来,一是受兄长熏陶,分不清好坏,进入了吃的误区;二是想想当时情况,高雅也高雅不到哪去;第三点可能是乍富还贫时,捡好的吃,没节制,吃顶了。
天下的母亲首先觉得对不起孩子的就是吃,依次下去才穿和玩。所以母亲讲起吃来,很像《红灯记》里面的李奶奶痛说革命史。1960年,父亲在部队挣的钱不少,到了北京站,3个孩子看见卖鸡蛋的挪不动脚(那时没我),父亲掏出一张大票去买鸡蛋,却被告知要排队,而且每人只卖一个。于是父亲就一次次排队,第一个孩子吃时,第二、第三个孩子看,第二个孩子吃时,第一个孩子已经吃完,连同第三个孩子接着看,父亲排得大汗淋漓,让每个孩子都吃了两回鸡蛋,而父亲、母亲却没舍得吃一口。
我开始对吃有印象是在1970年。林彪说要打仗,必须疏散,一声令下,我们被车拉到燕山脚下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子里,和朴实的农民成了邻居。
他家的吃,让我着了魔。树上开的花可以吃,叫槐花;嫩树权也可以吃,叫香椿;面条是灰色的——杂面;米是红色的——高粱。加上红薯、南瓜,桌上一摆,五颜六色,正合饮食的色香味。
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家的饮食如此单调,忿然罢吃。急得母亲捧看雪白的洼面去邻居家讨换乌突突的杂面。几顿下来,我明白了一个便道理,吃起来容易拉下来难。
难吃归难吃,关键还是怎么吃。比如防空演习的时候,一伙孩子钻进地窖里,脚下磕磕绊绊的,摸起采像是吃食,塞到嘴里,有时是白薯,有时是萝卜。
房东大娘的那点宝贝让我们啃得七零八落,大妨还缺着牙慈祥地笑,每到傍晚,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总是听她高声训斥憨厚壮实的女婿:“吃菜,就知道吃菜!弄点白菜心都让你王八蛋吃了,看看,吃一口馍,就两口菜,王八羔子!”农村里,1970年,菜以稀为贵。
那女婿吃起来嘴很大,吃法是往里面划拉。骂声不绝于耳,他像没听见,抽空还冲我咧嘴笑。
疏散了几个月,就记了个吃。
那时我还小,整日无事,常被部队炊事班的叔叔招呼去玩。
吃在军营(21)
炊事班出了两个神人,一个有用少量鸡蛋做大锅蛋汤的绝技,看着蛋花满眼都是,想盛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于是下令在全团推广。另一个战士的绝技有点像现在的气功,简称“一刀死”,猪被捆好后一刀下去,喊都不喊,顿时毙命。表演那天,蛋花汤一举成功。
杀猪的战士上场了,先敬个军礼,回头逼到猪的近处。眨眼间,手起刀落,那猪高唱一嗓挣脱绳子,拖着刀飞也似地跑了,战士怔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彪人马追在猪的后面,猪跑个马拉松,累死了。
几个月后,搬回城里,炊事班的锅里也渐渐丰盛起来。周日是两顿饭,下午一最好,掀开锅盖,满眼是肉,那锅的直径超过一米,铲子被换成了铁锹。炊事班;小白话不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喜欢我,发我两根筷子,把我抱到锅台上蹲下,他“转身去忙活别的事,小小的我在沸腾的大锅边探着身子寻大块的瘦肉。
第二次就被母亲发现了,她尖叫一亲于是规定。以后不许独上锅台,大锅饭,就要大家一起吃。
开饭时,我抱着碗,站在队尾,先是连、排长总结和布置任务,然后唱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一二三四”最后是连长一声急促果断的号令:“开饭”。战士们呼地一声把饭桶围个水泄不通。我挤近包子桶,包子已经没了,转身冲向馒头桶,徘长叫住了我,只见他两根筷子,每根串着四个大包子。边吃边传授抢饭的经验,不用看,只管使劲戮。
盛汤的口诀是:溜边沉底。为的是那点干货。
战士们吃饭突出一个快字刻钟,人去盆空。
细嚼慢咽在这儿用不上,因此个个练就一副铁钢牙合金胃。可怜的我只学了个形式,吃得倒是快,每天胃都疼。得五香粉的味道很重。
这些年又有去部队的机会,感觉饭菜吃起来和民用的没什么不同,倒是1978年去新疆边防采访,吃到了军绿包装的罐头,听我一个劲夸好吃,一个小战士趁四周不备,贴着我耳朵说:“好吃?你天天吃一个试试广大约是在1971年,出了炊事班碰上了,饲养员,饲养员了一块黑豆塞进我兜里,让我当零食吃。黑豆用盐炒的,很香,豆饼香过黑豆。等到傍晚回家,看见桌上的炒鸡蛋,没来得及说话,先吐了满地。急忙送到卫生所,小卫生员输液哆哆嗦嗦不到血管,母亲气得说,广天去三个地方这孩子快成你们部队的试验田了。
临近粉碎“四人帮”时,主食已经不成问题,副食还是跟不上,零食就更是少得可怜。百个伙伴带我去野外,吃一种叫野葡萄的果子。那东西长得小里小气,吃起来味道酸甜。另——种是酸枣,长在城墙外边,危险自不必说,吃几颗酸枣要扎半身的刺。
(22)
我家一个女邻居头发弯弯曲曲,总说自己是上海人,那时候说是上海人就像现在说是火星人。
不知道上海在哪儿,并不妨碍我对她不屑。母亲却认真地说:她说是就该是的。果然,那女邻居失踪了一段,再出现便说是从上海回来了。母亲去串门,拿回来一个小塑料袋。告诉我里面装了10片对虾片。
母亲坐在床边发愣,一定是在想做馅还是单吃。最后她决定让身单力薄的我独自享用,于是小心翼翼地取出虾片放在热水里煮。过一会去看,虾片消逝得无影无踪。
家里男女老少加上猫都被母亲怀疑一遍。
春节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物资突然间丰富。家家户户囤积起来,单等除夕一到,大开杀戒。
除了购货本上的每人半斤花生,二两瓜子,部队居然还搞到了栗子。可能与驻扎地有关吧,历史上良乡的板栗就是贡品。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崔健这句歌词用在母亲身上很合适。母亲接精炒栗子的字面意思在门口的锅台上炮制,开始没声响,有声时一下就炸飞了锅盖。全家只好躲回屋里,隔窗观望。直到后半夜动静小了,才打着手电,一个一个找回来,好在有院墙,基本上是颗粒归仓。
春节买鱼买肉是个艰巨任务。带鱼要宽,猪肉要肥,不认识售货员门儿都没有。我二哥肩负重任去了菜市场。后院的赵姨、王姨在菜市场工作,排队的人多,火气大,弄得亲人不敢相认。赵姨挑上几条6指宽的鱼称给二哥,被一人看出破绽,问赵姨,为什么他的鱼那么宽,赵姨头也不抬:“赶上了。”那人一气,鱼不买了,转身跟二哥来到了肉秤台,眼睁睁看着一块大肥肉放在秤盘里,这次他不问王姨,问二哥:“你是不是认识她?”这回轮到二哥表演了,翻着白眼说:“谁认识丫的!”
晚上王姨下班直接来到我家,见到我妈劈头盖脸一顿指责,什么狗屁儿子,说不认识,还丫的。
这时,肥肉已经变成了油和油渣。母亲陪着笑脸给王姨说着宽心话,盛了一碗油渣让王姨带回家。王姨不要,说我还缺这个,就是说这事讨厌。
于是,俩人又笑骂一顿二哥,王姨这才起身回家。
有了油,另一种食品应运而生:油饼。
面是糖和的,一张张作出来,趁热吃。这天晚上母亲发现儿女们个个饭量惊人。炸完油饼再炸排叉,一种先旋转再油炸的面食,春节期间走亲戚,吃饭不规律,排叉随时可以充饥。
等我玩到下午回家时,伏窗一看,几十只麻雀冲进家里,在偷吃排叉。我飞也似地跑去告诉母亲,母亲二话没说,跑回家,第一个动作就是关窗。
几十只麻雀被生擒后分批吃掉。
除了麻雀,还有知了、青蛙、蚂蚱,逮着谁吃谁。
吃得有道理(23)
陆文夫先生笔下的《美食家》没法摘,一本书从头吃到尾,吃品与人品。
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开学第一天。外地同学带家乡美食,湖南的腊鱼、腊肉;内蒙的奶片;贵州的辣酱;河南的烧鸡。父母为孩子精心准备的半个学期的储备,通常是一晚上就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