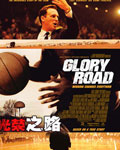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北方,瘟疫也同样扩展迅速,至1348年中期已直抵法兰西北部和巴伐利亚。当时,船只已经将“商人和海员携带的……首批瘟疫”传入不列颠的各个港口。英格兰众多城镇和乡村人口开始死去,教皇不得不“善意地宽容了所有悔过的罪孽”以希冀消除灾情。据同时代的人估算,大约只有不到10%的人最终存活了下来。其他文献上则说,死人太多,已经没有活人去掩埋他们。
穿越地中海的商船带回的不是货物和珍品,而是死亡和悲伤。病菌传染并非只通过瘟疫死者或船上常见的老鼠,船上的货物同样是致命的传染源。跳蚤会藏到运往欧洲大陆、埃及港口、黎凡特和塞浦路斯的皮毛和食物当中。在这些地方,最先遭到感染的似乎是婴儿和年轻人。很快,疾病沿着商道传播,抵达了麦加,导致大量朝圣者和学者丧生,并引发了新的灵魂困惑:先知穆罕默德应该说过,7世纪袭击美索不达米亚的瘟疫永远不会进入伊斯兰的各座神圣城市。
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写道,在大马士革,瘟疫“坐在国王的宝座上施威,每天处死上千人,毁灭着人类”。开罗到巴勒斯坦的道路上死者遍布,野狗在撕咬着比勒拜斯清真寺(Bilbais)墙下堆满的尸体。同时在埃及北部的亚西乌特(Asyut)地区,纳税人的人数从黑死病前的6000人降低到了116人,降幅高达98%。
尽管人口数量的骤降可能包含着人群避难的因素,但仍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死亡人数相当巨大。“人类的所有智慧”对此都无能为力,谁都无法阻止疾病的扩散,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前言中写道。他还说,在三个月之内,仅佛罗伦萨就丧失了十万多条性命。威尼斯的人口也大幅缩减:统计数字均说,瘟疫暴发期间,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丧命。
对很多人来说,这好像就是世界末日的到来。在爱尔兰,某方济各会的修士在他关于瘟疫灾难的记录中用一段空白作为结尾:“如果将来万一有人能活下来,请将我的工作继续下去。”人们已经意识到世界末日将要来临,法兰西编年史中说天上“掉下了许多青蛙、毒蛇、蜥蜴、毒蝎和其他很多类似的有毒动物”。天上也有明显的表示上帝沮丧的迹象:冰雹席卷大地,造成数十人死亡;城镇和乡村被闪电击中烧毁,散发“恶臭熏烟”。
有些人,如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以及追随他号令的主教们,将希望寄托于禁食和祈祷。1350年前后写成的各种阿拉伯手册为穆斯林信众提供宗教指南,也建议采取同样的举动,并指示说,把固定的祷告词默诵11遍就会奏效,祷告词与穆罕默德的生平有关,默诵它就能免于脓疮。在罗马,人们庄严列队,跣足褐衣,自笞悔罪。
还有少数人想出其他办法来平息上帝的震怒。瑞典一教士强调,要禁止性生活和“任何对女性肉体的欲望”,因此不要洗浴,避免在午前吹到南风。如果说这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的话,英格兰的做法则至少比较直接:英国的一个教士说,妇女应该改变自己的穿着,为了她们自己,也为了其他人。奇装异服和暴露的运动服都将受到神圣惩罚,“她们戴上了毫无用途的头罩,纽扣和拉绳紧紧系在脖子上,面罩只能覆盖到双肩”,这还不算,“她们穿一种短衣(paltoks),很短,甚至盖不住屁股和私处”。其他都不说了,“关键是她们穿着这些紧身衣服便无法给上帝和圣人跪拜”。
在德国还流传着一种谣言,说瘟疫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犹太人在水井和河流里投的毒。于是人们开始实施一个邪恶的计划,据说德国人将“所有从科隆到奥地利的犹太人”统统抓起来活活烧死。反犹太热潮开始爆发,教皇不得不出面干预。他发布指令,禁止在基督教国家对犹太人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并要求所有犹太人的财产和资产都应受到保护。这项指令是否有效另当别论,不过由于对灾难、苦难和宗教泛滥的恐惧,在德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早已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莱茵兰的犹太人就因信仰不同而遭到迫害。在危急时刻,不同信仰的存在是非常危险的。
欧洲在这场瘟疫中至少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据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在2500万左右,而欧洲总人口数估算在7500万。后世对瘟疫的研究还表明,在大面积传染病暴发之际,小型村落和远郊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城镇。看起来瘟疫传播的关键因素并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人口密度,而是大量聚居的老鼠。疾病在人口众多的都市地区传播并不比乡村地区更快,所以其实,从都市逃往乡村并不能增加任何存活的概率。从田野到农场,从城市到乡村,处处是黑死病造成的人间地狱:腐烂的尸体,鼓起的脓包,大范围的恐怖、焦虑和怀疑。
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我们对未来的希望都随着朋友的死去而一起埋葬。”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这样说。人们对未来在东方谋取利润的野心于此蒙上了深深的阴影。彼特拉克还说,唯一的慰藉是,“我们还可以追随先人的智慧。我不知道我们的日子还有多久,但我知道那天很快会到来”。他写道,印度海、里海或是黑海的所有富商都无法弥补灾难造成的损失。
瘟疫带来了恐怖景象,但它也成为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催化剂。其深刻影响远不只是欧洲的死亡,它促进了欧洲整体的再生。这一变革为欧洲在西方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种影响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彻底重组。黑死病之后,人口长期缩减,导致劳工工资陡升,因为劳动力变得更抢手了。那么多人死于瘟疫,直到14世纪50年代,“侍从、工匠、技工、农业工人和普通劳工”的短缺状况才终于开始缓解。这为曾经处在较低社会阶层和经济阶层的人提供了相当大的谈价资本。有些人根本“对打工不屑一顾,除非有三倍的工资,否则极少有人入职”。有证据显示,黑死病之后的十年间,城市雇员的工资出现了巨幅上涨。
农民、劳工和妇女同样从有产阶级的衰落中感受到益处。地主和房主被迫接受更低的租金,有租金总比没有好。低租金、轻义务和长合同都让农民和城市租户获得了大量利益。这种状况还得到低税率的推动,14世纪和15世纪整个欧洲的贷款税率都大幅下降。
显然,随着财富在各社会阶层的分配日趋平均,人们对奢侈品(进口商品)的需求大幅回升,因为有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购买他们原来买不起的商品。瘟疫带来的人口变化还影响到了消费模式,特别是那些工薪族的年轻人,他们面前摆着各种新的机遇。新生代们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本来就不愿意省钱,挣的工资还比父母要多,前途更为广阔,所以愿意花钱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尤其是追赶时尚。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欧洲纺织工业的投资和发展,欧洲纺织品的产量巨大,导致亚历山大港进口规模的大幅缩减。欧洲甚至开始转进口为出口,他们的纺织品充斥中东市场。面对西方生机蓬勃的经济发展,中东不得不为经济紧缩感到忧愁。
近来对伦敦墓穴发现的尸骨研究显示,当时财富的增长促进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健康水平。统计结果表明,瘟疫之后的重大影响之一是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伦敦瘟疫的幸存者在身体素质上明显比黑死病暴发前的人更为健康,当然也使人的平均寿命显著提升。
欧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平衡。大陆北部和西北部的变革最为迅猛,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与南部相比经济水平更低。这意味着地主和租户的关系比较融洽,因而更容易达成适合双方利益的协议。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即北方城市与地中海城市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在地中海城市,几个世纪的地区及长途贸易已经形成了一些能够操控商业竞争的机构(如行会),由个别商业团体垄断。相比之下,欧洲北部的繁荣则是得益于在商业竞争方面没有限制,因此在都市化和经济成长上比南方更为迅速。
新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在欧洲各地出现。比如在意大利,女性一般不愿意,也没太多能力进入劳工市场,还像瘟疫暴发前一样,到了年纪就结婚,努力生更多的孩子。而在欧洲北部国家,情况却有所不同。这些地区的人口缩减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推迟了女性的结婚年龄,并对家庭规模产生了长远影响。“别那么着急结婚,”诗人安那?拜恩(Anna Bijns)在尼德兰(herlands)写成的诗歌中建议说,“能为自己挣到衣食的女人不要急着去忍受男人的棍棒……尽管我不反对结婚生子。没有束缚最好!祝没有男人的女人幸福!”
黑死病带来的转型为欧洲西北部的发展奠定了长期的基础。尽管这些改变还未在欧洲各地全面开花结果,但灵活的体制、开放的竞争,以及最重要的,意识到只有勤奋劳作才能克服北方恶劣地理条件从而赢得收益,都为后来欧洲在近代早期的彻底转型奠定了基础。正如现代研究所不断昭示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根植于瘟疫后的世界:随着产量的提升,人们的野心变得更大,财富不断积累,同时消费的机会也变得更多。
随着尸体被掩埋,黑死病逐渐成为一种恐怖的记忆(后有周期性的二次复发)。南欧同样经历了重大变革。14世纪70年代,热那亚想趁着大瘟疫给威尼斯造成重大灾难之际夺取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但这一赌局发生了巨大的逆转:热那亚未能发动一次决胜性的进攻,于是突然陷入了战线过长的困境。通过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一个个连接中东、黑海和北非的商业城镇据点,统统丧于敌手。热那亚败了,威尼斯胜了。
摆脱了宿敌的威尼斯,如今一切转入正规,可以专心从事香料贸易。通过亚历山大港进口的胡椒、生姜、豆蔻和丁香越来越多。平均算来,威尼斯商船每年要从埃及运回400多吨胡椒,与从黎凡特运入的数量相当。至15世纪末,每年有近500万磅的香料(用于食物、药品和化妆品)进入威尼斯,然后再以不菲的利润售往其他地方。
威尼斯还是绘画颜料的进出港。这些颜料通常被统称为“海外来的威尼斯产品”(oltremare de venecia),包括铜绿(verdigris,直译就是“希腊绿”)、朱红、胡芦巴、铅锡黄、骨黑,还有黄金的替代品,比如紫金(purpurinus)或彩金(mosaic gold)。不过,最著名、最独特的颜色是从中亚开采的青金石中提取的纯蓝。于是欧洲艺术的黄金时期——也就是15世纪法拉?安吉里柯(Fra Angelico)和皮耶罗?戴拉?弗朗西丝卡(Piero della Francesca),以及后来的米开朗基罗、利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和提香等艺术家生活的时代——孕育而出:一方面,与亚洲贸易的扩大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这么多样的颜料;另一方面,富裕程度的增加使他们有钱购买这些颜料。
与东方的贸易利润如此丰厚,威尼斯政府不得不对贸易权进行事先竞拍,以保证中标者在遇到生意、运输或政治风险时仍能得到付款。一位威尼斯人自豪地说,商船从城市出发可驶往世界各地:非洲海岸、贝鲁特和亚历山大港、希腊各地,还有法国南部和佛兰德。财富的流入导致意大利房价大涨,特别是在靠近里亚托(Rialto)和圣马克大教堂的黄金地段。由于土地稀少、价格昂贵,人们开始使用新的建筑技巧,如用节省面积的小型楼梯井替代富丽奢侈花园双向楼梯。不过,一位威尼斯人骄傲地说,就算是一个普通商人的房子,都会装有金顶天花板、大理石楼梯,阳台和窗户都镶着由附近梅拉诺(Murano)生产的精致玻璃。威尼斯是欧洲、非洲和亚洲贸易的最佳集散地,并且能够用优雅得体的形象展示这一身份。
兴盛繁荣的城市不只是威尼斯。达尔马提亚海岸星罗棋布的城镇都是进口和出航的停留地点。拉古萨(Ragusa,即今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见证了14世纪和15世纪的繁荣盛况。1300年到1400年间,当地的财富增长了四倍,人们不得不为嫁妆的价格设一个上限,以限制过高的消费。城市资金过于泛滥,人们甚至开始考虑废除家奴:家庭资产已经如此富余,继续奴役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付工钱好像不那么仗义。像威尼斯一样,拉古萨也在忙于建立自己的贸易网络,加强与西班牙、意大利、保加利亚甚至是印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印度的果阿(Goa)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并以圣布莱斯(St Blaise,守护拉古萨的圣人)教堂为中心。
亚洲许多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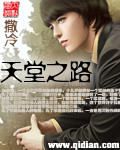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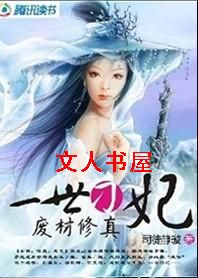



![[综]魔王的升级之路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2/296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