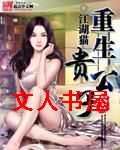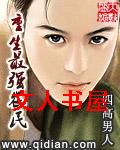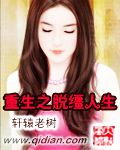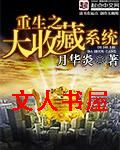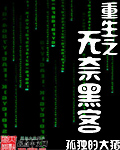重生之大业风云-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怜的女子。而今,向许安仔细探询,才知道这后宫之庞大,远超出我的想象。 杨广的后宫,有一个皇后,贵妃、淑妃、德妃三个妃子,顺仪等九嫔,以上倒还不算多,但是下面还有婕妤、美人、才人等世妇二十七人,宝林等女御八十五人,这些还是有品阶的,一般都得过皇帝的临幸,待遇不错,其他承衣和刀人,却是不计其数。近年来,皇帝每年都要从民间征集美女入宫,少则数百,多则上千。 我现在才深深体会到帝王的残忍。我决定,争取民心的下一步,便从这后宫开始。 十一月初六,下诏:东都、西都以外一切行宫,每处只留宫监1人、宦官10人、宫女数人看管;九嫔以下世妇、女御等,凡未生育者(杨广子女不多),听其自愿可自行婚配,按品阶赐银三百至两千两,其夫无官品者,授同品级散官(有职无权);承衣、刀人之类宫人,除留宫中日常所需,听其自行婚嫁,赐银五十两,夫家免三年钱粮差役;今后三年一征宫女以供宫中所需,每批不过百人,家中免三年钱粮差役,年满二十者,听其自行婚嫁,赐银五十两,夫家免两年钱粮差役。 诏书下后,世妇、女御等离宫者不多,但是大批低级宫女,终于可以重见天日,杨广啊,我占了你的躯壳,也不知道你如今魂归何处,就算我帮你积了德吧。不过,在这大批的离宫者中,并没有沈莺。 其实隋唐的时候,女人改嫁是很平常的事情。 十一月初八,宇文述大军班师,在则天门外举行“献俘”仪式。有旨:白瑜娑内叛朝廷,外结番胡,其罪当斩,今免其死罪,囚系终身,其余一百三十九人,处流刑,发配辽东效力,余众开释,发还原籍为民,官府不得为难。灵武之役有功将士,着兵部犒赏。 十一月十六,东北捷报。 本月初七,于仲文趁辽河结冰,率两万精兵夜越辽河,突然出现在辽东,猝不及防的高句丽守军被歼灭数百人,俘者近千,余者全部退进辽东城。面对防守严密的辽东城,于仲文遵照我“有利、有理、有节”和“有限反击”的“最高指示”,没有攻击辽东城,而是在附近大掠三天,解救为奴的战俘近千人,掠获高句丽平民五千余,然后将辽河东岸累累白骨收回,大军退回辽河以西。据于仲文奏报,共拣得尸骸十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三具。 十七日,圣旨:于仲文升从四品,一干将士,着兵部奖励;在武历逻城(辽东郡城)以南十里择地立“忠烈冢”,将阵亡将士遗骨安葬。其实东征军败的窝囊,阵亡者大多是死在溃逃的路上,不过死者已矣,就不必苛责了。 不久,大隋与高句丽达成协议:大隋归还被俘高句丽军民六千余,高句丽归还同等数量的隋军战俘。 这些日子,因为心底里对这些女子产生了一些歉意,我到三妃九嫔处的走动也勤了一些,虽然不曾临幸,但是也使她们心中多少有了几分慰藉,而我也终于仔细看了她们,倒的确不少国色天香。那贵妃是杨广登基以后所立,不过二十三岁的年纪,淑妃和德妃还要小些,还有九嫔中的一些,都还不到二十,其中萧嫔原是皇后身边的宫女,大业三年生下一个皇子,母以子贵,只是容貌在杨广的后宫里只能算作中等,仅封了个“修容”。 就这样,我迎来了在一千多年前的第一个新年。 总算羡慕皇帝,如今真的当了皇帝,才知道皇帝的日子并不好过,大年初一,还要起个大早,天色未明,就得接受一群儿孙的请安。这是我第一次见我的这帮“儿孙”们。 杨广的儿子其实不多,萧皇后有两个儿子:太子杨昭在大业二年就已经去世,留下了代王杨侑、燕王杨倓、越王杨侗,都是几岁的孩子;齐王杨暕,十八岁,原本是很有希望在杨昭死后立为太子的,可是近年颇不受杨广待见,连王位都有些岌岌可危,尚无子嗣。还有一个杨杲,就是萧嫔所生,不到七岁。 受完这平白捡来的“两子三孙”的礼,我还得颠颠地赶到金銮殿上接受一班臣子的朝贺,还要接见各国使臣。一天下来,实在累的不轻。 夜里,宫中举行宴会,皇后、妃嫔和皇子皇孙以及我的几个“儿媳妇”固然是要参加的,就是世妇、女御这等有品阶的,也得以列席,原本一共一百一十二个,因为我的“恩旨”,走掉十来个,却还有近百,其中不少,还是在我“康复”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和我近距离接触,一干合法的“小老婆”们少不得各自施展,以求我多顾上几眼,或者有希望“一沐圣恩”,皇后秉性宽容,也或者是这些年见得多了,再则她一直并不反对我和其他嫔妃在一起,所以并不干涉。而我却是第一次见到此等阵仗,心中近来有代杨广颇有愧疚,也不忍心粗暴—虽然我只需一声令下,她们就会顷刻间安安静静—对待她们,很是费了一番功夫,才算在许安的帮助下从“脂粉大阵”中“突围而出”。 我在皇后身旁坐下,佯作不满:“皇后母仪天下,这后宫,也不好好管教。” 皇后嫣然一笑:“姊妹们也是可心中挂记皇上,皇上不要生气才好。” 我扫视了一下,眼睛所到之处,不得不忍受上百道期盼、嫉妒和哀怨混杂的目光。其实内心深处,我很想能够看到沈莺,但是我也知道,她的身份低微,即便是能够来到宴席中,也不过是做个伺候人的差事,以许安的聪明,是不会考虑不到的。虽然我现在拥有足够的权力,可以让她从小小的“承衣”跨越世妇、女御而直接进入九嫔之列(册立妃子却还是要经过朝议的,多半得要出身高门),但是我现在内心中一直在挣扎—现在绝对不是可以“好色”的时候。 其实,内心里,我还有另外的顾忌,凭我从书本和影视中得到的经验,这后宫的勾心斗角,是非常可怕的(其实我现在也略有体会,比如前些时对皇后的流言),我若此时放着一大堆现成的“小老婆”们不管不顾,而宠幸一个宫女,那些妃嫔们会怎样?对地位高贵的皇后,她们或许还只敢限于偷偷的议论,可是对于沈莺这样的一个初入宫闱,单纯又没有背景的小姑娘,又会怎样? 这一夜,无论精美的食物,还是动人的歌舞,都没有让我产生什么兴致,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那个小姑娘的音容笑貌。当宴席散去,我身后留下的,只有一片失望。
第十一章 动心
我的赈灾、罪己诏、罢征令等一些措施,看来是取得了一些成效,灵武和辽东的两次不大不小的胜仗,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朝廷的威信,大业九年的局势,似乎要稍好于大业八年,也没有再听说新的叛乱发生。 不过,原有的叛乱依然存在,虽然我的“新政”限制了叛乱的规模,但是在山东、河北,那些已经造反了的人一时半会间是回不了头的,或者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想回头,过惯了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大秤分金的日子,已经不习惯再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良民”了。 早在正月初七,杜彦冰、王润等就攻陷了平原郡,大肆抢劫后离去。而我迟至正月十七才得到汇报,除开通信落后的原因,还因为大臣们怕坏了我过年的兴致。还好,因为我的要求,他们已经不会再把这些坏消息对我隐瞒到底。 我知道按《资治通鉴》的记载,本年正月和二月,在山东都有新的叛乱发生,不过当我向大臣们求证的时候,他们,连同我信赖的苏威在内,全都矢口否认。这使得我有些安慰:看来我还是改变了一些东西。 二月十七,我得到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使我对依然没有根本好转的山东、河北局势有了主意。 齐郡(今山东济南)郡丞张须陀于近日在泰山和黄河边两次大败王薄,斩杀过万。 这样一个捷报被快马呈送东都后,大臣们自然不愿耽搁,在第一时间就向我做了汇报。 老实说,一万多人被杀让我有些心寒,这毕竟不是外敌,都是大隋百姓,用句二十世纪的话,大家都是中国人啊。虽然咱不算觉悟多高,但是多少年的教育,还是明白不应该站在张须陀这样一个“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的立场上的,可是现在,张须陀就是我的一颗希望之星。并且,我知道张须陀也是算个好官,大业八年,齐郡和黄河流域其他地方一样遭灾,张须陀在无法得到远在辽东的杨广同意的情况下,冒着杀头的风险,不顾同僚的劝阻,毅然决然开仓放粮,称得上是之生死于度外了。而张须陀的作战能力,也的确相当出众。 二月十八,我命令下旨:授张须陀从二品兵部侍郎,领河南河北十二郡征讨安抚使,平定反叛,地方官吏必须通力襄助。并授张须陀麾下的虎将罗士信、秦琼正五品鹰扬郎将之职。 罗士信,据说就是《说唐(隋唐英雄演义)》里罗成的原型,十四岁从军,勇猛无敌。至于秦琼,大家就更熟悉了,不过这时他既没有上瓦岗,更没有跟了李世民,而是在张须陀的手下与农民军为敌。 我特地给张须陀写了一封信,连同任命的诏书一起送往山东:朕听闻你去年开仓赈灾,心中装有百姓,深感欣慰,现在又得到你大捷的消息,实在是朝廷在东方的柱石。朕现在把恢复黄河淮河间安定的大事托付给你,相信你一定不负朕的期望。不过你要记住,朕封你的是征讨安抚使,既要征讨,更要安抚,德威并用。那些变民,原本也是我大隋的百姓赤子,走上如今的路,朝廷也有责任,除开少数怙恶不悛者,不宜杀戮太重,有违天和…… 不知不觉间,春天就来了,北方的天气虽然暖的要晚上一些,不过过了春分,东都也已经草长莺飞、叶绿花开了。 我也忍不住,去御花园欣赏春色。 其实,我想看的,是一只“黄莺”。 她的小屋里,陈设添置了不少,床上的被褥,也精美了些,虽然比起其他嫔妃处,但她收拾的很整齐,也很温馨。大概是怕她一个人孤单,许安还特意在不远的另外一间小屋中安排了一个叫杜鹃的宫女,和她做伴。 她也不再是象前两次那样怕我,眉目间,倒多了几分羞涩。我唤她起身,她也不再跪着,我这才打量清楚,她大约一米五八的身高,浑身散发出的,是一种清新自然的味道。 “这个冬天,你过的可好。”我只能没话找话。 “谢皇上和许公公关照,奴婢好得很。” “手上的伤,该是全都好了吧?朕看看如何?”我说,她有些怯怯地把手伸了过来,我看见她微微用上齿咬了咬下唇,少女的些许娇羞姿态,更加甜美诱人,在我过来的那个时代,很少见到女孩子这般模样。 我牵住她的小手,这是我第二次握住她的手,便犹如第一次一样,心跳加速,不觉捏的紧了些,她稍稍有些把手回缩,却又不敢用力。 我知道自己有些失态,赶紧放开她的手,却已经看清,她原本白洁如玉的手背上,还有块蚕豆大小淡淡的红印,该是烫伤留下的瘢痕。 “朕去冬来时,听见你在唱歌,今日可否再为朕轻歌一曲?” “奴婢唱的,不过是些乡野粗俗的曲子,不敢有辱圣听。” “不妨事,朕喜欢听。”我说道。许安也插话道:“皇上要听,你就唱罢。” 于是她轻声唱起来:“春光好,花儿媚,碧空燕儿飞……”这该是民间唱春天的小曲,从她的小嘴里出来,格外悦耳,我不禁想起白居易的诗句:“大珠小珠落玉盘”。 等她唱完,我轻轻鼓掌:“好听。”在身上摸摸,却没有带什么东西,看看许安,帽子下吊了个小玉坠儿,于是一把扯下:“朕回头让他们给你补上。”我把小玉坠儿递给她,她却不敢来接,倒是许安在旁边说:“皇上的赏赐,还不赶紧收喽。” 我临离开她的小屋,突然想起什么,对她说:“春天来了,这御花园只怕也要不宁静了,朕若是和许多人来,你自管呆在你的小屋里,不要理会外面,朕若想听你的曲子,自会只带了许安来。” 出了小屋,走在路上,我问许安:“你怕她寂寞,安排个人照应,原本很好,只是不要乱传了出去。”许安回道:“皇上尽管放心,奴才精挑细选的人。” 说起来,对皇后,我更多的是出自一种“责任”和“义务”,我毕竟是“皇帝”,并且要人认同我是皇帝。当然,皇后的高贵、善良、善解人意,以及我所知的她的传奇经历,都使我对她颇有好感。不过,很难说这是爱情。 年后,在皇后的一再劝说下,我也偶尔到贵妃、德妃、淑妃和萧嫔那里留宿过一两次,除了萧嫔只能算长的还周正,其他个个都是国色天香。可是,这更不是爱情。 而对于沈莺,我体会到的,却是二十七岁的张明德的爱情,是那么真挚、热诚,却又藏掖着不敢示人。同样的感觉,在大学恋爱时,似乎也曾经有过,却又似乎不尽相同。 我去御花园的次数,慢慢多了起来,有时和皇后或者其他妃嫔去—我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