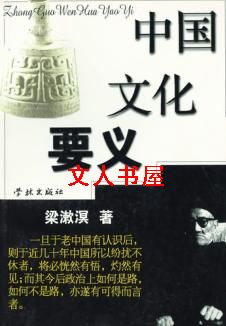文化苦旅(全文字)-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穿着白衣,年龄就不会很大,高个,瘦削,神情忧郁而安详,清晨的寒风舞弄着他的飘飘衣带,绚丽的朝霞烧红了天际,与他的银袍互相辉映,让人满眼都是光色流荡。他没有随从和侍卫,独个儿起了一个大早,诗人远行的小船即将解缆,他还在握着手细细叮咛。他的声音也像纯银一般,在这寂静的山河间飘荡回响。但他的话语很难听得清楚,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就住在山头的小城里,管辖着这里的丛山和碧江。
多少年后,我早已知道童年的误解是多么可笑,但当我真的坐船经过白帝城的时候,依然虔诚地抬着头,寻找着银袍与彩霞。船上的广播员正在吟诵着这首诗,口气激动地介绍几句,又放出了《白帝托孤》的乐曲。猛地,山水、历史、童年的幻想、生命的潜藏,全都涌成一团,把人震傻。
《白帝托孤》是京剧,说的是战败的刘备退到白帝城郁闷而死,把儿子和政事全都托付给诸葛亮。抑扬有致的声腔飘浮在回旋的江面上,撞在湿漉漉的山岩间,悲忿而苍凉。纯银般的声音找不到了,一时也忘却了李白的轻捷与潇洒。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力日渐减弱,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带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幸好还留存了一些诗句,留存了一些记忆。幸好有那么多中国人还记得,有那么一个早晨,有那么一位诗人,在白帝城下悄然登舟。也说不清有多大的事由,也没有举行过欢送仪式,却终于被记住千年,而且还要被记下去,直至地老天荒。这里透露了一个民族的饥渴:他们本来应该拥有更多这样平静的早晨。
在李白的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了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几句,我一直看成是当代中国诗坛的罕见绝唱。
李白时代的诗人,既挚恋着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着下江的开阔文明,长江于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他们知道,长江行途的最险处无疑是三峡,但更知道,那里又是最湍急的诗的河床。他们的船太小,不能不时行时歇,一到白帝城,便振一振精神,准备着一次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只能请那些在黄卷青灯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写诗了,那模样本不属于诗人。诗人在三峡的小木船上,刚刚告别白帝城。
告别白帝城,便进入了长约200公里的三峡。在水路上,200公里可不算一个短距离。但是,你绝不会觉得造物主在作过于冗长的文章。这里所汇聚的力度和美色,铺排开去2000公里,也不会让人厌倦。
翟塘峡、巫峡、西陵峡,每一个峡谷都浓缩得密密层层,再缓慢的行速也无法将它们化解开来。连临照万里的太阳和月亮,在这里也挤捱不上。对此,1500年前的郦道元说得最好:
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水经注》)
他还用最省俭的字句刻划过三峡春冬之时的“清荣峻茂”,晴初霜旦的“林寒涧肃”,使后人再难调动描述的词章。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让生命重重实实地受一次惊吓。千万别从惊吓中醒过神来,清醒的人都消受不住这三峡。
僵寂的身边突然响起了一些“依哦”声,那是巫山的神女峰到了。神女在连峰间侧身而立,给惊吓住了的人类带来了一点宽慰。好像上天在铺排这个仪式时突然想到要补上一个代表,让蠕动于山川间的渺小生灵占据一角观礼。被选上的当然是女性,正当妙龄,风姿绰约,人类的真正杰作只能是她们。
人们在她身上倾注了最瑰丽的传说,好像下决心让她汲足世间的至美,好与自然精灵们争胜。说她帮助大禹治过水,说她夜夜与楚襄王幽会,说她在行走时有环佩鸣响,说她云雨归来时浑身异香。但是,传说归传说,她毕竟只是巨石一柱,险峰一座,只是自然力对人类的一个幽默安慰。
当李白们早已顺江而下,留下的人们只能把萎弱的生命企求交付给她。“神女”一词终于由瑰丽走向淫邪,无论哪一种都与健全的个体生命相去遥遥。温热的肌体,无羁的畅笑,情爱的芳香,全都雕塑成一座远古的造型,留在这群山之间。一个人口亿众的民族,长久享用着几个残缺的神话。
又是诗人首先看破。儿年前,江船上仰望神女峰的无数旅客中,有一位女子突然掉泪。她悲哀,是因为她不经意地成了李白们的后裔。她终于走向船舱,写下了这些诗行:
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离去,谁
还站在船尾
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
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舒婷:《神女峰》)
终于,人们看累了,回舱休息。
舱内聚集着一群早有先见之明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出过舱门,宁静端坐,自足而又安详。让山川在外面张牙舞爪吧,这儿有四壁,有舱顶,有卧床。据说三峡要造水库,最好,省得满耳喧闹。把广播关掉,别又让李白来烦吵。
历史在这儿终结,山川在这儿避退,诗人在这儿萎谢。不久,船舷上只剩下一些外国游客还在声声惊叫。
船外,王昭君的家乡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激流把这位女子的心扉冲开了,顾盼生风,绝世艳丽,却放着宫女不做,甘心远嫁给草原匈奴,终逝他乡。她的惊人行动,使中国历史也疏通了一条三峡般的险峻通道。
船外,屈原故里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奇峰交给他一副傲骨,这位比李白还老的疯诗人太不安分,长剑佩腰,满脑奇想,纵横中原,问天索地,最终投身汨罗江,一时把那里的江水,也搅起了三峡的波涛。
看来,从三峡出发的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是怪异的。都会卷起一点旋涡,发起一些冲撞。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他们都不以家乡为终点,就像三峡的水拼着全力流注四方。
三峡,注定是一个不安宁的渊薮。凭它的力度,谁知道还会把承载它的土地奔泻成什么模样?
在船舷上惊叫的外国游客,以及向我探询中国第一名胜的外国朋友,你们终究不会真正了解三峡。
我们了解吗?我们的船在安安稳稳地行驶,客舱内谈笑从容,烟雾缭绕。
明早,它会抵达一个码头的,然后再缓缓启航。没有告别,没有激动,没有吟唱。
留下一个宁静给三峡,李白去远了。
还好,还有一位女诗人留下了金光菊和女贞子的许诺,让你在没有月光的夜晚,静静地做一个梦,殷殷地企盼着
洞庭一角
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
例子太多了。这次去洞庭湖,一见岳阳楼,心头便想;又是它了。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股子京重修岳阳楼罢,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直到今天,大多数游客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已成为一般中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熟语。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其他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
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罢。在这里,中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
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势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优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卷带中完全吞纳。
地是,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
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揪隘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确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优耶乐耶,也是丹墀金銮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意识,逼仄得多了。
而洞庭湖,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你看,正这么想着呢,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
朝游北海暮苍梧,
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
朗吟飞过洞庭湖。
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但是范文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这位道家始祖。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真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著与旷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抒,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
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至少,想着他,后人就会跳出范仲淹,去捉摸这个奇怪的湖。一个游人写下一幅著名的长联,现也镌于楼中: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史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沧然泪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他就把一个洞庭湖的复杂性、神秘性、难解性,写出来了。眼界宏阔,意象纷杂,简直有现代派的意韵。
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罢。我登船前去君山岛。
这天奇热。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记起了古人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这个“蒸”字,我只当俗字解。
丹纳认为气候对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以前很是不信。但一到盛暑和严冬,又倾向于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九月十五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秋空明净,可让他想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