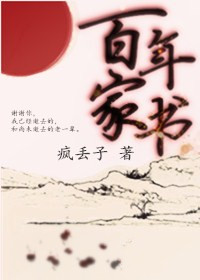傅雷家书-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傅雷在江苏路284弄5号宅院内(1961年)
傅雷在江苏路宅院内(1961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傅雷书房内(1961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1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院内(1961年)
傅雷与傅敏在寓所小花园内(1961年)
傅敏在北京女一中宿舍内备课(1963年)
傅雷与周煦良(1964年)
傅雷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的阳台上(1964年)
傅雷(1965年)
傅雷在杭州(1965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院内(1965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之阳台上(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的阳台上(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院内(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5年8月)
1965年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之阳台上。1966年9月3日凌晨含冤弃世于此。
1979年4月26日追悼会后,傅聪和傅敏送骨灰盒去骨灰堂
图为傅聪与傅敏(1981年)
傅聪与钱钟书和杨降夫妇在钱钟书宅邸(1981年)
1982年傅聪与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队在排练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1982年1月傅聪结束在京的演出和讲学后,李德伦和吴祖强在机场送行。(1982年)
傅聪在上海音乐学院讲学
1999年12月18日,三联书店在韬奋中心举办“艺术与爱的教育……《傅雷家书》座谈会”,傅聪和傅敏出席了座谈会。
图为傅敏在讲学(2000年)
图为傅聪在昆明演出(2001年)
傅雷摄影作品
黄山(云海)1956
黄山(散苑精舍前之日出)1956
黄山(始信峰古松)1956
黄山(狮林精舍的云海)1956
纪念傅雷…施蛰存
1966年9月3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二十周年纪念。这二十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15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几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1939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1943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于翻译罗曼·罗兰。这一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例。他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我说,依照你的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他说“对”。我说:“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
傅雷有一本《国语大辞典》,书中有许多北方的成语。傅雷译到法文成语或俗话的时候,常常向这本辞典中去找合适的中国成语俗话。有时我去看他,他也会举出一句法文成语,问我有没有相当的中国成语。他这个办法,他也不以为然。我主张照原文原意译,宁可加个注,说明这个成语的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某一句成语。当然,他也不以为然。
1958年,我们都成为第五类分子,不便来往,彼此就不相闻问。不过,有一段时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她们俩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间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况。
1961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于是我又常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衷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的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雷逝世,其实我还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书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地了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他要把他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他的理想的人物。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洁白的纪念碑……读《傅雷家书》…刘再复
一
翻译家死了,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留下了一颗蓄满着大爱的心。
二
纯真得像孩子,虔诚得像教徒,比象牙还缺少杂质。
三
把全部爱都注入洁白的事业,像大海把全部爱情都注入了白帆。
四
莫扎特的曲子中醉了,因为畅饮了善的纯酒。能在善里沉醉的人,才能在恶的劫波中醒着。
五
雪,任凭风的折磨,雨的打击,总还是一片洁白。
六
人的意志可以把雪抛入泥潭,但不能改变雪的洁白的颜色。
七
我爱默默的白塔,翩翩的白鸽、白鹤与白鹭,但更爱洁白的、不被尘埃污染的心怀。
八
比诗还令我泪下,比小说还动我情感,比哲学还令我深思。征服人的心灵的,是心灵本身。
九
心灵是文学的根抵。伟大的文学仰仗着心灵的渗透力,把高洁的芬芳注入世界。
十
未能发现心灵的潜流,只能盘桓于文学的此岸,感慨彼岸他人笔底的波澜。
十一
是时代的镜子。显示着一代天骄怎样闪光,怎样凋残,怎样怀着忠诚,至死还对故土唱着亡我的爱的恋歌。
十二
是心灵的镜子,照着它,能使人纯洁,使人文明,离兽类更远。
十三
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
十四
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十五
不懂得珍惜水晶心,那是真正的不幸。
十六
碎物的珍珠不是悲剧,毁灭心的珍珠才是悲剧,被毁灭的价值愈高,悲剧就愈加沉重。
十七
应当为失去江山国土而忧愤,也应当为失去洁白的心灵而忧伤。
十八
正直的战士,保卫着祖国的森林、海洋、城廓和田野,也应当保卫洁白的心灵和智慧的前额。
十九
纪念碑飞翔了,洁白复归了,我感谢春天母亲的情怀,她懂得爱,懂得珍爱那些和自己的乳汁有着一样颜色的儿女。
赤子之心…傅聪谈傅雷
北京饭店长长宽宽的走廊里,冯亦代先生和我匆匆地找寻着傅聪的房号——我们相约,在他养病期间作一次长谈。门开处,傅敏迎了出来,床上坐着微笑着的傅聪。这是一次尽情的畅谈。对祖国深深的爱、淡淡的愁,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对艺术的挚爱与追求,对父母的思恋和怀念……。沉静的傅聪竟是那样容易激动;以音乐为生命的他,却具有一副哲学家的头脑。记得一篇文章的开头两句话:“傅雷是傅聪的爸爸,傅聪是傅雷的儿子”。是的,同是那样的一颗赤子之心。
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
晓:《傅雷家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您有些什么想法,愿意向读者讲些什么吗?
聪:父亲一故世,欧洲就有好几个杂志的负责人问我这批书信,因为在国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那时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个出版社多次问我,愿出高价,我都拒绝了。原因是我觉得爸爸的这份家书是有永恒性价值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我不愿让它成为任何一种好意或恶意的政治势力的工具。现在由三联书店来出版它,我高兴,但有时也有些doubt。
冯:疑虑?
聪:这词不好翻,不是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疑虑,而是自己思想上的东西。格不同,难翻。我爸爸是个赤裸裸的人,不仅对我,对朋友也这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内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出来了。但这些信都是他五、六十年代写的,都带着当时的时代气氛和他的心境、情绪。虽然他一直是坐在书斋里的人,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连的。不过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会很不同了。
晓:那是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聪:这些信的价值正在于此。我刚才说我还有些doubt,就是说他在某个时期对自己作了相当多的解剖,自我批评,现在看,有一些可能还要回到原来的认识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到社会上去,看到了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到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补了课,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可是我觉得他原来的这个见解却是对的。经过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不行的,不择手段本身就把目的否定了。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的doubt。因爸爸在国内文艺界有一定声望,大家尊敬他,这些家书出版后,会不会对有些内容不能真正从本质上去了解,而只从表面上去看?
晓:人们会理解的。在当时,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那种虔诚,那种热爱。他急于要跟上新的时代,急于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时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改造自己、否定自己,是那样一种真挚的感情。
聪:也许我在西方耽久了。我认为一切信仰没有经常在怀疑中锤炼是靠不住的,是迷信。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对造成现代迷信也有责任,知识分子应该象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是最敏锐的,应该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爸爸说过:“主观地热爱一切,客观地了解一切。”我觉得这还不够。中国为什么走这么大的弯路?正因为中国人太主观地热爱一切,而不客观地多作怀疑,多怀疑就不会盲目闯祸了。爸爸基本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的“了解一切”,就包括怀疑。了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怀疑,先要提出问号。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执着真理,却又死死抱怀疑态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