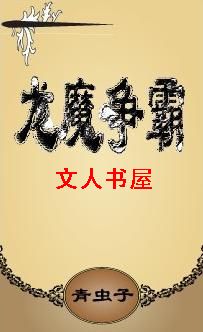狗日的战争-第6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乡亲们认出了翠儿,一个个打着招呼。山西女人大老远就招着手:“翠儿,俺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翠儿一个个招呼了,拉着驴走向自己的家院,她惊喜地发现堂屋竟然搭上了房顶,窗户也补好了,院子里的土也挖运干净,除了几堵院墙还是破的,竟可以住人了。
“袁白先生说你会回来的,就让人帮你弄好了……”谢老栓的女人说。
“翠儿当然会回来,还用得着先生说,俺还说让人把你的院子也收拾了,那帮干活的人都是些认钱不认脸的,修好了屋子就跑别人家去了,俺还说给他们几个小钱留下,可他们才不稀罕,说有的是大洋的活儿。这都什么事儿?什么时候打短工的这么神气,比那些老麦客还要牛气呢。”山西女人喋喋不休。翠儿心知她都在扯淡,自不点破,隔着墙头看了看她家,房子院子都恢复一新,窗棂还没上漆,窗户纸已经贴上了。
“各家各户都分了米,够吃小半个月的,你的那份儿在袁白先生那儿,翠儿,娘家还好不?”山西女人拉着她的手问。
“哦,还好,还好……”翠儿不知该如何回答。她走快几步,甩开她的手进了院子。
院子里的土挖掉不少,剩下的都踩实了,虽然没原来清爽,踩上去松松软软的,但毕竟已是能站能坐的院子。桂花树枝叶轻摆,活得自是滋润,树下的蚂蚁窝不知踪影,它们算得到刮风下雨,却算不出黄河决堤。房屋的老土坯晒干了,下面楔入了加固用的木锥子。屋里的土她早就清理过,进去便闻到新草和油毡的味道,抬头看到久违的房顶,像吃了颗定心丸一样。
有根在院子里蹦了会儿,在树下执着地扒着蚂蚁窝,翠儿找到一把扫帚,扫着满是土的碾盘。扫了几下就觉得错了,这算什么紧要事儿?她忙抱着孩子出了门儿,寻到坐在太阳下的袁白先生。三月不见,先生像老了十年,一张脸受气包似的。袁白先生手搭着凉棚,见是她就笑了。
“回来了呦,还胖了呦。”
翠儿呵呵笑着,笑着笑着就想哭,她想把真话告诉他,这是她在村里唯一信得过的人。但她还是忍住了,别给老爷子心里添堵了。他一个宁死不吃鬼子食儿的倔老头,又能帮你什么呢?再好的宽慰,抵不过半碗填肚子的稀粥,不如一方遮风挡雨的房顶,一面干干净净的土炕。
“先生却瘦了,但气色还好呢。”翠儿拿出一包茶叶递给老头说,“这是给你带的好茶,说是毛尖儿,俺不懂,就拿了。”
“嗯,是好茶呢。”袁白先生闻了一下说,“娘家还好?”
翠儿嘟着嘴,假话在舌尖打颤,先生淡淡地看着她,像是知道她要说什么。“娘家没了,爹妈也没了,俺在别的村儿避了避,先生,俺不想让人知道俺就是孤儿寡母了,俺不想让人可怜……”翠儿咬着嘴唇,忍着涌上来的泪。
“娃啊,宽心点儿,带好有根和肚子里那个,老旦会回来的。”老头看着远处的筒子说。
“先生咋知道俺有了?”翠儿惊道。
“你走过来的时候俺就看出来了,俺脑袋糊涂,眼神儿还好使哩。”袁白先生笑起来,“你气色甚好,眼睑明亮,这也都是妊娠之色,回来就待住了,板子村往后八成饿不死人了。”
“听山西子说饿死了十几个……”翠儿坐下了。
“都是些老不中用的,死了就死了,我做的主,只许小吃大,不许大吃小,粮食都让给年轻女人和孩子了,有她们村子就在。我也想饿死算了,被她们弄活了。”袁白先生说得随意,翠儿却听得浑身冰凉。
“先生可不能走……先生,既然你知道了,就给我这肚里的孩子再起个名儿吧?有根是你起的呢。”翠儿推过有根,孩子是个懂事的,扑进袁白先生怀里,一下下摸着他的白胡茬。
“早就给你想好了,既然有了根,如今就只剩个盼,就叫谢有盼吧。”
“是个小子?”翠儿惊喜道。
“嗯,是个小子。”袁白先生不假思索道。
第二个果然是儿子。翠儿那天正在村口挑着给孩子做衣服的花布,肚子里像开了锅,叫了一会儿,下面就和开了闸一样。翠儿走不回家,觉得自己像颗裂缝的鸡蛋,正流出黏黏的橙黄,她扶着炮楼边的一棵树就倒了。村口只有卖布的卖梨的卖鞋的卖烧饼的,他们都哇啦啦喊着,但没人敢走向炮楼子这儿。伪军们看见了,金牙兵几步跑来,知道她要生了,便让另一个兵去村里唤接生婆。树坑里流下殷红的血,翠儿开始号叫。几个鬼子被吵了午觉,穿着背心出了炮楼。翠儿大惊,想爬着回家,却哪里动得了。小贩们不敢来,金牙兵也不敢碰,村里人还得过一阵才来,来也不敢来几个人。翠儿知道这下完蛋了,早不生晚不生,偏偏这时候。
几个鬼子走过来,看着翠儿的情形,咕噜噜彼此说了几句,翠儿认得最高的那个是田中一龟。他看了看情况,似乎也认出了翠儿,对金牙兵板着脸说了几句,金牙兵哈伊点头,唤来几个伪军。
“太君说了,就近到炮楼里面生,把接生婆给你叫来了,那里阴凉背人。”他们不由分说抬起了翠儿,连汤带血地抬进那黑乎乎的炮楼,放在木头楼梯上。几个鬼子哇哇叫着,翠儿身边跑过拿枪的家伙,一个平头鬼子瞪着栗子颜色的眼低头看她,嘴咧得能塞进个小窝瓜。接生婆就是谢老栓的老婆,她并非精于此道,只因是板子村手最小的女人。谢老栓的女人脚不沾地被一个伪军拎进炮楼,她哆嗦着挽起袖子,要扒去翠儿的裤子,见一群鬼子环视在旁,便犹豫着下不去手。
“赶紧的,谁爱看谁看!”翠儿抬头大叫,这孩子撕裂着她,势如破竹样顶着她。田中说了几句,他们就扭过身去了,还有说有笑的,似乎在打着赌。谢老栓的女人麻利地干起来。“这小子倔,腿和鸡鸡先出来了。”她在下面拧来拧去,塞了又拔,像揪着赖架的老丝瓜。翠儿疼得嗷嗷的,说你赶紧把这小子弄出来,俺恨不得抽他两巴掌。谢老栓的女人说那你要使劲啊,就是拉屎你也要使劲儿,别说生个鸡鸡娃子了。她环顾左右,说看有啥给她咬的,她使不上劲呢。
“玉米棒子,玉米棒子,那玩意儿好使。”汉奸刘不知何时钻进来,撸着袖子像要帮着接生一样。
金牙兵跪在翠儿头前,将一只干玉米棒子卡进她牙口里。翠儿啊哼一声,棒子咔嚓就断了,一个鬼子看见了,往她嘴里又塞了个东西,翠儿咬进去,知道是圆圆的木头,眼睛斜瞟,才看到还有个铁疙瘩。可这下有劲头使了,一口气立刻奔着丹田去了,她听见扑哧一声,觉得五脏六腑都喷出去了,偌大个人只剩一副汗津津的皮囊。谢老栓的女人啊呀一声,又剪又擦地忙活一番后,托起一个肥嘟嘟的孩子,见他没动静,谢老栓的女人翻烙饼一样将他翻了个儿,一巴掌扇在腚上,有盼呜啦一声大哭起来,将鬼子们都震得回了头。他们低头看着有盼,一半欢呼起来。
“太君们刚才打赌,赌带把儿的都赢了。”金牙兵找来条毛巾包起了孩子,翠儿靠在楼梯边上抱过儿子,见他哭得响亮,小腿儿乱蹬,这十个月的苦一下子没了。她看着周围,这是什么样的一群啊!鬼子、汉奸刘、伪军、板子村的接生婆,不远处还蹲着一只大狼狗,它耷拉着舌头,莫名其妙看着炮楼里的人,比她还要不知所措。鬼子们嘻嘻哈哈逗着她的孩子,汉奸刘端来一盆温水,几个伪军乖乖地站在一边笑着,谢老栓的女人洗着有盼儿,一个劲儿说着车轱辘话:“你看太君多好,你看太君多好……”
翠儿恍惚起来,此情此景定是梦里一番混乱,那些可怕的事儿从未发生。她甚至怀疑郭铁头的娘是不是被鬼子刺刀捅死的,村民们验证了事实,说那老太太身上三个窟窿,都是穿个透心儿凉。翠儿无法将对她微笑的鬼子们和杀害郭铁头他娘的鬼子们合二为一,但她理解了这个矛盾,就像理解自己身上的矛盾一样。
“你命好,这孩子来得不易。”汉奸刘站在一旁,笑呵呵地说,“你傻呀,还不谢谢田中太君?”
翠儿回过神来,见鬼子们一张张陌生的笑脸,田中仍是板着脸,低头说:“生了,生了……”
这半年里,板子村起死回生,村庄去了污泥和尸骨,心头便去了阴郁。新的土坯房一个个盖好,一切又美好起来。村子还是那村子,但一切又仿佛不同。带子河还了曾经颜色,仍然不深不浅地流着。河里多了长腿的小鱼,吐着蚕豆样的水泡。庄稼地重垦之后肥力陡增。种下去的玉米像竹笋那样噌噌猛蹿;埋下去的菜种还没落雨便满地乱爬,南瓜结出了葫芦样子,花生结出挤满老头儿的长条,西瓜藤抢着架子,要和丝瓜一较高低,大杏长成了桃子模样,半夜里噗噗砸进土中;就连村里的野狗都换了性子,一身赖毛泛起油光,丧家的眼时常望月,它们挤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含着舌头一声不吭,尾巴轻巧地扫着落叶。
翠儿最怕的游击队一直没来,郭铁头也不见踪影。刀哥说的计划风一样没了,亦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刚回来的日子夜夜难眠,村口的狗叫,窗棂的抖动,都像是他们的到来。翠儿宽心地想,他们或许都被鬼子杀了吧?她虽然憎恨鬼子,但仍希望如此,如此,痛苦便成了秘密,而她会忘掉这些秘密。
没了男人的村子像不长果子的大树,再旺盛也没有收获的可能。女人们受够了回忆和想念,开始聊起村口的伪军和炮楼里的鬼子。有人说金牙兵长得挺俊,有人说有个长鸡胸的鬼子仪表堂堂,还有人说每逢周一在村口卖西瓜的小伙子有一口比瓷碗还白的牙。但说归说,没人敢动这可怕的心思。田中一龟据说对下面极严,一个伪军偷了村里一只没人养的走地鸡,竟被他当着众伪军抽了鞭子。传言说他以前是个唱戏的,有一副闷如老牛的嗓子,也有人说他有不大的双胞胎女儿,刚生出来半个月就到了中国。
炮楼时常也杀气腾腾,他们排着队伍早出晚归,偶尔也进村翻来翻去。炮楼上的探照灯总是惨白的光,夜里靠近的一只野狗被打成了烂肉。鬼子像勤快的毛驴,抢了公鸡的活儿,不管刮风下雨都按时折腾,一大早就光膀子蹦蹦跳跳,绕着磨盘样的炮楼跑个不停。伪军也得陪着,在后面哭丧着脸。村民们远远看着,开始新鲜,渐渐乏味,最终失了兴趣。只有山西女人倔强地坐在村口观望,在风里摸着她老黄瓜似的脸。谢老栓的女人说她想男人想得裆都烧起来,袁白先生说她也是个苦命孩子。翠儿什么也没说,她常听到山西女人在夜里的哭泣。那时翠儿觉得,几个月烂梦般的经历,是她必然要经历的磨练,那仍是老天的恩赐,就像曾决堤的黄河,给板子村带来死亡和绝望,也带来如今异样的生机。
袁白先生从那以后再不出村子一步,只关在屋里院里写写念念。鬼子前来搜查,全村只有他敢插着门闩。田中一龟似乎对他忌惮,或是敬重,还带着礼物登门一次,据说是求字去了。袁白先生装聋作哑,手抖得像打摆子的老绵羊。田中黑着脸去了,但出门还是鞠了躬。鳖怪知道惹不起,想哈着腰一直送到村口,被随田中同去的鬼子一脚踹在脸上,翻了三个跟头才止住。
转眼棒子也熟了,粗如小号的碗口。田中一龟带着鬼子和伪军,在一个傍晚为板子村掰下棒子。亩产是去年的两倍,乡亲们在地垄上敬起菩萨。鬼子们看来也不少是庄稼汉子,咔嚓咔嚓掰得熟练,全村几十亩地的玉米堆满了谷场。鬼子给板子村定了新规矩,按人头分够全年的粮食,其它的按价全部收缴,那价格比国民政府略低一成,却没人觉得委屈,大家心知肚明,鬼子和伪军出的人力可没算钱,有人说百里之外几个村庄颗粒无收,更觉这一炮楼鬼子的不易。不知谁在炮楼下摆了香案,供起大桃和馒头,老人向鬼子伸出大拇指,挂着翠儿不曾见过的笑容。
这里和融一片,外面一无所知。村民们接受了这幸福的事实,觉得杀人的鬼子只是抓壮丁的国民政府散布的谣言。说一千道一万,吃在嘴里才是真的,暖在身上才是真的,炮楼凶狠,但也只是条看门大狗,曾有的匪盗没了踪影,来年的丰收还将继续,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有盼长得和棒子一样结实,四岁的有根蹿得比桌子还高。翠儿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让房子和院落焕然一新,让屋里现出老家的光彩,小黑猫拐来只可爱的白母猫,屋檐下住下一窝黑色的燕子。媒婆们开始在这里走串,冬小麦开始泛黄,女人们开始泛骚,一切都像是要顺理成章,就像鬼子来之前那样。谢老栓的老婆又开始偷别人家的鸡蛋,全村奶子最大的谢小兰又招惹了几个不要脸的老鳏夫,山西女人和伪保长郭石头有些不清不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