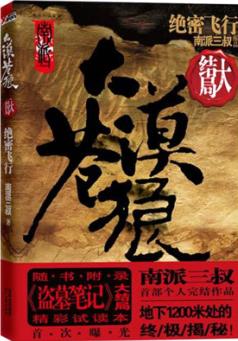苍狼与白鹿-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久,当东方发白的时候,最后一群人也消失于小丘的背后,原本热闹的营地已变成了一片旷野,只有铁木真一家的帐幕孤伶伶得被遗落在原地,苍凉得守卫着也速该的亡魂居所。
诃额伦下马,缓步走到被丢在原地无人收殓的察剌合埃不罕老人的尸体面前,双膝跪倒,将老人的头枕在自己的膝盖上,端详着老人那临终尤自义奋填膺的面容,将头深深低了下去,发出轻声的啜泣。铁木真带着合撒儿、合赤温、帖木格以及最小的妹妹帖木伦也一齐走上前,向母亲那样,在她的对面围成一个半圆,跪下来。
铁木真哭了,在父亲死时没有流出的泪水,在这一刻不可遏止得泉涌而出,为这乞牙惕族中唯一的勇士而痛哭流泣。面对部众离散尤其自坚如铁石的他,此时却痛悔万分,对这位不畏强权的赤诚老人,铁木真自觉无以为报。他所亏欠于老人的是一条性命,无价的性命!
诃额伦渐渐止住了哭泣,担心得看着对面号淘大哭的儿子,轻声道:
“蒙力克走了,捏坤台石和答里台也走了,就连锁儿罕失剌都走了。”
她细数着每一个熟人的离去,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也速该生前,都与她们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如今,却已不复存在。正如人们之前说的那样:“湖水竭,美玉灭,也速该,命已结,复以何言耶……”
“不,我们还在!”
铁木真倏然抬头,眼中闪着电光与雷火。他手指自己,随即又指向远处那孤零零的帐幕。那里有他的弟弟和妹妹。
他猛然站起身,向着天边每天照样升起的旭日长声呼喊着:
“长生天,请看吧!我——们——还——在——!我——们——还——在——!”
他的声音穿越呼啸的晨风,刺破空廓的苍穹,在茫茫草原之上回旋、荡漾,经久不息!——
(1)春祭乃漠北民族之旧俗。《元史。祭祀六》载:“每岁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后,于烧饭院中,用马一,羊三,马湩,酒醴,红织金币及里绢各三匹,命蒙古达官一员,偕蒙古巫觋,掘地为坎以燎肉,仍以酒醴、马湩杂烧之。巫觋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可见,这一次的春祀就是所谓的十二月十六日之后。
(2)她们其实是俺巴孩汗的遗孀。
(3)《拉施特书》作“箭入项部”。第一篇 黑暗的日子 第六章 家 族
第六章家族
压服部众叛逃终告失败,虽然诃额伦因其勇敢过人的表现(1)赢得了月伦额客(2)的美誉(今后,本书也将以此名呼之),但毋庸置疑的是,极其悲惨的生活阴影已经笼罩在一家人的头顶。留下来的除了最忠实的女仆豁阿黑臣之外,全部是也速该的遗族:月伦额客母子六人与侧氏速赤吉勒及其所生二子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十名老幼妇孺守着一座破旧的帐幕和少数几头羊马,孤伶伶得驻留在不儿罕山的斜坡上,被整个世界所遗忘。没有商队,甚至没有过客。生活的来源被骤然截断,牧民首领的家人瞬间变成了弃民。生存的威胁从未象现在这样迫近他们。
背叛者们撇下月伦母子,悉数加入了泰亦赤兀惕人在斡难河上游的营地,他们奉泰亦赤兀惕氏首领塔儿忽台为共主,组成了以泰亦赤兀惕人为主体的新的蒙古部落。关于这一切,月伦额客与铁木真都并不知情。荒芜的世界将他们与人间彻底得隔绝开来。
“怎么办?”小一岁的合撒儿神情茫然得问道。
铁木真用双手按住弟弟的肩头,向他宣布道:
“从现在开始,我将取代父亲的地位,成为一家之主,你和合赤温、帖木格就是我的第一批部下。你们必须绝对忠实、听话,不得违背我所下达的任何一条命令。打猎的时候,你们要跟紧我;放牧的时候,你们要时刻不离我的身边;如果别克儿帖和别勒古台来找麻烦,你们要与我并肩对抗。如果我倒下了,你们就继续听从合撒儿的命令。都明白了吗?”
铁木真用热切的眼光看着弟弟们,静静地等待他们的回答。月伦额客则微微抬起头,同样凝视着自己的次子。她意示到,这将是一个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的时刻。
三个孩子的小脸都涨得通红,尤其是合撒儿。比兄长小两岁的他有着一张俊俏的面容,挺得笔直的身躯几乎与铁木真等高,只是略显淡薄而已。却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样子,反而凸现出矫健灵巧之姿。他在沉默,并非因为犹豫,而是因为兴奋。终于,他稳了稳心神,带头说道:
“诺!唯兄长之命是听!”
接下来,合赤温与帖木格也一一表示了忠诚之心。跟在他们后面又响起了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
“帖木伦也要做哥哥的部下!”
铁木真伸出手去,将瞪着大大的眼睛,一路歪歪斜斜走向前来的小女孩抱了起来。用自己的脸紧紧帖住她的小脸,心中既感慨、又兴奋。
对于这个比风中芦苇更加飘摇不定的家庭来说,今晚的誓约是弥足珍贵的。虽然没有喝下血酒,对天献祭、祝告这样的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但每个立誓者都表现出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诚恳与严肃。即使是帖木伦,也许她现在还根本不懂“部下”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其用心之诚却是毋需置疑的。
从这一刻起,父亲也速该所留下的全家的重担就正式落在了铁木真的肩头,为了重新振作这个行将万劫不复的家庭,最初的从属关系和基本秩序被以誓言的方式确立了下来,并将维持至终身。也就是从这一刻起,铁木真的身份之中不仅包涵了长子的义务,更包涵了政治上的君王、战争中统帅、权威的立法人以及执法者等多重职责,建立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小国家。同样是这一时刻起,这样一个充满了苍凉、凄楚的有风的清晨,十岁的铁木真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这一步,对其个人乃至整个家庭而言,或许只是小小的改变,然而,对于草原牧民部落体制而言,却于无形之中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此前,没有哪一支家族的族长有过如此绝对的权威,更不曾直截了当地指定过继承人,家族成员也从未向首领立下如此绝对服从的誓言。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此时故然仅仅是因为了生存下去而悄然形成的,然则,当此家族日后对草原政局的影响渐趋扩大后,便会被推而广之的为更多人所接受。
诚然,做为其创立者的铁木真本人此时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此举的深远意义。他现在所做一切无非是为了满足全家的基本生存,其中还有一点针对于来自两个同父异母弟弟——别克帖儿与别勒古台的威胁。
这种威胁,从他们长得与铁木真一般高矮的时候就开始存在了。自从父亲死后,他在进出帐幕的时候也曾几次与两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双方六目交汇,彼此凝视的时候,铁木真分明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对方心底的强烈的排斥感与敌意,直至擦肩而过,彼此都不曾有一言之交。虽然自从童年时代起他们之间就从未有过兄弟般的亲近,然而那个时候也不似今日这样关系变得倏然紧张起来。以至于当铁木真与他们距离很远之后,那种如芒刺在背的感觉亦无半分消减。这就是他们传递给自己的感觉:与其说是自己的弟弟,不如说是两个比背弃的部众以及泰亦赤兀惕人更加危险的潜在敌人。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自己的视野之内,肘腋之侧。
果然,这种敌对倾向在不久后即转化为公开的对立行为。
※※※※※※※※※
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从不儿罕山脚下至斡难河边,就时常闪现着一位女子和几个孩子的忙碌身影。这便是月伦额客和她的五个孩子。他们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活下去,因为没有任何人会来帮助他们。关于那一段岁月之中的艰辛,在后世作者的笔下一首著名的歌颂月伦额客的诗中便可见其一斑:
那位贤能的诃额伦夫人啊,
独自抚育着她的幼子。
系紧她的固姑冠(3)啊,
扎束起衣襟在那腰带中,
来往奔波于斡难河的上下,
收集起野果杜梨和稠梨。
就是这样的日夜辛劳啊,
也才使得全家能糊口。
那位勇敢的月伦母亲啊,
亲手养育着她的英烈之子。
手持着桧木短剑啊,
挖起地榆(4)和狗舌草(5)的根,
就凭这样粗劣的食物啊,
也可让阖家人足饱一餐。
那位勤劳质朴的蒙古母亲啊,
亲手植起山韭和野葱,
吃着这些食物长大的孩子啊,
日后终成为天下之共主。
那位贤良方正的蒙古母亲啊,
用山丹之根来喂食诸子,
吃着这些食物长大的孩子啊,
后来成为英明的执政者。
那位容颜美丽的蒙古母亲啊,
在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中教育孩子,
就是这磨难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啊,
人人都是威名远震的英雄豪杰。(6)
这诗中的“蒙古母亲”,自然是指月伦额客而言。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称谓那么简单。当其日后,更推而广之为“蒙古民族之母”的重大意义。也就是说,月伦以其超凡的坚韧和高洁的母爱,抚育出蒙古民族的复兴之神,从而走上了与“光之圣女”阿兰豁阿并驾齐驱的至高地位,成为了所有蒙古族女性的光辉典范。甚至可以这样说,她也同样是全世界最为伟大的母亲之一。因为,她的事迹较之阿兰豁阿的神奇传说更为真实而直观,每个亲身感受过肯特山区那种严酷环境的人都无法置疑于其事迹的真实性并由衷地认同其当之无愧的地位。
与母亲的种种辛劳相比,铁木真的表现亦毫不逊色。十岁,这是一个怎样的年龄?当我们这些在自己十岁的时候做的是什么呢?无忧无虑的玩耍,攀住父母的脖颈撒娇,为了一件不能到手的玩具躺在地下打滚、哭闹。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十岁儿童的天赋权力,放诸四海而皆准。然而,在不儿罕孤儿们而言,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铁木真们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别说是男孩子们,就是帖木伦这样一个刚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女孩,也要跟着月伦母亲一起上山下河,终日劳作。环境永远是人类最为真实的导师,它总是会于潜移默化中教会一个人很多,很多。
“不能让母亲一个人如此劳碌!”
这是铁木真就任一家之主后的第一道动员令。然后,他为弟弟们分派了各自任务。在这其中,他留给自己的工作份额是最多最繁重的。每当天不亮的时候,他便第一个起床,然后叫醒三个弟弟,一起去畜栏中放出家中仅有的十匹马和十几只羊。而冬天的时候,由于一家人没有勒勒车,因而无法迁徒以避北方的寒风冻雪。而这个时节正是草原上众多食肉动物也因食物短缺,转而袭击家畜的高发期。为了保护全家人的命根子,铁木真只能独自一人睡在露天的畜栏之中,忍受着刺骨的风吹和令人四肢麻痹的雪地。一夜被冻醒几次更是家常便饭,而一旦猛兽真地袭来,他还要强忍着恐惧与之作殊死搏斗。合撒儿见兄长太过辛苦,几次提出二人轮流值班,可是铁木真却不放心他的体力,最终还是一个人支撑到春暖花开的季节。从十岁到十七岁,他就这样苦熬了七次花开花落。
每当他看到那匹率先出栏的银灰色骟马摔起漂亮的鬃毛,摆动健美的四蹄,发出清越的嘶鸣时,铁木真的眼中就会出现短暂的幻觉,他会不由自主得将一个人的身影添加到马背之上,随其一路跑出的富于韵率感的上下起伏而趋于生动。仅仅在这一刻,他觉得父亲还活着,依旧往来驰骋于家人的面前,用沉静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人,时而会报以赞许的微笑。说来,这一生之中,他还没见父亲笑过几次。然而,只凭那仅有的不多几次展颜之中,他便感到父亲笑的样子其实很好看,甚至于有一丝腼腆。过去,他总觉得父亲过于吝惜笑容,现在真正当家了才了解到,原来父亲并非不愿笑,只是被身上的各种重压抑制了笑的心情而已。
现在,铁木真不仅要带领着弟弟们终日放马牧羊,还要利用有限的闲暇时间去河滩边钓鱼以奉母亲。母亲太累了,可是仅有的羊又不能宰掉,只能补之以鱼肉,否则她很可能会因操劳过度而一病不起。父亲已经永远的失去了,再不能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失去母亲,不然今后的生活就只剩下一片黑黯了。至少目前的天空无论如何阴霾,总还有母亲用那双业已粗糙不堪,裂了无数小口的手勉力支撑着一丝缝隙,总算有一点阳光照落在自己以及弟妹们的身上,既微弱却又弥足珍贵。
但是,在铁木真的生活之中,更多的还是密云不雨的时候。大大小小的乌云叠梁架屋般在他头顶上织出一张又一张危险的罗网,这其中距离他最近的莫过于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
自从那个背叛之夜后,这两个人便一直采取自行其是的态度,丝毫没有承认铁木真新确立的一家之主地位的意思。最近,随着他们愈发健壮起来,挑衅的事件便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