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缘千里-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天雪下得很大。我们出了学校,在墙外头的野地里点上三堆火,围着火喝了几瓶酒,喝着喝着就哭起来,男男女女哭得跟傻X 似的。我喝得最猛,越喝越难受,都喝吐 我一个劲儿劝大家咱们到哪儿都是好汉, 以后永远也不哭。说着我又向大家赔不是,我打过不少人,我不对,一边说一边扇自己耳刮子。我拉着大明说下去以后咱们木兴闹不团结了,要抱成一个团儿,干什么都要一条心,决不能让那些土包子农民欺负 我跟他握了手,算是和好 不管怎么说,我们同学一场,又要一块难儿下农村,千万不能再窝儿里斗,得帮衬着朝前奔。大明还真算够意思,没撤火,跟我一块喝了酒。就是看着他和鸣鸣傍在一块儿心里有点发堵,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儿,装看不见就是
就那么满怀希望地下了农村,一下去就傻了眼,跟他妈劳改犯差不多。想再回来却回木来了, 死活得在广阔天地里打把式 这边方新并没有去什么进修学院,而是提升当了革委会副主任。听人家说他写了很长的报告,讲他怎么当好班主任把一个落后班变成了先进班,又教导一班人树立远大革命理想,初中毕业就奔向广阔天地,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个念英文的摘帽右派写的报告比谁都生动,引起了注意,成了“教育革命”的成果,北河市报登了他的先进事迹,从此这人就发迹大学开始招生以后,他又成了热门人物,因为他这人教英语是一把大拿,第一年就教出了几个英语大学生,出了名。想上大学念英语的全投奔了他门下。老天爷保佑着他,一顺百顺,一事顺,事事顺,什么时候他都得意。当校长,人党,又混成什么政协委员,还参政议政呢。他肯定早就忘了这一班人,十六年前的这一班,不过是他教过的几十个班里的一个, 过去就过去 人家现在关心的是大事,要木是得了癌症,还不是天天得意?我怨恨过他,特别是刚下乡那阵子。听说他没去教师进修学院而是当了革委会副主任,肺都快气炸 在知青点儿里一到晚上黑灯瞎火的时候,我们就凑一块儿臭骂他一顿,恨不得回城来找他算账。最恨的还是我自己,恨自己斗不过他这个老狐狸。十八岁上,老以为自己长大了,是个人了,到了儿还是人家刀下的一盘菜。
可事到如今,倒该感谢他,特别是我该感谢他。要不是他把我们骗下乡去,我这辈子就跟鸣鸣无缘 也许早早儿的就破罐子破摔, 说不定哪一回玩儿命打架就连小命儿也折进去
鸣鸣彻底回心转意了,答应给我生个孩子,这回是真的。
唉,我他妈三十四了!这么快就小四张儿
尾声 烟柳
暮春时节,熏风遍野。北河城里柳絮纷飞如雪,钻天杨已飒飒起一城的嫩绿,把这无河之城无花之城浸润得清朗爽秀,自是别有一股翠微之气淡淡地发散自古城的街巷院落。这是北河最好的季节。
北河的大街上自然是难觅花影。追着潮流奔着现代化的街道两旁耸起着一排排条条块块住宅楼,看似车水马龙地繁华着,却是毫无美感地排列而已。经过如此整齐划一改造了的古街巷,古树已砍光不知去向,或剩下一个个光秃秃的树墩子,或植上一溜溜细细的小树苗,倒像似刚刚修起的一条条新街或战乱后恢复中的新旧间杂。这样的街上是没有春天的,更是难觅春光。永远是光秃凄惨粗陋的破败景象,一年四季一个模样。永远是更新的未直起腰杆那新的已成俗屋陋厦。
这些地方已经不是北河。
北河的春天似乎是在那些深深细细的胡同大杂院里。尽管那些百年老屋已败朽褪色,尽管那些大杂院堆垛着林立着透不过气地拥挤着碎砖头陋屋破棚子,那里仍有百年的古树,杨树、槐树、枣树、桃树、杏树和丁香,都在顽强地抽技,泛出新绿。那里的破墙根下坚韧不拔地钻出一枝枝树条子,碎砖缝儿里隐隐地绿着一线线青草,虽然让人踩得永远出不了头,却依旧一日绿似一日,像一股股绿泉蹿流其间。
最叫这些灰蒙蒙大杂院生辉的应数那些艳丽的桃花 一场春雨洒过, 桃树老秆新技会泛起古铜色的油光来,暗红的光泽如同漆过的红木家俱一般光亮可鉴。那缀满一身的粉红花朵娇艳耀目,衬得一座座院子生机盎然,里里外外透着喜庆。谁家的桃树枝子探出头未亮在墙头,半枝的花朵更是在墙缝中的绿草映衬下显得美丽珍奇,像是谁插上去的假花枝子似的,着实爱人儿。
似乎这里才是北河。这里才有四季。
护城河黑糊糊地绕旧城墙淌过,可河坡上却也是一片芳草妻妻,远看那河边绿柳白杨,也有绿烟霞蔚的景象。
就在古城墙下的河边民居中,有一座颇为雅静的四合院。院中几株红桃白杏交相辉映,树下一群孩子在做游戏。
丢,丢,丢手绢儿,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一对白发老人沐浴在阳光中,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
大雁北飞,呼啦啦掠过古城墙。
老人和孩子都仰头看那人字形的雁阵,看得出神。
“方爷爷,雁子干嘛要往北飞?”一个小女孩问。
老头儿眯着眼睛说:“北方有它们的家。”
“它们上南方去干什么?”
“南方也有它们的家。“他说。
“爷爷,您讲的不是北河话,”小女孩说,“像电视上香港台湾人讲的话。”
“爷爷不是北河人,”老婆婆说,“他是打南边儿过来的。”
“爷爷的家在哪儿?是香港台湾 ”
“哦,比那还远得多哩,越过大海,在离中国远远儿的岛上。”老头说。
“那就是外国了,对 ”
“对,是外国。”
“爷爷是外国人?”
“不是,爷爷是中国人。”
“我知道,”一个聪明的小男孩抢着说,“爷爷是住在外国的中国人,那叫华侨。”
“不对,”小女孩打断他的话,“那叫台湾同胞海外侨胞。”
“你真老外,那叫美华人!”又一个孩子显得比谁都聪明。
“你没看见电视上管外国的中国人叫美华人?那意思就是特别美的中国人。”
“什么呀,人家说的是住美国的中国人!叫美什么华人来着。”女孩说。
老头儿哈哈笑 老婆婆也笑得合不拢嘴。
“爷爷,告诉我,你是怎么上了外国的海岛,又怎么到北河来的?”女孩穷追不舍。
老头儿抬头望望院子南边的古城墙,山一样的城墙做了这四合院的一面墙。城墙上的砖头一块块剥蚀了,坑坑洼洼如累累伤痕。依稀可见墙上用白灰涂写的几米见方的大字,那还是“文革”初期写上去的吧——“三支两军万”,“岁”字早就让风雨冲刷干净 有鸟儿从破砖洞里飞进飞出。 城墙缝里这里那里斜斜地挂着几根树枝子,在努着劲朝天上长,鲜绿鲜绿的在春风中摇曳。
“爷爷就是一粒树籽儿,”他说起那个“儿”话音来仍然很不自然,说成“树籽——儿”,“一阵风把我吹到南洋,我就在那——儿长成一棵椰子树。又一阵风把我吹回祖国,吹到北河这地方,我就像这一墙的树枝——儿,有点——儿土,我就扎下了根——儿,歪歪扭扭地长成这个老样——儿。”
小女孩让他说得哧哧儿笑
老头儿却把自个儿说得泪光莹莹,噙在眼里,挂在长长的睫毛上,珠儿一般透灵。
这时一双大手从背后伸过来捂住老人的眼睛。
“难呀,这么淘?”老头儿问。
老婆婆笑着说:“你还猜木出来?还有谁敢这么着?”
老头儿抬手握住那双手,浑身一颤,“是海子!”
“爹,你刚才的话听着真像诗!”
“爹!噢,叔叔管他爸爸叫爹,说话像乡下人!”孩子们叫着跑开大家全笑
老头儿这才发现方文海身后的来客。
“天啊,今——几个什么日子,你们全来我这幼儿园视察。
全是我的施主,有失远迎。“
青木季子灿灿地笑着挽着李大明,向老人深深鞠一躬。“方老师这个小院儿真美,古墙、古屋,人面桃花。我要好好儿把它画下来,回日本去准能得大奖。”
“哎呀,Miss Aoki,你这样的大画家来画我的幼儿园,真叫老身荣幸。”
“方老师别客气,”青木季子说,“您就叫我季子,或叫我的中国名字秀珍吧。”
“那怎么行,您是国际友人嘛。”
“方老师,”大明说,“我这次是来辞行的,过几天我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
“你都后几回 ” 老头儿眯起眼睛,有点不快地问,“这些年了,你在中国还没安安生生呆上几天呢。这回又去几年?还回来不?”
“我有什么办法?一走就想回来,回来了又想走。反正国外有的是地方请我去做博士后。”大明说不下去,哽咽住
“那中国 ” 老人气急地问,“报上电视上,那么些个博士后不是都回来干得挺好。”
“方老师,”吕峰说,“你就别说他了,他这人就这德性。他在哪儿也呆不住。”
“还有你,也招人烦,”老人冲吕峰说,“三十好几了,没个稳当劲儿。赶紧娶个媳妇儿,安安生生过过日子,行不介”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刘芳笑嘻嘻地挽住吕峰,”我来拴住他。“
“你们俩?”
“对,”吕峰说,“找来找去,还是打小儿一块儿长大的好,老有说不完的话。”
“真好!真好!”老婆婆用袖口沾沾眼泪说。
“不过,”刘芳说,“他把我拐跑了,我得跟他天南地北地去流浪了,嫁狗随狗 ”
“你们都走吧,我们陪方老师,”许鸣鸣满面春风地说。“方老师,别管他们,他们就是脚野,可心里总会想着咱们。反正根儿在北河,还愁见不着他们?”
老婆婆抚摸着鸣鸣的手说: “闺女,有三个月了 别怕,好好儿保养,生了,送我这儿来, 我给你们看着,错不 你们的孩子都送我这儿来,老方还能教他们说英语,|Qī…shu…ωang|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特级老师去?”
“我准往这儿送,”冯志永说,“赶都赶不走。当年我没跟方老师学英文,我得让我儿子好好儿跟方老师念书。”
“我这儿学费可要的高,”老人说,“你们虽说给我捐了钱办幼儿园,可你们的孩子要进来,该交多少还得交多少,一分不能少。你得给我交日元。”他冲青木季子说。
“爹!”文海忙挡住他,小声说:“你尽乱说,人家是猪熊太太,和大明只是Lover 关系。”
大家全心照不宣地笑
一群鸽子从城墙上掠过,鸽哨清脆悦耳,直到看不见影儿了,余音仍在城墙头上缭绕不去。
这是1992年的春天。
跋 北河
写完《孽绿千里》这部小说,我几乎难以自己。人,谁个不是一粒树籽儿,任风吹送?谁个不像古城墙墙缝儿里的枝条,巴上一星儿土就扎根,就歪歪扭扭地努力向上长,往高里长?
据说笔者父系那个宗族曾经是西亚某沙漠之国里的一个小部落,三千年前不知让什么风给吹到了咸阳,被赐了个汉人的毕姓,就在渭河两岸撒籽儿长树。又不知让什么风刮得这儿一撮儿那儿一堆儿,寥若残星地不肯自生自灭。
终于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我在河北平原上的一座古城中找到了一星儿黄土,也就长起来。
凭着一种血液的感知或是远宗神灵的启示,我从小就不把那儿当成故乡,不肯认同。心流浪二十一年后我终于乘风远去,南下闽江。
自以为从此永远摆脱了那个异乡的阴影,自以为找到了儿时苦苦寻觅的“别处”
的生活。可是当我皈依了艺术,艺术之灵却在向我频频昭示:除非我心眼踯躅在那个我生长了二十一年的故地,除非我不断地乞灵于那口我从小就鄙弃的方言,除非我身在外乡心灵却一遍遍重温那段生活,我就无法获得形而上的再生。这是对我怎样的报复!
我不得不听从那个血流中有节奏的声音——附体吧,为你的故乡转灵:故乡就是童年。
这真叫残酷。我拒斥着与它认同,可我的故事叫我附丽其上。
每每闭上眼睛,每每双手抱气进入一个万籁俱寂的气场中,我眼前出现的竟是平时无论如何凭理性回忆不起来的儿时街景,包括大门口石狮子上的划痕。我相信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信息沟通。我在接收着二十几年前的频率和讯号。
我能一次次重温往昔的温暖童年感触,它使我年轻。
愿借唐代苦吟诗人贾岛那首《渡桑干》来观照这种心态。“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当我问或凭着办公楼的十几层高窗俯视灯火明灭中的京畿,我似乎并无特别的触动, 反而会抬眼向南遥望, 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沿三环路往南三百里就是那个“野火春风古城”。如果能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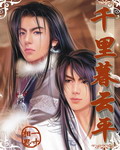
![[重生]修仙道之--躲不掉的孽缘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17/1727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