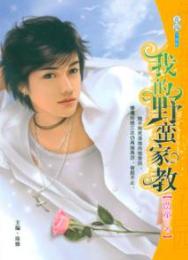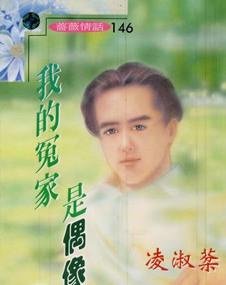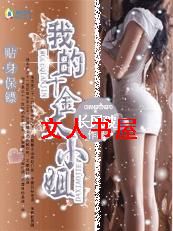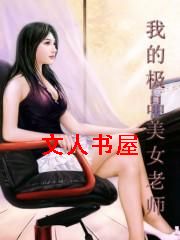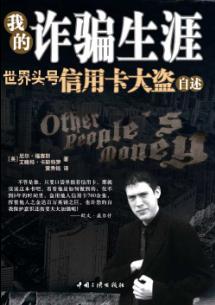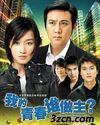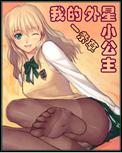�ҵķ���������-��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ԭ���ǽӽ������Ĺ��������˸��顣����δ�ܵĺô��ǣ�����С���۶���ֻҪ��˵�û��е��������ʱ���첱�Ӵ֣��������Ͷ����ˡ��ٹ����������ͳ��˷����ϵ�Ц��������ͷ����ĸ����������ر���С���۶������˶�һץһ��ѣ����ϸ�Ů�˿�����ô������֣�ȷʵ�Ƚ��ѵá���ʵ�ͺ�γ�����Ҫ����Ҫ�������������������ж�������������ľ����Լ��ǶԵģ���һ�����Ҫ��
�����������嵽�dz����۽�����Ǻ�����������ڵ�����Ļ�ϰ��ǵ����Ȼ���һ�£����ڷ����ˡ�˵ʵ�����Ƕ������Ƕ�ʵ��̫�ѿ��ˡ�ǰ��˵������ζ�Ǯ��ǿ������飬���������������������������������Ĺ���Ӱ�Լ�Ҳд������һ�仰�����Ů�������ӣ����Լ�����ʱ��С��������Ҳ��������߶�ȥ��
������������˵˵��ε����Ӻ�ǰ��˵��Ҫ��һ��ĺ�ε�����������������˵������������������ȽϺ�˵��
���������������Ū��һ����־�ǡ���I��
��������Look���綼�С���������������һ��ǵ�һ�����������һ������������˵������ʿ�ֵ�ר�����һ�����һƪ������˵�����ء�ʽ�����ģ�������һƪ���¡�����˵��֮ǰ������һ�����ϡ���Ū���û��С��С������Ҽ�����ʱ����־���棬��ƪ���¶ԡ����ء�������˵�������רҵˮ�ģ�Ωһ�������ǣ��������ʺ�һ��ʱ����־�ĵ��ӡ�
����������û�м���ʱ����־����˼��������Ȼ���൱������ʷʱ�ڣ�ʱ����־�����ǰ�������ӵ��˿��ġ��Ҳ���ð�����ߣ�����������ô��ġ�������ǰ׳գ�˭��ָ����һ��ʱװ������־�����һ������������ʷ���������һ��ǡ������͡��ģ�
����������ΰ˵��Σ�����
�����������ڿ�������ε�ʱ�������������������������Ϊ���뷨�����������߰���־���������棺��Ҫ��һ����˼����Ʒλ����־���������͵���һ������Ʒ��˼��ҡ���ʵ�������Ʒ���Ǻó�ʱ�䶼�������ü�Ǯ�����ܶ�˼�������һ����Ӫ�����������߹¶����ϻ����˶��������һ����ä�����˴˲�������֮����ε�ʱ�ܶ��˵�ӵ��һ������é®��������������ӵ�е�ȫ�������뷨������嶯����ȱ�ٶ���־�г�ӹ�ױ��ʵĻ����жϡ�
����������ʱ��ΰ����־û���ë��������ͨƪ�������֡�Ωһ�����⡱����ʵ���������ĵ�·�Ϻ��Ҳ���ǵ�һ��ˤ��ͷ���Ҽǵ�������һ�����£���ͷ˵���ǡ��ĵ�Ӱ�����ȶ���ǧ���ܸɵ��¡�����Ϊ�Ȱ���־��Ǯ���ˡ�֧������жϵĹ����������ģ���һ����һ��е����Ⱥ�ڳ��棬���������������Ƕ������ˣ����߶��������ǰں��˼���վ��ɽ����͵ȿ��ģ�ɽͷ�ϵ���ӰʦͻȻҪ�ϲ������ѻ���һ�������ˣ�ƫ���ϲ�֪��˭�����Ը������ij��ŵ���һɤ�ӡ���ʼ������ɽ��Ұ������������һ���ź����߾����dz�ͷ�������Ƶ�����������Ϊ���������ǽ����˵ģ�ÿ������һ�˾���10��Ǯ����ߵ���һ�����ã��Ͻ����Ŵ����Ⱥ������ܣ���β��㡱�����������Ĺ���Щ������������˵������������ú�ν���������ôд������˼�ö࣬˵������ǰ�����������ڣ�����Ҫ���Ǻ��˵����������Ѿ�Ӿ��ܵ�ʱ���ǹ�Ω�����²��ҵľ��������Ҽ����Ŀ�ͷ�����������ʽ��Ҳ���Ҷ��ĵ�Ӱ�������ֱ�ӵĸ�����ʶ��
��������������ˣ��ںܳ�ʱ�����γ���������������鹹����������ɧ�ű༭�������ɣ����־����Եر��������ij嵽��һ�ߵij嶯����֢״�ϱ���Ϊǿ�ҵı༭����������ᣬվ��ƻ�������Ա߱ȱȻ���������ͼ��һ������Ǹ����ô����ô�������߷��Σ�Ҫ�������е����ء���
����������λ��Ը���µ�����־����Ŀ�༭������ÿ��һ����Ϊ�����屻���I��
��������Lookǰ����ȫ��ȥ��һ���ൺ�����ѻ��������ڲ����������к�εĻ������衣���桶�֡�Լ����εĵ�Ӱ���ۣ�����ʱͦ�˷ܣ�һ�ڴ�Ӧ���������Ҹ������̣�������д��������������ܺã������˸�ͽ����ÿ��50��Ǯ�ķ���������3�죬���Һ��м�������ȥ�ļ��ƣ�Ū�����Լ������ù�û���ģ�˵ʲôҲ����������д�����ˡ�
����������ε����������DZ�һ��һ�εIJп���ʵ����ġ���һ��I��
��������Look�������༭Ū��һ��ѡ��С��ն���ͬ�Ĵ�Ѿ��Ѿ����Ѿ�����ҵ�����ģ�طֱ���һ������ʮ�����̫̫��һ����ʮ�����С�����һ���������СѾͷ�����������п������Ķ�����Ȼ��ק�����Ǻ�����ŭ���ߣ������Ǿ�����־�������ǿ���Ц����ʵ���Ǹ�ѡ���ڼ�ŭ����֮ǰ�ȼ�ŭ���������ڱ༭������º����ú�κܾ�ɥ��������Щ�µĺô�Ҳ�Զ����������ú��Խ��Խ�ӽ�һ�������������־һ���Ǹ�����Ⱥ�ڿ��ģ����Ը��˰��ú�ƷλҪ��������Ⱥ��ϲ���ּ���Ҫ��
������������������صĵ��������˺�θ����ҵ�һ�仰���������ں���Ƕ�ѧ��������Ҫ�Ķ���֮һ���༭��Զ���������������������������ñ༭�ͻ��༭��һ����������ֻ���ܲ���ʱ�������Լ����ݵ�������ȥ�����ˡ��������������ô����˵�ģ��������ϲ���Լ��������־��д��ȥ�������е�����
����������ε�ģ���������ˣ���ǰ���ᵽ��ѧ����Ⱥ�ڳ���ʲô�ģ�ֻ��һ�㷢��ˮƽ���ѡ��ⲿ���Ҳ�˵�ˣ���Ϊ�ܶ��˶����Ҹ��з���Ȩ������������˭ѧ˭��������µ���ѧ˭��˭���������������ߴ���ס���ˣ�Ӧ�ö����������ʱȽϺõ��ˡ�����Լ�����������Ҳ���ã�����ô����һ��Ƚ����ɡ���һ���κ����ȥ��һ��ʲô��Ӱ���������һ�˹�˾��������ײ���������Ҽ���������Ϸ��Ч���ĺ�Ρ�����һ����û�������·���һ����֪����Ϸ������ŵģ�û���ü������������ϵ�ױ��֪����˭�����ģ�������Ҫ�Ѻ�λ���һ����Ů�ˣ�����������������Եĺ�����������ֵֹģ�������ο϶��ͺ��û���κι�ϵ������Ķ������ģ���ô����ô������һ���¹ʡ�
������������Լ���ȻҲ�ܲ�����˼���ڹ�˾���������ġ���Ҫ�����Ǵ�Ҷ��ոճ��극������������ͷ�Բ�̫���������˵���仰��ʱ��ӭ�������ϰ�������ӣ���ƽ����������죬�ܵ�ϰ���Եط���һ���������������������ڹ�˾����˸�����������ı���ӡ�Ư�����ˡ�����Ư�����ˡ��������Ա�����ʵ�ڲ�����ͬ������ͬ����Щ���������ͬ�£������Ϊ���Ѱ�æ�����Բ����̻�ױʦ���Լ������������������Ǻ�ξ�ҵ����ľ������֮һ�����ҵ����⣬ͬ���Ǽ�ʹ���ޣ������ҲӦ���ǶԺ����������ľ��⣬������ʲôƯ����Ư��֮��Ķ�������Ҫ˵���Ǿ������Ҽ��������ѿ��ĺ�Ρ������ǵ���˾��ʱ���������գ��һ��Ǻ�С�ĵ�����20���ӣ������رܺͺ�ε������������ҵ�ʱ����ʵ�뷨�ǣ�һ���˸�Ū������ʵ����̫���ˡ������һ�����������ں������Ҫ�ߵ�ʱ��������������ˣ���ʱ������ǣ������װ��ʲô��û���������ӣ���Ȼ˵����ȥ����Ϊ�����������д�ں�����ϰ����Ƕ�������Ҳ���ʺϱ����ҵ���ʵ�뷨����Ϊ�Ժ�ε������ڳ���ͬ־�Ǿͷֲ�������Χ���ײ����ķ�Χ֮�ڣ����л���һ�����ҵ�ʱ�����࣬�����־�������˵�κ�һ�仰��������⣬�ҼȲ����ú�ξ�������������ˮ��Ҳ������ͬ���Ǿ�������Ϊ������������ˮ��ֻ��ֱ�㶵ظ��ڵ��ؿ�����������������Ȼ�Ǹ��ִ���������������һ�֡���ʱ��εĴ��������˾����ã���������һ�䣺����Ѿʲô����˵��˵�Ҹ��㼱�������̾Ͱ��Ҿ��ˡ���仰������������������������һ�ߵŰ����һ��ͷ������Ѿ˵˭�أ���֪����ɵ�������DZȽϴ����ı��֡�
����������ֻʣ��500����˵��ε����ӣ������ⲿ����������Ϊ��������Ҫ�IJ������ú�˵˵�ģ�����ֻ����ª�ͼ�
������������˵��5000�ֵ���ҵ������˹��Լ��һ���飬������ʮ�����֣������θ���������5000���Ǹ���5000�ֵ�һ������ѹ�����̾�С���ˡ����м���һ�κ�ι���˵���������DZߴ�绰��������С�㰡�������г��Ŀ������Ǿ��û���ϣ����дһд�ͳ¿�����¡�����˵�ðɣ��Ҿͼ�һ�£��ͱ��������ص����������
�����������д�úܺõ���ʣ���һ������I��
��������Look����д����Ů��СŮ�ˡ�ר�������ں���д��������С���ˡ����ӳ�ɫ�Ͽ�����Ҫ����һЩ����д�ֶ������ҷ������˲��࣬�����һ�������д�����������������ֱ���û�еĻ�����ǹ��е�����벻�ۡ���������������������������ĸ�����ͷ���Ե��˱Ƚ϶࣬�Լ���һƬ�������棬��Ȼ������뿪���ںó�ʱ������ߣ����Ժ���ȴ��һ���ر�����У�����д������Ȼ·���Ƚ��ر��ҵ�ʱ�뿪�Լ���ְ���Ǽ���ʳ���ǵı��磬����Ǯ��ɻ�����ܹ�������־��һ����Ҫ��ԭ������֪����һƪ�����˷����ء��Ǻ��д�ģ���������������Բ������һ�����ӵ���Ŀ���ͻ�����ƪ������Ϊ��Ŀ����ʱ���룬һ����д�����������ϰ壬Ӧ�ñȽ�����˼�������ˣ���û�뵽���ǣ���α�����Ļ�Ҫ����˼һ�㡣
��������д������ҷ�����ʵ����û��ôд�������ֿ����ڵĺܶ���ں�ε��������Ķ�������Ϊһ��д��Ϊ�����ˣ���֪���������ˣ�һ����д�����ıȻ��˸�����һ�㣬��һ���ǻ�ı�д�����ĸ�����һ�㣬һ���Ҹ�ϲ�����ߣ���Ϊ����ñȽ����������Ҽ����ĸ��������������棬����ڵ�һ��Ӫ��
�����������˵��ΰ
�����ÿ���txt������
����������ΰ�����������ģ�˵ʵ������Ҳ��֪������ô���ģ�ͻȻ�䣬I��
��������Look�༭�����˸�ʱ�������ӣ�ʱ��������Ĵ�ͷ�����˵��д�����²���Ӧʱ�п������������Ҳ�ò����Ƕ�ȥ����ΰ������϶����Ҷ࣬��ʱ���Ҳ���̫������ǰקʲôŷ����ʷ�������ѧ��ƭƭ�������㹻�������⺢���ҵõ��ġ���д�����£����������һ������һ�ַdz���������Ĭ���ر��ѵá���ϲ��������˼����Ц�����ߣ�����ΰ�Ķ�����Զ�����ȫ��
��������������ĭ���õĸ߳�������ͼ��һ�����ᡷ������־�����ڡ�WIRED���͡�RED��
��������HERRING��֮�䣬������һ������������˵����ʣ���ʱ���뷨���кܶ༼���ϵ����ϱ�����Ӣ�ķ�������ȵ����ڶ��벻������ԭ����֮���Ҳ������ĵ��˲����������ӹ�ˮ������������ˮ�������������ҽ�����һ�������ߣ����������Ů���ѣ���ΰ�����ù���ͱ���ȥ�����α༭�����Ǹ��dz�ʧ�ܵ���Ŀ������û�ɹ���������ΰ�ܹ����ܱ�ı����ҵ���������ᡣ����һ����ץ������ˣ����ҽǶȷdz������ڲ�������������û���ܱȵģ���֤��ʵ���������Ҵ�����֪���������������ô�����ϣ�������öൢ��
���������ҿ���һ���С��ܱ༭�����飬����д�������ܱ༭�ļ��ɣ������潲��һ�����£���ŦԼ�͡��ܱ༭���ˣ��ʣ������뵱���ң����DZ༭����
��������ӦƸ�ش𣺡����༭����
���������ܱ�˵����Good��������ŦԼ��ض��ǣ��ñ༭û��������
��������������Ҳ����������������һ���dz���������Һ����������༭һ����Ϳ����Ҫ�ѱ��˵ĸ���ij��Լ�����Ʒ�Ű��ݣ�ʵ�ڿ���֮����
����������ΰ�Ǹ������ң����Ǹ��ɹ������Ҳ��һ���ñ༭��
�����������ᡷ�����군�Ժ���ΰ��ȥ�����֡�����ʱ���֡��Ǹ���濯������ѵ�ֱͶ���й��Ĵ���ж��кü��������⿴�ijԺ����ֳ���ָ�ϡ��ɾ���û��һ�����й��˿��ġ�����Ҳ�;������ƺ��е�ֳ̫���ˣ��óԺúȺ���ĵط�ֻ��Ӣ�Ŀ�����й����ѵ����ؼҴ��ţ������ڶĿ������ǰ첻�ɡ�˵��ʵ����ʲô�г����鶼û�������֡�����֮����ܻ�ӭ����ΰ���ڡ��֡����˼��ڣ����չ����ڹ�濯���ÿ����κ����ݣ�����ûţ����ܵ����ഺһ�塷�༭��ȥ�������˱�д�����ˡ�������ʱ����ԭ�����ϱ༭����I��
��������Look����ʼ�����ˣ�ԭ����֪ʶ������ȫ�ܵ�����ȥ�ˡ���ʱ��������Ϊ�����ģ�ҲΪ������ż���������ʱ����ΰ��һ������߶߶��˵���������Σ�����˵�仰����
�����������С������Ǿͽ����ҵİ칫�ҡ�
������������ȥ��һ�¡�������˵���������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