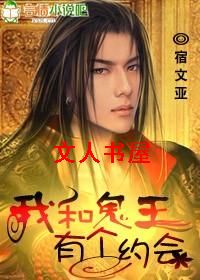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谐!宝钗嗯了一声,点了点头。这时候,黛玉缓过气来了,含羞带笑反击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罢了!真讨厌。那总要占上风的凤姐不依不饶,她指着我,跟黛玉笑道,瞧我家兄弟,要门第有门第,要模样有模样,要家产有家产,要学问有学问,哪点配不上你?说呀!黛玉什么也不说,说不清她是羞还是气,反正是她起身便要走。若不是宝钗及时拦住了她,就弄得大家都有些尴尬了。宝钗是这么劝她的:凤姐只是开个玩笑,你干吗当真呢?若是你这么走了,就显得都没意思了。黛玉犹豫了片刻,只好坐了下来。这时候,我父亲的二房,那个肇事者贾环的母亲赵姨娘来看我了,凤姐那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就适时地收了场……
刚才,闻听凤姐要进来,黛玉就赶紧走开了,看来她是把凤姐的那个玩笑当真了,是这样么?我不敢确定。不是这样么,她当时只是生了气?我更不愿这么想。至于她是不是想嫁给我,或者说我愿不愿意,能不能够娶她,实话说,当时我并没有多想,至少没往深处去想,我以为这都是以后的事情,我所在意的,是我俩的感情好不好,相爱深不深,而不是嫁不嫁,娶不娶的问题。
于是,当晚我就让晴雯去看望黛玉了,并且要她带上我的两条手帕。我之所以让晴雯去潇湘馆,而不是叫袭人过去,那是因为我觉得袭人跟宝钗姐姐走得更近,而晴雯和黛玉心更近。然而,即使是晴雯,对我的行为也很有些不解,她问我带这两条不新不旧的手帕干什么呀?我笑了笑回答说,你不用多问,她会知道的。
黛玉会知道么,她能知道些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的。如果说凤姐那天给黛玉开了半真半假的玩笑,弄得她无以应答的话,眼下我就算是给她做了个谜语,我倒想看看她将会如何破解它。这个谜语,是无谜底的,她会如何解答它,我心里也没底儿。
过了许久,晴雯才回到我们的怡红院,她把黛玉的答案带回来了。她给我带回来的是黛玉的心,黛玉的情——在我送去的那两条手帕上写下的三首诗。我的手帕啊,去时你们是洁白的,回来时你们就染上了如金的墨迹点点。不,应该说你们又完璧归赵了,而且上面镶嵌上了一粒粒珍珠。我手捧着它们,端详着,念诵着,咀嚼着,现在我禁不住将那它们抄录下来: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尺幅鲛绡劳惠赠,教人焉得不伤悲……
当时,我念诵着黛玉为我而写的诗,眼流夺眶而出,一滴滴泪水淋湿了手帕。现在,我抄录着黛玉当年写给我的诗,早已是泣不成声了,我的心颤栗着,握笔的手也在抖动,我抄一行诗,流几行泪,一滴滴泪水淋湿了纸张。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泪流满面的我,都在想着黛玉为我写诗时的眼泪。我知道,她的眼泪为我而流的,也为她自己而流,更为我们而流。她知道么?我的眼泪当然是为她而流的,也为我自己而流,更为我们而流。哦,她的泪,我的泪,那时的泪,此时的泪,全都一片模糊了,也全都融合在一起了,那就让它们点点与斑斑去吧。
我记得很清楚,多年之前那天夜晚,晴雯带回她那咏泪诉衷情的题帕诗后,我曾详细询问了黛玉写诗时的情景。晴雯是这样给我描述的:她把我的手帕递给黛玉,黛玉凝眉思量了片刻,便叫紫鹃掌灯,缓步走向案台,研墨,蘸笔,顿了一下脚,一副全然不顾的样子,流着泪,开始书写,她停停写写,边写边流泪,边流泪边写,转眼间白手帕上就满是墨迹了。她似乎还要再写下去,但见她两颊片片桃红,她走到镜台前,掀幕照了照,听到她气喘吁吁,身姿摇晃了一下,差点儿栽倒在地,紫鹃急步上前扶住了她,去床上歇息了。听着晴雯如此这般的描述,我当即就心疼得流了泪,怪自己不该多事,送去什么手帕劳动了她。那时候,我只以为她是为诗所累,怎知道我那原本就有病的黛玉妹妹,由此而病得更深了呢。
黛玉在手帕上为我写下的那三首诗,当时我是把它们当成书信——情书来读的,之后我也就将它们当成信物珍藏起来了,我把它们珍藏多年了。在大观园里里生活时,以及此后的一些日子,我都把它们藏在我的书柜里,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把它们带在了身上,一直揣在我的怀里。眼下,我把它们再次掏出来,放在案前,带着哭腔念诵起来。
我这墨迹点点的白手帕啊,经过岁月的浸染,你的色彩更丰富了,早就泛黄了。现在,你们至少有三种颜色了,黑的,白的,黄的,黑的是字迹,白的是本色,黄的是岁月。眼下,我再次端详着面对着你俩,除了阵阵悲伤,不尽的悲伤,忽生出一股刺骨的愧疚来,是啊,我愧对黛玉!她曾为我写下过如此哀怨缠绵的诗篇,另外她还有不少诗是为我而作,或因我写的,而贾宝玉,你这个自以为也是个诗人的家伙,竟几无一首爱情的诗篇献给她。你还配说自己也是个诗人么?呸!我对着自己。
许多年之后,我还在回想,回想着那个青春骚动的季节,那个春暖花开的人间四月天,那个困乏慵懒而情思悠悠的午后,那个差点就发生了灵与肉交媾的美妙而危险的时刻。直到现在,我都说不清那究竟是一桩终生的遗憾,还是一个莫大的庆幸。
那时节,我又信步晃游到了潇湘馆,院子里静无声息,连那只巧嘴鹦鹉也一声不吭,它在打盹,我生怕惊动了黛玉和鹦鹉,便蹑手蹑脚走到了窗前,一缕好闻的幽香飘入我鼻息,弄得我头有些晕,骨头也有些软了,我把脸贴在有暗香流过的纱窗上,想偷窥一下黛玉在做什么,还未及看到她的人影,却听见了她一声悠悠长叹,接着就是一段吟唱:这些时坐又不安,睡又不稳,我欲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嗬!黛玉在唱《西厢》呢。没错儿,这是剧里崔莺莺夜听琴那一折。那崔莺莺想念着张生,愁绪满怀啊!莫非,此时黛玉也像她(崔莺莺)想念他(张生)那样,想念着我?顿时,我心里甜滋滋的,痒酥酥的,再透过薄纱看见床上的黛玉伸着小懒腰,一副愁闷无尽的样子,我想是时候了,正好是时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可以也应该进去看她了。
妹妹呀,你为何,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我一边笑着跟帘内人说话,一边掀开帘子走了进来。
我那忘情了的妹妹一下子就羞红了脸,她用衣袖遮掩住颜面,转过身去,背向我,佯装睡觉。我明知她这是在跟我玩小把戏呢,就想上前去再把她的身子搬转过来。不料,后面却有人拽住了我的衣襟,回头一看,是紫鹃,原来她悄悄跟着我进来了,紫鹃跟我小声说道,姑娘正在睡觉呢,你过会儿再来吧。
这时候,黛玉却一个骨碌坐起身来,她揉了一下眼睛笑道,谁睡觉了?她这么做,显然是不想让我离开的。有戏!我暗自欢喜,并且揣摸着。见此情状,紫鹃笑了笑,分别看了我和黛玉一眼,很懂事地走开了。
坐在床上的黛玉一边轻拢着有些凌乱的云鬓,一边微笑着嗔怪道,人家正要睡觉呢,你进来干什么呀?
来看看妹妹呀!我笑眯眯地应答道,来陪妹妹说会儿话,来解解妹妹这坐又不安,睡又不稳的午倦,不好么?
妹妹的脸又红了一下,没再言语。看她两腮晕红如桃,颈项乳白如荷,秀发散落如瀑,胸脯颤动如兔,双目迷离如水,我已是神魂荡漾,心旌摇曳得不成样子了,直想猛扑过去,紧紧抱住她,狠狠亲她几口,真的很想,但又怕惊吓了她,就只好忍了忍,忍了又忍,换上一副笑脸,很有些挑逗意味地问道,妹妹刚才哼唱什么呢?
哪有啊?黛玉若无其事一般回应道,我没哼唱什么呀。
呵呵。我搓起拇指和中指,在她眼前打了个响亮的响指,哼!还说没哼唱呢,我可全都听见了。
你听见了什么?她看了我一眼,反问道。我想,她可能是故意这么反问我的。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我拖着长腔,重重地重复着,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她呀了一声,捂住了脸,轻轻骂道,哥哥不要脸,偷听人家……
嘿嘿,我是无意听到的呀。我先是做出一副很无辜的表情,紧接着就装作无知的样子追问道,妹妹每日家情思为何人?
你说呢?她这样问我时是低着头的,随后她抬起了头来:
你说什么呢?我那是念唱《西厢》的……
好啊妹妹!我拉住她的手说,那咱俩现在就一起唱段《西厢》,好不好?
正想着看黛玉会如何回答呢,却听见了紫鹃在帘外说话,她问里面的两个有什么要伺候的,我应声答道,那就给我来碗好茶吧。黛玉却笑着接道,紫鹃,你不用理他这个坏人,先给我舀洗脸水去。紫鹃在外面笑着回应,姑娘呀,先客人,后主人嘛,我还是先倒了茶,再去舀水吧。黛玉笑骂道,鬼丫头,偏心眼儿。我诚心夸赞道,好丫头,好心眼儿啊。
很忽然的,我就心头一热,很自然的,我想到这紫鹃有点像《西厢记》里的那个红娘。于是,我灵机一动,像张生对着红娘那样唱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我把同鸳帐这三个字咬得很清,很重。我得承认,当时我是借他人之戏语片断,唱出了我心中之真情实意。
哪想到,黛玉脸上顿时变了颜色,她双目圆睁着问道,宝玉,刚才你哼唱些什么?
哪有啊?一看黛玉动了气,我赶紧像她刚才那样抵赖道,我没哼唱什么呀。
哼!还耍赖?你分明又在我面前滥用这艳曲淫词,拿戏里的事儿欺负我!黛玉一边说,一边哭,一边要跳下床去。
这时候,我装作怕她要去老祖宗那里告状什么的,就软了下来,忙拦住她央求道,好妹妹,别去,别去告我,都怪我不好,怪我一时头脑发热胡思乱想,怪我这张破嘴信口开河胡说乱唱,真该打,真该死!说着,我象征性地扇了自己两个大嘴巴,接着便又是发誓赌咒,哥哥以后再也不敢胡说乱唱了,若是再这样冒犯妹妹,就先烂我的嘴,后烂我的舌头,或者让我变成只会哇哇叫而讲不出话来的哑巴,好妹妹,你就再饶坏哥哥这一回吧。说到这里,我向她抱拳作了个揖,差点儿就要给她跪下了——如果不是这时候紫鹃给我端茶过来了的话,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那紫鹃一看当时的情景,她放下茶便默默离去,也不再进来给黛玉送洗脸水了。紫鹃一走,我又开始继续批判自己,并且朝更深远处发誓赌咒。其实我这么做,就是在跟她做戏,做游戏,就是想让她开心一笑。
而黛玉,真的也就被我这套言语和行为逗笑了,她擦着泪笑道,瞧你吓得这样子!谁说要去告你了?我说你呀你,到底还是苗而不秀,一杆银样镴枪头啊。
啊!我心猛颤了一下。她又像红娘嘲讽胆小的张生那样,说我是银样镴枪头了。这可如何是好,该怎么应对她呢?我想了想,便一脸笑意试探了她一下:妹妹,瞧你,不让哥哥说戏里的话,眼下你却又在说了。你要再这样说,我也那样说了呀。
你敢?!黛玉瞪了我一眼说。
不敢,不敢呀。我对着她做了个小鬼脸说,你以为我不敢么?
许我这样,不许你那样!黛玉这样说,已很有些撒娇的样子了。
是,是,我顺着她笑道,你可以,我不可以,我是哥哥,你是妹妹,我让着你。
这还差不多,黛玉笑着说,她笑得很灿烂。
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上床,陪妹妹说会儿话?我趁势要求道。
嗯。黛玉点头笑道,看你认错态度还好,那就上来吧。
好!我猴儿一样上了黛玉的床,一手握了她的手,一手轻轻揽住她的腰,她的腰那么细,那么柔软,那么有弹性,感觉真好,不仅仅是手感,我浑身上下都有感觉了。虽如此,可我不敢朝更深处想,手也就停留在那地方,没有更多的动作,尽管我的心已是怦怦乱跳,念头如火苗乱蹿,很想跟她有更深的亲热之举。可实话说,我有些怕,怕她不悦,怕她不想,怕她不愿意,于是,我就言不由衷了,顾他而言左右问道,妹妹这几天在念谁的诗?
黛玉似乎怔了下说,随便乱读罢了。哥哥呢,在看什么书?
我嘛,这两天又在重温《庄子》呢。我感叹道,庄子好文章,真是百读不厌啊。这是我第五遍,要不就是第六遍读他了。
哦。黛玉淡然一笑说,那哥哥就给我聊聊庄子?
好的。我给妹妹背段《庄子·庚桑楚》吧。说着,我便得意洋洋的,摇头晃脑地背诵开了(现在想来,我当时那个样子真是傻透了,憨死了,可笑极了):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无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