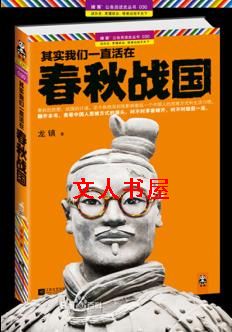炎黄春秋-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点东西发表。过去的近20年间,除了小范围说过几句外,我一直避免谈论《顾准文集》出版的相关情况。其主要原因,一则是因为《顾准文集》出版后引起的所谓“热”,社会认知了顾准的卓越思想,这个时候去说什么有点借光之嫌,而我这样想,顾准是伟大的思想家,出版《顾准文集》只是我责任编辑的职分而已,因此不该说,不该因此“沾什么光”;二则是因所谓“敏感”,当年因《顾准文集》而遭遇了一些事,其中一件是:强力机关的人明确要我不对外讲《顾准文集》的相关情况,否则——因此我一直没有说。今天,中国社会、人群深刻和宽容了,再也不会不让说了吧。
关于顾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几近不了解。1982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小册子,很好读。回忆起来,我大约是1990年读一些有关西方文化的书时读的该书。读后的感觉是立意深刻,文字流畅,不同于其他呆板的学术著作。但此书并没有介绍作者顾准的更多情况。因此,“我不认识顾准”(李慎之先生语)。1993年底,大约11月初吧,突然收到王元化先生写的一封信,字不多,推荐《顾准文集》来出版,信中未对推荐作品有评价文字。元化先生是通过其弟子胡晓明君转来信,胡晓明君的弟弟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工作,其弟将信转到我手上。没有看到顾准先生的文字,且出版人都知道,文集的出版是有规格的,不是像现今随便什么写手汇拢其文章就可出版所谓文集。顺便一提,《顾准文集》出版前,少见文集的出版,后来,出了很多的文集,这也是一件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因此,心里没底,不敢应承。但王元化先生是学问大家,其学问人品我是高山仰止的。顾及此,回信请求元化先生安排人将书稿寄我一读。我给元化先生的回信大意是,说明了对文集出版的规格要求,需要有真正的相当水准的学术创见,我对先生的推荐是十分重视的,相信是一本好书等。也许是因于我的严格及真诚吧,很快,收到了陈敏之先生寄来的书稿复印件及简短回信。信中说明了书稿几经周折未能出版的大概情况,且说1994年是家兄的20周年祭,如能接受,希望能应时出版。
应该说,我真是在百忙中看了顾准书稿。是时,我手上共有16部书稿正在处理,在顾准书稿前已列入重点出版的“中国市场经济法律问题丛书”,16部书稿要每本都审读后写出审读意见,最后选用9部书稿编辑出版(巧的是,这套丛书后来获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客观上减弱了因《顾准文集》带来的压力)。说实话,对顾准书稿,看以前并没有特别重视的感觉;看完后心里就惊讶了,写得好,特别是后半部分,精彩无比。审读完书稿,记得大约花了一周时间,再反复边翻阅边思考、掂量——真掂量!掂量书稿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与也许要承受的“风险”,最终决定出版。电话告知陈敏之先生,陈敏之先生反复询问肯定吗?我回答肯定,签出版合同吧。他说太感谢你了。签合同往返还有一些时间,陈敏之先生还是担心出现变故,几次来电谈顾准书稿出版的周折,如实地说了几家出版社的处理情况,也把退稿信复印后寄给我,要我拿定主意,如有困难,授权我删改几处文字。这些情况自然也引起我的注意,这些出版社的处理意见写得很好,对顾准书稿评价很高,但退稿理由含糊其辞。最终,综合各方面情况,我给陈敏之先生的回答是,肯定出版且不删改一个字。电话那头的陈先生问真的吗?真的吗?我说,在我看来,顾准先生通过对西方历史、中国历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体察和研究,表达的观点是有理据的,不是象牙塔里学术八股书本上的推演,更不是悬浮在空中的判断,思想深邃、见解卓越,实在不应该删去任何文字,应保留它原来的面貌,哪怕有不当之处,让历史去评判吧。陈先生说,我很同意并佩服你的看法。谢谢你这样理解,我相信家兄的书一定能出版了。你需要我怎么配合尽管说。合同马上签,不要稿费。鉴于学术著作不好卖的情况,为减轻你们的负担,我提供15000元钱作为出版补助(批选题时,此笔费用是起了作用的;后来钱全数退还陈敏之先生了)。就这么定了。
审读《顾准文集》书稿花费两个月的时间,与陈敏之先生商谈出版事宜大约花费一个月时间,作出出版决定的过程没有曲折反复,一切都理性而有序,以至于陈敏之先生后来说,几乎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谈妥了出版事宜,关山万重阻隔不了相互的理解和支持,阻隔不了对顾准的认知。
《顾准文集》出版了,一部好书,历史将证明它是一部好书,就这样出版了。
出版《顾准文集》,我将因此面临压力,当时的心理准备是,出版完了离开贵州去深圳(地方都找好了),离开这个行业。作为责任编辑,无名无利,求什么呢?只有两个字:责任。
为什么要出版《顾准文集》?审读和编辑加工顾准书稿后,我所列的理由是,“顾准研究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研究经济学、哲学,究天人之际,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道,其理据充实、思想深邃、见解卓越,是我迄今未曾见过的”。这是理由之一。“顾准在那样严酷的年代,行进在那样艰苦卓绝的探索真理之路上,其目的是中国‘雄飞于世界’,此种境界是百年来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高标”。这是理由之二。“顾准的研究理路是,先弄清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然后进行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贯通东西方文化,他谙熟英文,既懂数学,也精通经济学、哲学,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这是一个学问大家的品格。我十分欣赏顾准理性且冷峻的‘不唯书,不唯上’,通过自己艰苦研究,独立作出判断的治学方法”。这是理由之三。《顾准文集》中很多思想观点“于今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如对价值规律的认知,对专制的否定,对民主的辨识,对中西方文化特质的描述,对经济制度与法权制度相互关系的理解等等,都具有耀眼的思想光芒,启示现实,可能也启示未来”。这是理由之四。还有,透过书稿看出的顾准高贵的心灵及为探求真理不畏强暴的勇气……理由还不够吗?引号中的话是我当时编辑手记中留下来的,以我的智力和学识,只能理解到这种程度了。但我想,这些理由足够让我决定出版《顾准文集》,足够让我认为不是贸然作出出版决定,值得为此承担一份责任了。顺便补充说说,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许多书稿特别是本土原创作品,读后乏善可陈,我认为是不值得为其写编辑手记的。
《顾准文集》出版后,曾有媒体记者就审查问题询问过我。这里我可以说,图书的审读是按正常程序走的。我此前责编了诸如《比较法总论》、《原始人的法》等世界名著,参与策划了“国际经济惯例丛书”,主持策划“中国市场经济法律问题丛书”等工作,得到领导的信任,且张劲夫同志的推荐信也是说明顾准书稿价值的重要材料。复审和终审都是走程序的,北京有关方面的人也是理解《顾准文集》的,私底下许多人还对我说《顾准文集》是一本好书。后来在“问责”出版《顾准文集》时,没有将我往死里整就说明了这一点。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印制出来了,销售成了大问题。我社发行部不愿卖,新华书店不愿卖,理由是学术著作卖不动。10月初在武汉图书订货会上,第一批40本书从襄樊运到会上,没卖出一本。我将书推荐给一些社科书店,并送书给书店,请他们读后认为好就打电话给我,要几本都行,只要愿卖。但仍然没有书店要书。200册书运到在北京的顾准女婿张南处,分送顾准生前友好、同事,100册书运上海陈敏之先生处,也分送顾准生前友好、同事。最初,《顾准文集》就这样无人问津,一本都没卖出去,难道就没有人能识货?心里很着急的。但不久,突然出现了转机,也许是张南先生送出去的书让顾准生前友好、朋友读后引起了议论。一天,接到素未谋面的北京三联书店郝杰女士打来的电话,说要300册《顾准文集》,马上发货。并说别的学术著作我们一次订货总是三五册,《顾准文集》一次就要300册,很特殊了。我听这话有弦外之音,但不明就里,到现在也不太知道具体情况,大致猜想当时是三联书店负责人安排的吧。郝杰的电话让我十分感动,是她那里第一个愿意销售《顾准文集》,并且一次就要了300册。书到三联书店(当时是在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一小破门面)十几天后,郝杰又来电话添货,说你这是什么书,头天买走的人第二天又来买,有很多人还一次买几本,传开了,不够卖,赶紧再发货来吧。听了郝杰的电话,我心里有底了。中国是有人认识顾准的!不久,北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打来电话,要求在北京地区独家销售《顾准文集》,第一次要4000册。销售由此打开局面。至今我仍然从心里感谢郝杰和刘苏里。
1994年10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纪念顾准座谈会,张劲夫、杜润生、雍文涛、徐雪寒、王元化、李慎之、吴敬琏、李人俊、林里夫、骆耕漠、赵人伟、张卓元、何建章、董秀玉,青年学者俞可平、刘军宁,顾准家属等40多人与会。经济学所党委书记于祖尧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高度评价了顾准在经济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王元化先生专程从上海赶来参会,在会上讲到顾准思想点到之处都使我们放不下,具有很大的启发性,顾准的思想紧扣时代,又超越时代;杜润生先生深情地说,顾准学问很大,他既懂数学,又懂经济学、哲学、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我很遗憾在他生前没有多向他请教学问。吴敬琏先生作了长篇发言,大致内容是后来发表的文章《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说,早就听说过顾准,但不认识,印象中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文革后我重新工作,分管社科院学报工作,创刊号有一篇顾准的文章《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我认为写得很好,建议刊发,但正式出版时文章去掉了,很遗憾。慎之先生话头一转,没有再直接谈顾准,而是讲到当下改革开放的国际、国内情况。总的感觉是慎之先生眼光高远、话锋雄健。散会后,我单独找到慎之先生,请慎之先生就顾准说几句话,慎之先生说:“我不认识顾准,没有什么可说的。”然后扬长而去。
顾准纪念会后,吴敬琏先生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上。俞可平先生也写了文章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于是,顾准思想及其精神流布开来,顾准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顾准文集》的销售越来越好。
再说到李慎之先生。会后大约一个多月,慎之先生托人打电话让我去他家谈话。进门未寒暄,甫一坐定,慎之先生就说:“我要炒顾准。你很快会看到我(写顾准)的文章。”我心里一震。一个月以前,李先生不说顾准,一个月以后却主动要说顾准,其间经历了怎样一个大的转变,不得而知。我肯定的是,以李慎之先生的博学和高远的见识,不会轻易臧否人事。停顿一下,我问李先生:“您所说的‘炒’是哪方面的意思?”李先生说:“你怎么理解都可以。”然后,他顺着顾准思想谈起了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国存、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命题。谈到民主与专制问题,谈到人口众多的中国公民素质教育,甚至谈到他是十分佩服邓小平的,邓小平1979年访美是十分重要的事件,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李先生从上午九点一直谈到下午一点。
不久,《读书》发表了李慎之先生《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这篇文章连同此前吴敬琏先生《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一起,使中国思想文化界为之一震,促发了一大批学者结合当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考。
至此,王元化先生、吴敬琏先生、李慎之先生这三位大学问家,都公开发表了文章,对顾准及其思想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中山大学石冷(笔名)先生也写了很好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上。早些时候,杰出学者朱学勤写下许多关于顾准思想的文字,业已传播开来。
1995年11月,在钱竞先生、张南先生的张罗下,一批学界青年才俊自发召开了一次《顾准文集》座谈会。李慎之先生、王蒙先生、邵燕祥先生、何西来先生等年长学者专家与会。朱学勤先生专程从上海来京与会并作了精彩的长篇发言。此次座谈会上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经过前一段时间学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