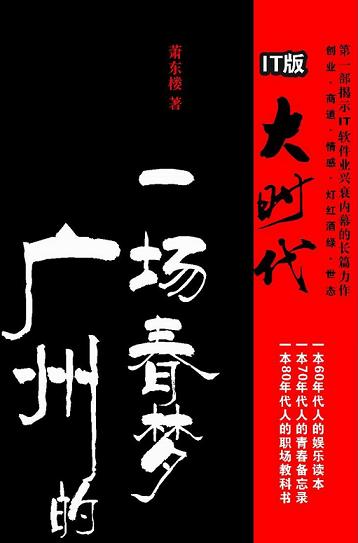逃离北上广-第5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标准的上海人的精明。如果不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我绝对学不会这样的思维方法。上海的肌理已经深入了我的思维。”陈乐笑得很无奈。
正因为上海人有如此鲜明和强烈的物质和消费表演的欲望,而且自成规矩。所以,如果想在上海滩上混出点名堂,就必须让上海的肌理渗透进你的思维,让上海改变你。
上海是滩,滩没有空间阻隔,它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易中天所言,“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
所以,不同于北京人的“圈子意识”,上海人身上体现的是鲜明的“滩涂意识”。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总弄文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作为一个外来者,融入上海,就意味着放弃从前的生活,甚至是过去的自己,你要学会和上海人一样思考和生存,有时这种放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潜意识作用,就像陈乐一样——变得世故和会算计,只是在这座城市里待久了,势必要付出的“代价”。而这是好是坏,全无定论。就像有人拼命挤进上海,有人却背着行囊悄悄离开,你们只是各自计算了一下得失,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那些离开的人是觉得这种“消融”的代价太昂贵,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生生在你身上灼烧出一块属于它的印痕——这个实在太贵了,他们舍不得那块单纯、完好的皮肤。你呢?
3。膜拜“红房子”
红房子西餐馆开业于1935年,是上海滩第一家法式西菜馆。上世纪40年代,红房子西菜馆重新开设在现在的陕西南路上,店名为喜乐意(Chzlouise)饭店,因门面漆成红色,被当时常去聚会就餐的工商界人士称作“红房子”。
在上海,不少人学会吃西餐是从红房子开始的。听说当年张爱玲就是红房子的“粉丝”,有一份张爱玲最爱点的菜单: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这几种红房子的看家菜,沪上很多名人都十分偏爱,赵丹、黄宗英、白杨、王丹凤、俞振飞等,都爱点这几款。
所以,红房子也成了上海老克勒(“克勒”是外来语,是“Color”,彩色的意思,音译过来解释的,也有指“Class”作等级、阶级解释的,“老克勒”是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旧上海的老克勒,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一群人,也最先吸收结合西方文化,那时的他们土洋结合,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海派文化)怀旧的场所之一。
但上海人对西餐、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也是基于其城市性格特征中的实用主义。如果北京人看到的是西洋货,那么上海人看到的是先进文明;如果北京人在意的是“主义”,那么上海人看重的是“利益”。这就是上海人“崇洋媚外”的实质,注重的是这种行为正在和即将带来的实际利益。
不重主义,重利益
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广州,都是《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但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将殖民建筑林立的外滩作为城市的象征和对外宣传的名片。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发文称,上海政府耗资2。8亿英镑,“将分割黄浦江与外滩新古典主义建筑的高速公路改建为地下通道,同时拆除有碍景观的立交桥”。这座立交桥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桥”。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名为“威尔斯桥”,是座木桥。它是由供职于怡和祥行的英国人威尔斯和宝顺祥行的韦韧、霍梅等20人(多为祥行经理或鸦片巨贩)凑资组起的“苏州河桥梁公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投资建造的。2008年,外白渡桥被翻新迁移,重新连接浦江两岸。对此,英国人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上海政府“已经意识到与水连接的重要性,这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城市而言都至关重要”。
显然,英国人纯粹是从一座桥的功用来看待上海翻新保留旧建筑的举动。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引人目光的建筑物轮廓线有着如此的英式味道,如果看照片,我们或许会将它与利物浦默西河滨混淆”。
经常有国人指责上海人“崇洋媚外”,可能看到就是这些殖民建筑群的表面。但实际上,上海人崇拜、推崇的,并非西洋货,而是先进的文明。上海人处理原则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注定了他们更在乎某件事物带来的实际利益,而非这件事物的属性或最初进入时的方式。所以,“主义”对上海人没有意义,“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
比如,余秋雨眼中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明代进士徐光启,就体现了上海人的“功利心”。《文化苦旅》一书中对此人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往,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一位日本人这样形容和介绍上海人:他们口气夸张,有极度的优越感,喜欢讲排场,好面子,惯以领先时代、崇尚时髦而自傲。他们同时还具备实践能力,并且能够巧妙地利用他人的财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上海人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
不拘泥于过去,这是对上海人最精准的描述。只要这个过去,妨碍了他们获取现实的利益,上海人就会明智地将其迅速抛弃,所以他们毫不介意、甚至相当自豪地将外滩作为城市的标志。只因为1930年代,当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几亿农民都蹲在炕上啃窝窝头的时候,上海人正在享受可口可乐。
上海话只是工具
出于功利的目的,抛弃过去,上海人对待自己被殖民的历史是如此,对待作为自身标志之一的“上海话”时,也是如此。基于沟通的便利性,上海人自觉自愿地抛弃了上海话。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上海著名语言学家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新民晚报》专栏作家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他认为,“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另一个声音也在网络上喧嚣尘上,“在上海这个不会说上海话完全混得下去,不会说英语却万万不行的城市,不说上海话又能怎么样?”
上海市大同中学的几位中学生,于2005年暑假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的调查结论是:“上海话‘处境’不妙”。学生们发现最应该使用上海话的地方,比如城隍庙的商铺,上海老街,通用语言都是普通话。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刘民纲教授说:“上海话从古越语变成汉语的方言,语法和词汇跟普通话比较接近,而且越来越接近。有些上海话特有的词汇正在逐渐消失,被北方方言的词汇所替代。上海语音也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音正在逐渐消失,很多字的读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
同样的道理,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从1990年,上海的定位被设计为“国际大都市”开始,“国际化”逐渐蚕食了“地方性”。朱大可感觉最突出的是上海话缺少了造词能力。众所周知,上海话中有大量词汇来自英语的音译,比如“沙发”的来源是英文单词“sofa”,上海话使用之后,才被引入了普通话,时至今日,用上海话读“沙发”,发音和英文单词非常接近,用普通话发音则相去甚远。
类似的词汇还有“嗲”。“这个字是根据英文单词dear的读音生造的,造得非常成功,后来也进入了普通话。但近二十年来,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只出现了一个语式‘不要太……’和‘捣浆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词。”
其实,无论是上海话的语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古音逐渐消失,还是上海话中引入了许多英语的音译词汇,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上海人只把上海话当做一种交流的工具,而非不可替代的母语。
上海语言文字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语言的一个特点是嫌贫爱富,广东的经济上去了,上海人中也兴起过一股学习广东话的风潮。”而这一特点被上海人贯彻得炉火纯青。
与之相对的是广州民众对粤语的强烈捍卫。201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协建议广州电视台增加普通话节目,以方便广州亚运会期间国内外宾客的收视习惯。但这一建议在网络上却被解读为取消粤语节目,“推普废粤”。于是,自尊感极强的部分广州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