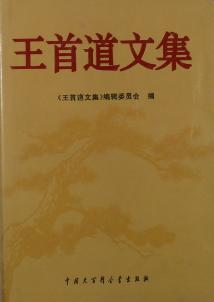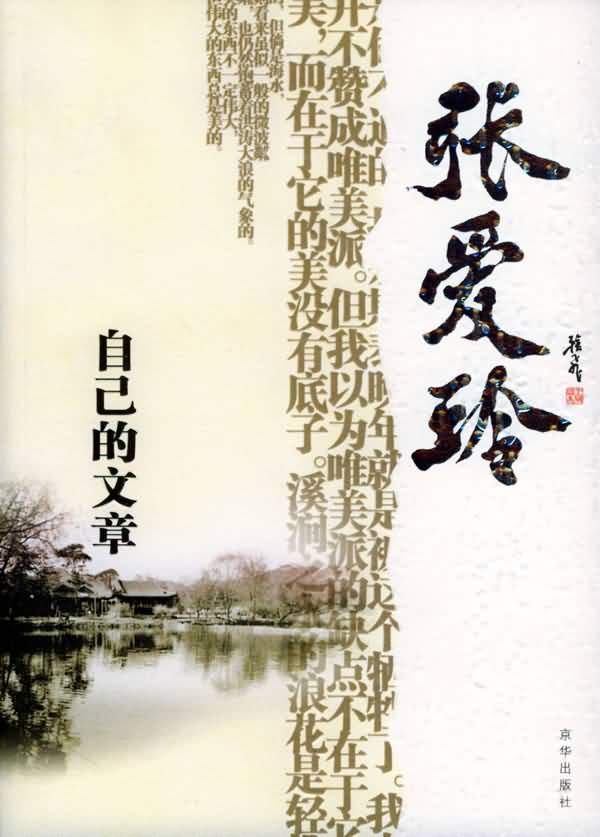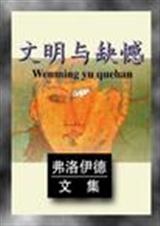胡绳文集(1979-194)-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损失,而且终于导致了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本书作者在上卷前言中已指明,这十年是“我们党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
(上卷,2页)。
这个断语是需要论证的。
为什么必须经过一个探索时期呢?
究竟是探索,还是盲目地乱闯呢?在探索中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成果呢?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严重的失误呢?而且为什么积极成果为失误所掩盖了呢?
这种探索究竟有什么历史意义呢?
它和1978年以后的新时期有什么关联呢?
今天回顾这十年的探索,特别是探索中的许多失误,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呢?
这些都是需要答复的问题,而且并不是很容易答复的。
我们读一波同志的这部书会感到,他毫无顾虑地面对一切事实,从事实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在下卷中以46万字写了22个题目,从容不迫,条理分明,摆事实,说道理,读之使人忘倦,发人深省。书中的叙述和分析,既是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又是提纲挈领的而不是繁琐的。
书中评论许多重大决策和事件的是非、得失、成败,是有分析的,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出发,并不是简单地根据现在人们在实践和认识上已经达到的水平,对过去说三道四;同时又是按客观历史本身的逻辑,说出现在人应该如何接受那一时期的许多经验教训。本书作者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论述表明了,在1978年以后的新时期中党的路线方针的制定,是和1957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中的经验
211
胡绳文集191
教训有密切关系的。我感到,读这本书可以对三四十年前的过去获得比较完整的深刻的了解,而且通过对过去的了解,进一步提高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包括我们党所执行的并将继续贯彻执行的路线方针的认识。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部饶有兴趣的值得一读的好书,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
在这里,我只就以下几个方面说一点初读后的感想。
第一,这部书是如何叙述和评论这十年间的重大决策中的失误,恐怕是读者们所特别注意的。
应该说,本书对这些失误是毫不掩饰的。这些失误无论涉及谁,涉及毛主席、少奇同志或其他领导同志,其中有些也涉及作者本人,本书都一一据实加以叙述和评论。这些叙述是客观的,这些评论是有根有据的、讲道理的。
这里试举一个例子来看看。1957年冬到1958年初这半年间,毛主席曾连续不断地批评反冒进。他的批评是针对陈云、恩来、先念和其他管经济工作的一些同志的。从后来的事实发展看,毛主席当时的批评和责备显然是错误的。本书中明确地指出,“批评反冒进是不适当的,批过了头,为以后的大冒进开了路”
(下卷,651页)。书中还说,“对反冒进的批评具有标志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转向不正常状态的严重性质”
(654页)。
这些相当尖锐的论断,不是简单地轻率地得出来的。
本书在上卷中,已经对1956年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和怎样提出反冒进的问题,作了说明。在下卷《批评反冒进》这一篇中,首先对毛主席批评反冒进的经过情况如实地加以叙述。然后又在五个问题上,基本上用毛主席自己的话
212
291胡绳文集
说明了他对反冒进的批评的内容。作者在这五个问题上,或多或少地作了些评论,然后才对批评反冒进这一段历史作出总的评估。
读者会感到,这样的评估确实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是能够给人以有益的教训的。
书中还从对这段历史的评估,进而论述到,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党内的批评必须正确地进行,必须有充分的依据作基础,必须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能进行过火斗争,以势压人。批评的重点是正确地分清是非,目的是取得经验教训,有利于促进和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党的工作”
(654页)。
我以为,本书对于过去历史上的决策中的错误的评论,可以说就是党内批评的这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的实践。
对于“大跃进”
、人民公社、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等等事关全局的失误的议论,占了本书的很大篇幅。读者可以看到,本书中明确地说明了毛主席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和这些失误的关系,但也从事实出发,说明不能把一切责任归于个人。例如,书中说,“人民公社的建立,虽然毛主席负有主要责任,但决不是他一人的责任。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北戴河会议的人,都举了手,都有一份责任”
(747页)。
又如,在论述1962年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其失误时,根据许多事实说明,“当时存在的‘左’倾思潮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人的责任,而是全党性的思想认识问题”
(103页)。读者还可以看到,本书在对于这些重大失误的认真研究中,不但说清楚了这些失误为什么必须被认定为失误,而且努力探索造成这些失误的原
213
胡绳文集391
因。书中往往把造成失误的个人的因素和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所得出的许多结论是很可贵的。
这十年中,党内只反右,不许反“左”。所反的右几乎又都不是真正的右,“左”却泛滥了起来。对这些情形,书中讲得很透彻。作者说,“建国以来,我们在工作中虽犯过右的错误,但更多的是犯了‘左’的错误。
‘左’是一个顽疾“
(1043页)。
这十年的经验证明,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一般地看成是阶级斗争,把某些不同的意见说成是资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这是非常有害的。针对这种情形,书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党内矛盾主要是认识问题。当然,不能排除社会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党内也会有某些反映。但如果把党内存在的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意见随意说成修正主义、阶级斗争,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导致在政治上犯错误”
(100页)。很明显,作者是严格地按照自己所提出来的这种观点进行论述的。他把“左”的错误观点和“左”的思潮,总是当作认识上的错误来加以分析评论。固然他也说明这些错误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是不给这些错误的认识戴阶级的帽子,把它们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我认为,这样做是好的。既然经验已经使我们看到,把阶级斗争任意地引入党内是非常有害的,那么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也不应该重犯这种错误。对党内的错误倾向,深刻地剖析其认识根源,至少要比简单地扣帽子更能够给后人以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214
491胡绳文集
第二,本书对许多事情分析得很细致,说出了许多读者所没有注意到的情节,从而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看法。
对此,我想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看来还是正确的方针政策。但不到一年后,在反右斗争中发生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进一步发展了八届三中全会的主张。同年,发生了“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都显然离开了八大制定的轨道,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八大后两年的这种变化,究竟是怎么来的?如果认为八大一开过,所有的文件都被撇到脑后,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
本书指出,1956年的八大的一个重要功绩,是适时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从解放生产力转变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来的决定。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实际上在八大以后,党中央是尝试作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的。
本书中说,“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试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愿望”
(658页)。又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无疑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是相适应的”(673页)。这样说是符合事实的。当时的所谓“大跃进”也是把全党的注意力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如实地指出这些,当然不是为那时的总路线和“大跃进”辩护。书中对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执行中的
215
胡绳文集591
巨大偏差“
,作了详细的论述,说明了“这次工作重心转移的尝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经济生活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
(658页)。
仔细研读这些论述,会使我们看到,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就能做到的。
1957年的经验,乃至后来1959年、1962年、1964年以后的经验,都表明对形势的估计是多么重要。如果无中生有地、或者不是恰如其分地而是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那就必然把重心转移的良好愿望冲垮。还可看到,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就必须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保证。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时就能提出两个基本点,包括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等政策。但是,书中用生动的丰富的事例说明,不懂得也不愿意承认客观规律(客观的经济规律乃至客观的自然规律)
,沿用革命战争时期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来搞经济建设,这样做只会造成破坏生产力的结果,也就必然使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心动摇。
“大跃进”
的失败既不证明工作重点不应该转移,也不证明国民经济不可以发展得快一些。
由于书中对八大正确的决定(其中也有一些不完备的地方)如何转向反面,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我感到人们是可以从这里得到相当丰富的教训的。
我在这里想讲的本书中另一个分析细致的例子,是关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这次庐山会议,开始是反“左”
,继而转为大反其右,在全党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从表面现象看,那就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而毛主席不能用正常的对待党内批评的态
216
691胡绳文集
度来对待这封信。这当然都是事实。但是,如果彭总不写那封信,或毛主席对待批评的态度好一些,形势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么?这好像很难令人相信。
书中认为,这次庐山会议以前半年多的纠“左”
,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也指出,这时期的纠“左”是极不彻底的。书中说,“当时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下进行的,如果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动摇,就认为‘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在这个前提下纠‘左’,当然是不可能彻底的,因而庐山会议后期出现反复就不足为奇了”
(840页)。
这就是说,庐山会议的反复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不仅是由于彭德怀同志写封信这样一个带有偶然性的事件而发生。所谓不彻底,就是不认识、也不承认在“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指导思想有什么失误,而认为那是完全正确的。
书中说,“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用说‘言词偏激’,就是稍有微词,也就成了‘对立面’,成了‘右倾’了。彭(德怀)
、黄(克诚)
、张(闻天)
、周(小舟)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
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
庐山会议转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