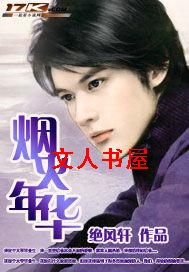������ʮ��-��7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Сƽ����ƽ�������Ὠ��Ĺ�������Ҳ���ͷ���ൺ�����׳������ò��������һ��������֮̾Ϣ����Ҳ�ǿ��ϵġ������ɣ�
Ԭ��������
�������������Ѯ����ʥ�������뾩����֮ʱ�������ڳ��е�̷��ͬ�����¾��ɾͽ����ˡ����������֮������й����鲢ȡ��һ���������ΪΨһ�������Σ�֡�ŤתǬ���İ취������˵��Ԭ�������˱�������Ԭ����Ч�һ��ϣ�����»��п�Ϊ��
Ԭ������ʱ��ͳ�ʵġ��½�½������ǧ���ˣ�����Ϊ���֮�ڣ���ȷ�Ǹ�ʵ���ɡ�����������˼��Ҳ�������Ǹ������������������ʽ������ֻ�ǡ�ֱ������ʹ��������»�����һ�����Ӷ�Ʒ����ʡ���м��������׳ơ���̨����Ԭ֮�д˵�λ���������»�ġ�֪��������Ȼ������»����úܽ�������»����̫����ĸ������Լ�Ҳ��ǰ;���ޡ�������Ҫ��������»������̫���תͶʵ�����Ŀ�ͷ�۵������Ԭ�������˻�ǰ;�������������������Ǹ�����ĶIJ����������ⳡ�ۺ��ͻ֮�У���ֻҪ������������۵��ͱ�Ȼɱͷ���Σ�ȫ����û������óȻ����۵����˱�������������ǧ�ӵܣ�Ҳδ�ؾȵ��˻ʵۣ����Լ��Դ������ܰ�ҡ�Ԭ�����Ǹ�����֮�ܳ�������֮���ۡ�����֮�䣬���Ƕ����ۻ�ġ�
�ʹ��Ƿ�֮����˵�ɣ�Ԭ��������߳���֮�ģ�����λ�嶯��С���ӡ�����˧��������ɲ��������ͺ�����������������ġ���̢������Ԭ��ȴ�Ǹ����Ϻ�����Ϻ�����Ϻ��꣬���Ͳ�������Ⱥ���������Ĵ��ˡ�������һ�������ڵ�ʱ�Ծ�����ͷ�ԵĹ۲�ң���������ָ�ƣ��δ���һ��������ʷ���������������أ�
������ʱ�ĵ۵��е����Է��ӣ������ٲ���֮����������Ҳ�ѱ��Ƶ�Ъ˹����ij̶ȣ�ֻ������������ҽ���˲��������ˡ�����ʮ���գ��������¶�ʮ���գ�Ԭ�����˷����뾩��ʮ�������ú���ʥ����������ο���мӡ�Ԭ���������ͣ�������ʹ��ȱ�����ԡ����ɺ�ר������������ʱ����Ӧ�����ˡ�����һ��Ԭ�������һ�����Ӷ�Ʒ�����м��ط��٣�������Ϊһ��������Ʒ����������������ơ����ɡ�����������项ͨ�ơ��ù١���������ƽ�Ȱ��µġ�Ԭ�Ǹ�����ǿ�ɵ��ˣ�������Ϊ����ľګ������֪������ߪ�����и���ԭ���������ڡ�л����ʱ���ʵ����ͣ�Ҫ������»��������¡���
��ʱ��»�ѻ���鱨����һ������������Ա����⣻һ������Ӣ����ս�ļ���Ϣ������ר���Ԭ�����ؽ�Ԭ�����ڽ�������֮ʱ���㷢����̷����������ҹ�ܷõ������¼�����Ԭ�����й¶�ġ������ռǡ����أ�����ʮ���գ��������³�����̷��ͬ�ҹ���ã������ż�ɽ�ĸ���������̫������»�Џs���ͷ�������ı������ϣ��Ԭ�ϱ��ݣ��ʱ������»����Χ�ú���Ԭ����δ�����̫���أ�̷˵���ѹ��кú���ʮ�ˣ���ȥ�����࣬���Ҷ��ѣ������ù������ơ�Ԭ�����ռ���˵�����ԡ�������⡹��������ͬ��ʱ�ѡ����Ʒ����ϵ�����ӽ������������Ҳ����ܡ��ò����ײŰ�̷���ߡ�
�Ͻ��ѽ�������Ԭ�����Ǿ��������̷��֮ͬ��ı�ġ�����֮�����ص�����˰�̷�ļƻ�����»ȫ��й©����ʵ̷����һ���ܼƻ�����̫������»����֪����Ҳ���Ѳ�ȡ�ж��ˡ�����������ʮ���գ������������գ�����������ʮһ����ʽ�ٳ���ѵ�����������ʦ���ϣ���ͣʻ���漴�Ľ��ʵۡ������µ��������������ָ��ɷ����������ν���������䡹�ˡ�������̫��һ��������µ�����Ҳ�ʹӴ�������ɢ���ʵ�Ҳ�����̨��
���絳�˱�
����������ʱ����һ���س��Ѳ���Ҫ������Ȼ���ǿ���Ϊ�ˡ�˭֪��������ǰһ�գ���ҡ��ڵ��߳���ȥ�����ϵ�һ����������������Һ�ƽʱҲ���������С���ʱ�������ѱ�������ʹ�ݣ���װ��ȥ�������������µ��йأ�δ�����ߣ���Ը���߶������߷���ʮ�ˡ�������Ҫ���Ӿ�����ν�������ӡ�����̷��ͬ��������������ڡ�������Ϳ����ʡ�������δ����Ѷ��������ǰ�����������¶�ʮ���գ��ڱ������пڱ�ɱ��������ɵĴ�ͷͷ���㡸��ն���������㣨һ�����ߡ�һ�ũ��������ǽ��Ǿ������Ļ��ʻ���ʲô�������Ѱ���ū��������Э���ѧʿ������һ������
���������֮�У�����ѳ�������Ҫ��̷��ͬ��һ�����填һ�˾Űˣ��ˡ����������ߡ�������������������ǰ�棻����ʧ������ѳ�ѵ�������ͬ����Ȱ�����ߵ�����˵���䷨�ͱ�Ȼ����Ѫ��Ҫ��Ѫ����Ӧ�ô�����ʼ���������ʹ��ݾ����ˡ���ͬ��һλ��˽�İ����ߡ�һλ����ӣ��л�����ĺ��ж���
�����㣨һ���ľš�һ�˾Űˣ�Ҳ��һλ������������������ĺ�����ʷ������ȻҲ��ά���ɣ������������ѳ���ʵ����̫����ʽ��ѵ�������ʵ۱��ģ��ٳ�ս��֮ʱ�������ɱտ�����������ƫҪͦ��������ڵ�ʹ�������֮�ʣ����������������������±������塣�����Բ�����������ǧ�ٸ���ʷ��������������ר���Ӭ��������ƨ����ν����Ա�У��м����������أ�����ɽ���ǿ���������ʷ�����Թ٣��ż��Ҫ�㡸��Ȩ���ܷ����أ�
������֮��������w����Ҫ������ʮһ��Ŀ����ʣ�һ�����ߡ�һ�˾Űˣ�������û�����٣�Ҳû����ά���˶��е�����Ҫ�ɲ������Ա䷨ʧ��֮�������ı��ѣ�Ҳû�����ѡ���Ϊ��ʵ��û�б�ɱ����״�����������ڳ�ʬ���пڣ�ֻ��Ϊһ���ʸ����ǡ�����Ϊ�ĵܵܡ����������ڱ�ɱ֮ǰ����������ͷײǽ����ʹ���ţ�ʵ��Ҳ�Ǻܹ����ҵġ�
����ʿ�������µ��м�����䡢������������ţ�һʱ�㾡����Щԭ������ͬ������ͬ����Ӧ�Ŀ�������������������ͬ���������裨����֮�����������Ա�������վ��������¡�����һ����Ҷ����������ˣ�����۹��������⽻���ߴ�Ȩ��������������̫��Ϊ�ģ�һȺȺ�����ӹ��������֪����˽����֮�֡�����������ÿ�������������������ȭ���͡��˹�������֮������Ҳ����˳�����µķ�չ�ˡ�
��Ȼ֮����żȻ
������䷨�����ҹ���ǧ����ʷ�У�����������Ԫǰ���ũ���ǰ�����ˣ�����ç����Ԫǰ��������Ԫ������������ʯ��һ����һ��һ��������֮�͵�Сƽ��һ�ũ�����һ�ž��ߣ�֮ǰ���������˵ı䷨�˶�֮һ��
�����������ԱС����⡸���ѡ������岿������ţ���������ѳɼ�����飩��������ҡ���çʳ�Ų�������������壬���Ҳ����ͷ������ʯ�Ծ�ƿװ�¾ƣ��������õĹ��һ���������������ѷ��Ĵ�̬��ᡣ���ܱ�ȫ������Ҳ���ǡ�����
��Сƽ��������ı䷨ר��֮�У��������λ��ߣ�����ç����һ������������С���������ػ��������֣��������Ƿ���Ů��ȫ���ܶ�Ա��һλ����Ҳ������ƽ�����������µİ��֡����ٸ㵳��Ҫ�������£���ĸ����ơ��䷨ά�£��Ƿ�ҲҪ�����������£��������й©��Ŀǰ˭�֪Ҳ�����˸����ۻ𣬵�֪���Ѹ����������¡�����ܷ�������ϲ��£���������һ���Ĵ��˺�ͨ�����������Ĺ۲���ǣ���˵�����ˡ���ʵ����֮ҡͷ���Ե�ר��ѧ�ߡ��������ֵ�����֮������̨ý�壬�����Ű��ɡ�����������������������������������쳵�ı����Լ������ں�˵�˵������������յ�������´��ˣ�ԭ����ã���¶��ˣ�Ҳֻ���ɺϡ���˵���������س���ԣ�������ͨ����֪��ȥδ�����Ǿ������������ˡ���ҩ��ʦ˵�úã������»����ʺ��ˡ�����֮������������������ʦ���Ի��й�ƽ�����ϡ�
���ڿ���Ϊ����䷨���Ͳ�Ȼ�ˡ�����ȥ��δԶ��ʷ����ȫ��ˮ�����ڣ���ʵ��Ȼ������������������»����Ȩ��������Թ�Ѷϡ�����ʷ�ң�����Ϥʷʵ�����ɼ���δʼ�������۶�֮�ԣ�����ʷ���������ȡ����߲���dz�����������룬��Ϊ�ⴻ�������ڳ����£��������ԣ��Կ����ð¡������̽ᣬ��������䷨����ʷ�ϣ�����Ӧ��������λ�أ�
��������֮������һ����ʮ����й�����ʷ������ᷢչ�������ϣ�ԭ��һ����ת��ʷ���������йŶ����͵���ᣬת���ִ������͵���ᡣ��һת����ѻƬս����ʼ��ʱ������������Ȼ�ǻ����йű�Ե�ġ��������硹���乤��֮��ޣ������֪��������ʱ�Ĺ���үҪ��������ѱ�֮���͡�������֮��ָ��֮�䣬���Ȼʧ�ܣ�ʵ����ѱ�ī������һ�������һ�£����ǿ���˵��������䷨֮ʧ�ܡ��Ǹ���ʷ�ϵġ���Ȼ����
������ʷ�ϵġ���Ȼ����������Ϊ��żȻ�������ҡ���Ϊʧ�ܵ�ʱ�䡢�ռ䡢ȫ���ֲ�������ͷ���ʽ��Ӱ�����ڶ������ڡ�żȻ�����ء���Щ��żȻ����ʱҲ�͡���Ȼ���ij�Ϊ��һ����ʷ��չ�ġ�����gene����cause����
���磺��ȫ��ʧ�ܡ��͡��ֲ�ʧ�ܡ����߶��ǡ�żȻ�������Ƕ��߲�ͬ�Ŀռ䣬����һ����ʷ�Ļ��ʹ���ͬ��
���磺ʧ���ڡ����ա���ʧ���ڡ�ʮ���Ҳ������Ϊ���صġ�żȻ���������ⲻͬ���̵�ʱ�䣬������һ�λ���ķ�չ��Ҳ�͡���Ȼ���о����Ե�Ӱ�졣
�о�����䷨������֮����Ҫ����ƪƪ�������ʿ���Ϊһ�˵�Ե�ʣ��������������ʷ����Ȼ��������Ҫ�ġ�żȻ�������ǿ���Ϊ������˸�personification�����ѿ���Ϊ���ɿ���Ϊ��������䷨�������ʷʧ�ܵĹ��̣���������һ���������Ļ������ã����ܾ���ȫ��ͬ�ˡ�
ͨ�Ž�֮�䣬ʶ����֮��
�������ʷ֮�У����������ݵĽ�ɫ��Ӧ�������ۼҡ�˼��Һ����μҡ����ҿ���Ϊ���������棬�����������������߱�����Ϊ��Ϊ�ִ��й������ۼҺ�˼��ң����ļ�ʶ��ѧ��ʵӦ���Ž����������������͡����϶���ѧ��һ����dz����ʶ�������粻���������蹵����ǿ��֪��Ϊ֪��������Ϊ��������ë�㡸��Ծ����������ũ����ǧ����������Ƶ�ǿ��֪��Ϊ֪�����ʹ��һ��ʷ����
���ڿ���Ϊ�ĺ�ѧ�����Ļ��ɻ��������顢Ǯ����֮�ϡ����ҵ������ʲ��Է⣬����ħ�����˽�������Ĵ��������ʫ˵������ʷĪ����˾��������Ψ��һ������ǧ���ʷ���ϲ�����˾������������ʵ������Ψ��һ���ӽ��ļҹ۵������Ҳû������ֹ��������˵���ټ�������ԭ��ʢ�¡���ǧ�����ã��Dz����������ͨ�����ã�����Ӳ�Ľ����������ų�һ�С����������������壬�����黳���ȵ�������֮������ͬ��Ϊ�Ŀ����ɺ�������䷨ά�������佨���ԣ����������Ϻ�������ɶ���ľ��档��������֮Ϊ���й�������Ϊ��ʼ��ٸ�ߡ�������Ҳ�Ǹ���ʷ�ġ�żȻ����
���������ۼҡ�˼���Ҳ�Ͱ��ˣ�����Ϊ���ٿ�������������롢��������μ����ϧ����Ҳû�������μҵı������������Ǹ�������Ⱥ��ľګ��Ƨ��������̼����֪ʶ���ӡ���ʮ�����飻�ҹ�ǧ����ף�����֮Ϧ������������һ���������·���Ҳ�dz��¡����������Ƨ�����ɣ�ȴ�������·���Ū����ʧ����֮������ʱ��Ϊ��������һ��Ҫ���������¡����������游ȥ��֮�գ���Ҳ�ڹ�ǰ��ɻ®��ԯ�����²�ȥ�������겻ʳ�⡣���Լ�˵����ʱ��ɥ��������֮ѧ����ν����ţ�����ٲ㡣�һ����Զ�����������Լ�Ҳ˵������������������Ц֮�����������Կ䡸������㣬ִ�ش������ˡ������������أ��Ų��ں�������������أ�
�ǵ����˱ʼ��ೢ����ij�̣������š����ij��⡹֮˵��������ҹ��������һ�Ρ���ҲҪ���ռ�����ij��⡹�ؼ�¼����������Ϊ��������ľګ��Ƨ֮�ˡ�
�������꿵��Ϊ��̬��֪�ࡣ����С�д�ѧͬ������֮�У�����֪�ж��١��˸����䲻��ͬ�ĸ��������ʽ������Ӧ�˴���ǿ�����������˾Ͳ��ܵ������ء������㡸P��R�����������Dz����������ĵ����ˡ�
��Ϊ�����ڣ���һ�١����Բ��ۡ��ľ�ɥ����֮�£�Ҳ��ϰ���������з����������Dz����ʱ��Ū������Ц�����ij̶ȡ���Ҳ�Ǹ������ķ����Ե����Ա����ף�������Ц�����dz��ھ�����������ҽʦ�ԣ����˱�����֪������Ϊ����������ҽ�����伲�������롣�粡���Դˡ���������ǾͿ��ܱ�ɡ����ӡ����������Կ�����ѧ������̫�ס����������·��ӡ��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