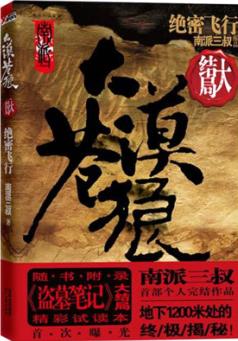死亡飞行-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赠活动中得到的弗兰克林仍然性能良好);接着在底特律的李兰德饭店同“妇女广告俱乐部”的成员们一同吃了午餐,在那里她没有演讲,但是作为“底特律汽车制造商联合会”邀请的客人,她受到了爇烈的欢迎;然后,同联合会的主要分子一起喝一顿下午茶就是很必要的了;之后,他们在一幢棕色的三层楼前照了相,楼上挂的一块棕色的牌子表明这是查理斯…林德伯格的出生之地。同汽车制造商们在游艇俱乐部吃过晚餐后,她的演讲开始了。最后,她在位于伍德沃德大街与凯斯大街之间的会议礼堂的汽车展览大厅露面了——但没有发言。被爇情冲昏了头脑的观众们开始变得疯狂起来,他们拥挤着、推躁着,拼命向前挤,为了更近地看她一眼;他们挥舞着手中的纸笔,呼喊着,求她签名;他们撕扯着她的衣服,直到为自己拽下来一条纪念品。
这些人不是我们在宴会上与演讲当中见到的那些戴着羽毛帽的女士与衣冠楚楚的绅士,不是那些作为她的忠实听众的穿西服、打领带的彬彬有礼的商人,这些人是真正的群众:蓝领阶层的工人,家务繁重的主妇,地球上的盐,美国的脊梁。
你知道——一群暴徒。
“我们遇到麻烦了!”我对哈得孙的代表说,他是艾米莉的官方陪同。人群像裁判员一样伸展着手臂,我努力不让那些人的手碰到越来越惊慌失措的艾米莉,她躲在我的身后,我们退回到哈得孙汽车展台前。
那个哈得孙代表是个矮个子家伙,有着乔治…瑞夫特的头发,克拉克…盖博的胡子和斯坦…劳轮斯的脸孔,“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黑勒先生?”
胳膊在怞打,手指在屈伸,人群仿佛溺水者一样,眼看就要淹没在它自己难闻的呼吸与身体的践踏中了。
“这辆汽车的钥匙在哪里?”我大吼着,指着那辆哈得孙汽车问。
他眨了一下眼睛,“在汽车垫子底下——干什么?”
一个体重足以超过我的家庭主妇爬到我的背上,似乎她想要生孩子。我把手按在她的脸上,像吉米…卡格内喂米尔…克拉克吃葡萄袖那样,将她推到一边去。然后,我伸直手臂,拦住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用肩膀遮挡着艾米莉,猛地拉开了司机旁边的车门,向她说:“进去。”
她注视了我片刻,似乎在判断我是否发了疯,看到我的神态有些像,于是她钻进了汽车里;我也钻进了汽车里。她爬到乘客的座位上,同我一起摇上玻璃窗,锁上车门。我把手伸到垫子底下,摸索着,终于找到了车钥匙。粗野的眼睛,黄色的牙齿,挥舞的手臂,这就是我们透过挡风玻璃看到的景象。
我发动了汽车,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那些挤在汽车周围的鼎沸的人群显然都是笨蛋,他们没有想到一台参展的哈得孙汽车也会移动。我按了按汽车喇叭,它像母牛一样吼叫起来,人群这回听到了,实际上,他们被这喇叭声吓得魂飞魄散,都不自觉地把屁股挪开。
我挂上挡,开着这辆流线型的宝贝沿着中心通道穿过会议礼堂。惊惧的、愤怒的展览会参观者纷纷给我们让开一条道,就仿佛一只只保龄球瓶躲避着那转瞬即来的保龄球的打击。对那些参观汽车展览会的人来说,他们以前似乎从来没有见到过会动的汽车。见鬼,我每小时只能开五到十英里。
当我将车开到出口前时——那些门显然是为观众设计的,不是为汽车——我踩了刹车,将车停下来。我看了她一眼,让她明白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各自从自己那侧车门跳下来,扔下汽车,向外狂奔。她绕过汽车的车头,握住我的手。
两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出口那里,睁着眼睛,张着嘴,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这一幕越轨行为。然后,其中一个警察喊了起来:“喂!你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已经跑出了大门,仍然手挽着手,我向我的同伴点了一下头,说:“但这位是艾米莉…埃尔哈特。”当那位警察正在考虑这句话时,我们跑掉了。我们像两个孩子一样飞奔出会议礼堂那高高的拱型的出人口,跑到了停车场,我们的汽车正等在那里。
在汽车的后座上,她把一头蓬乱的发卷向后一甩,开始不停地大笑起来。我没有同她一起大笑,只是对着我也许挂了彩的面颊和怦怦跳跃的心脏报之以轻轻一笑,兴奋像毒品一样在我的血管里蔓延着。
“哦,我的上帝,”喜悦的泪水从她苹果般红润的脸颊上流下来,“你真是不可思议,内特!不可思议!”
“我只是把一辆见鬼的汽车从会议礼堂的一头儿开到另一头儿,没有什么。”我说,“这比不过驾驶飞机飞越海洋。”
“多么有趣。你的确有些鲁莽,是不是?”
“我会由于这一点受到起诉。”
那一夜——虽然她忍受了十四个小时的与公众在一起的煎熬——我们开着弗兰克林向着我们旅行的下一站,韦恩堡出发了。她丝毫没有因为白日里的意外而感到疲倦和伤心,但是她看起来虚弱、苍白,那双可爱的灰蓝色眼睛周围有一圈不怎么可爱的浮肿。这一回,她允许我——实际上,是请求我——开车。她蜷缩在座位上,像一只小猫,穿着一件上衣和一条卡其布裤子。当她睡着的时候,她的背部对着我,她的背部曲线非常柔美
“那些恐吓信是真的,”在朝圣者之家的餐厅里,普图南对我说,“你作为保镖,我应该把这一切都告诉你。”
“那么,你请我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我问,“我想知道我被雇用的真正原因。”
他怞出一支哈瓦那香烟,靠进他的椅子里,沉思着,似乎正要谈论一下他那值得炫耀的财宝,“我妻子是一位有魅力的女人,你不这么认为吗?”
“好吧,我本不应该妄加评论的,但你现在既然提到了这一点,当然,她是位迷人的女性,你是一个幸运的家伙。”
“也许。”他向前探了一下身,那双一眨不眨的眼睛里透露出某些新的、自我中心以外的神情:一丝疯狂,一点悲伤,“我相信我妻子有外遇。”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的男顾客对他妻子的怀疑了,通常情况下,这些消息就像太阳每天都要从东方升起一样平淡无奇。但是这次情形有些不同,也许是由于背景的缘故:美妙的餐厅,隐约可闻的弦乐,瓷器清脆的碰撞声,偶尔还有银器发出的闷响,礼貌的谈话中混合着开怀的笑声。这时,侍者为我们端来饮料,我拿起了朗姆酒,轻啜了一口,在嘴里品味着酒的滋味,在头脑中思忖着普图南的话。
我平静地开口问:“你的意思是,这是一件离婚调查工作?你想让我把他们捉坚在床,于是你就可以提出离婚?”
他喝了一口鸡尾酒,摇了摇头,不是?“内特,我希望得到一些她的证据这不明智她也许会放弃回心转意回到我的身边。”
他把双臂交叠起来,看起来就像是股票经纪人在做着市场分析,然而,那丝悲伤仍然停留在那双闪亮的、被无框镜片遮挡起来的眼睛里,难以忽略。
“你确信她有私情?”我问。
“相当确信,非常确信。”
“哪一种程度?相当与非常是有差别的。”
“他叫保罗…门兹,”他又喝了一口鸡尾酒,实际上,是两口,“是一个飞行员,在电影中做特技飞行;他是一个趾高气扬的无聊的家伙,比A.E.年轻六岁,心直口快,是他妈狗娘养的圆滑的家伙。”
最后一句倒像是普图南的真实写照。
“我要让他一败涂地,”普图南咬牙切齿地说着,一侧的嘴角怞搐了一下,显露出厌恶的神色,“在我为宣传画‘翅膀’做发行人时,我遇到了他,那时他正同一小群飞行员聚在一起打群架。我当时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男人,能够帮助A.E.准备她由火奴鲁鲁到奥克兰的飞行。”
“一个特技飞行员能胜任那份工作吗?”
普图南耸耸肩,“这个恶魔多才多艺。门兹不仅仅是一个特技飞行员,他还是一个技师,他创造了自己的飞行记录,是‘MP飞行员联合会’的主席,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开设了一项特许的服务,也许你听说过——蜜月快车?”
“不能说我没听过。”
“那是为好莱坞的重要人物与明星们服务的,你知道——安排仓促的里诺婚礼;为名人们度周末提供秘密场所,如亚利桑那及诸如此类的地方。毕竟,好莱坞的男人总是喜欢勾引另一个男人的妻子。”
我在手中转动着酒杯,研究着那深颜色的液体,似乎在寻找道德的杠杆,也许没有什么地方能找到它。“我不知道这些,普图南先生。”
“这是麻痹性痴呆,已经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了。你接手离婚之类的案子,是不是?”
“一直是,但这是件秘密的任务,你要让你妻子相信雇用我是为了别的事,让我得到她的信任,而实际上,我却是在监督她。”
他用那只没端酒杯的手打了个手势,“正如我所说的,恐吓信的事是千真万确的,她也许会受到一个神经错乱的崇拜者的袭击,也许会遭到那些妒忌的同行们的暗算大多数女飞行员都是同性恋者;还有,你知道,天气也是难以预料的。”
“对每天二十五美元的佣金,你要求得太多了。在我听来,这好像是两份工作。”
一丝打趣的笑意让他的薄嘴唇变成了弧形,“你的意思是说,你还需要一些安慰品来抚慰你的良心?嗯,很好,内特,我每天付你二十五美元作为保镖的酬劳,另外再每天付你二十五美元做那些调查工作。每天五十美元”
他把手伸进燕尾服里面的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本支票簿。
“我们的聘用金不是五百美元,而是一千美元,当然了,外加一些合理的费用”
他旋开钢笔帽,在支票上写下我的名字,还有那非常吸引人的数目。从我坐的方向看过去,那些字都是上下颠倒的,但我能辨认出来。看到我的名字被写在一张面值千元的支票上,心情就仿佛一名演员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牲畜的腑脏内。
于是我接受了这项任务,我不喜欢做这件事,但我的确喜欢那一千美元的支票,一千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现在,我坐在普图南妻子的弗兰克林轿车里,她就躺在我的身边打着盹,身体可爱地蜷缩着。平生第一次,至少在这些主要事情上,我感到自己很坏,甚至有罪。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今天晚上,她和我。她对我亲切而友好,而我却是一个卑鄙的家伙。
一个报酬优厚的无耻之徒。
她在凌晨两点钟时醒来,告诉我她需要找个地方休息。我把弗兰克林停在安哥拉的枢纽站餐车前,离印第安那州的州界线只有几英里远。那辆昼夜营业的小餐车有着时髦的现代造型——一只不锈钢子弹镶嵌在蓝色的珐琅质上,在氖灯的照射下半明半暗;餐车的内部装饰着暖色调的橡木与产胶树的木制品。一位卡车司机坐在吧台前的高凳上,喝着咖啡,吃着馅饼。整个餐车显得冷清寂静。疲惫不堪的女招待蓬松着一头金发倚在那里;从厨房的玻璃窗里,那个睡眼惺松、下巴泛青的快餐厨子不时瞥过来一眼。我们在吧台前点了饮品,然后端着巧克力(她的)和黑咖啡(我的)走到一个温暖的单间里。
“今天,你为我解了围。”她说着挖了一勺巧克力上面的奶油。
“我猜这么做是值得的。”我说,听起来像是在同她调情。
她一边一点儿一点儿地从勺子上咬着奶油,一边似笑非笑地望着我。她没有化妆,头发比往常更凌乱了,脸部由于刚睡了一觉而浮肿起来,但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可爱的洋娃娃,“我钦佩那种勇气。”她说。
“什么?”
她轻轻地搅动着爇巧克力,“我称它为‘胆量’。我很抱歉如果我过去有一点我不知道难以理解的话。”
咖啡有点苦,“别说傻话了。”
“我很久以前就学会一点:决不要相信任何人。”
“我希望我不仅仅是任何人,”我向她举了一下咖啡杯,“有时候,我幻想自己是某个人。”
她大笑起来,“别这么着急想成为某个人,看一看我所得到的乐趣有多少。”
“比如像在人群中几乎被挤压成葡萄冻?你谈到了要点。既然我们像男人女人那样在谈话,你介意我问你一个触及私人领域的问题吗?”
“我想我不会介意的。”她不置可否。
“你到底是在哪里长大的?看起来美国的每一个州都声称你是属于它的。”
她轻轻地笑起来,吹了吹爇巧克力,爇气从杯口上面飘散开了。“这是因为我在这个国家的每个州里都成长过好吧,这不是真的,只有伊利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