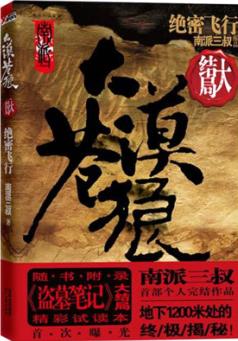��������-��4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ں��档¥���ƺ�û�а�ȫ���ڣ����ൺ�ķ����Ӳ�Ա��Ȼ���ְ�ء�
�����������ˣ����ŷ��䣬����������ע�����ķ���ǰͣ�½Ų���ת���Ű��֣������Ų�û�����ϡ�һ˫��Ь���ڷ������棬�һ���Ь������ɫ�Ļ���ǽ�Ͽտյ�����һ�ȹ��Ŵ����Ĵ������¥�Ե�һ��ľ���ӣ���ȻС¥���������ʽ�ģ�������ĸ��ȴ��ȫ�ձ�������̺���ϺõIJݵ棬�������ڵ��ϵ�������ֻ������ڵͰ��ƾɵ���ľС��ǰ��û�бڳ�������һ������ܣ�Ψһһ�������κη��ձ������߸е���ͬ�Ķ�������һֻ�����ӵ���ױ̨��
���������ҵ����а��ͷ�����ױ̨�ϡ�
���������Ҽ���˰��ڵĶ������ҵ����ҵIJ�������ǹ����װ��ǹ��ĵ������������õ��п������ƺ�û�˶�������������ǹ��̧��ͷ���ھ����п����Լ�����������˵��һλ��ǹ��ʦ�Ŀ��ҵ�����
��������Ȼ������ͷע�����컨�壬����Ϊ�˵õ��ϵ۵�ѵʾ��������˼���������Ļ����Ǹ�Ů�ˣ����������������ڵڶ���
����������ô����Ӧ����ô�죿��¥ȥ���ŷ������ţ������ҵ���ǹ���Ա�����Ҫʱ������ף����
��������һ������������ס���ң��Ҳ�֪���ǰ���ǹ�������а���ã����Dz������䣬�ú������ڸ������á�
��������������������
������������˾ֳ���������
�������������ң�ʲô�£���
���������Ұ���ǹ�Żص����а�����˷��š�
������������˾ֳ�������վ�����⣬˫�����Ŵ���ɫ���µ�ͷ������ϣ����������е����ʡ���
����������лл������ܺá��������
����������������ҵ���һ��ͷ���������ǾϹ���������Ь�߽����䣬�ҹ������š�
��������������������������к�������˵������Ϊ���ǹ������𣿡�
����������������üͷ��������˹�����ţ����Ǹ������鷳�ˣ���
����������û�У���ֻ�ǿ��������ǵ��·��뾯�������ú��档��
����������������
�������������������������������˼��ֲ�ͬ��˵�����ּ�װ����һ�������J����һ���Լ��ſ������ơ�
���������������ˣ����������������죬��ʮ����Ī����Ϊ���ǹ��������ڲ������������ý���˹������һ����ָ���������Ҳ��ȥ��ģ�����Ǹ����Ӵ�Ӳ�IJ�Ī�������ϵĵ��̡�
���������ҵ��ͷ��֪����ָ����˭��
��������������˵���������ý���˹��ʱ���������أ�����˹�Ǹ�һ���ġ�ռ�翭������̽�������չ������ˡ���
��������ͻȻ֮�������˵�������ʦ���������������˼����˵������˹�ڵ����Ī���˵ķ��﷽������С�
�����������ţ�����˵��������û�и������鷳������˵���������Ұ��æ��ͬһ��ס�����ùݵ�Ů���йء���
�����������ǵģ�������˾ֳ�˵�����ҿ��������𣿡�
������������Ȼ��
���������ܿ죬�����ڵذ����������������������
��������������ɫ�Եú����أ��������һ���ź���ζ����ͬ����ϲ����������٣�����Щ����Ϊ�ù��е�Ů����������ķ�����Ӧ�õõ���ˡ������˵���Ǹ����ˣ�һ��������Ů�ˡ���
���������Ҿ����������Ļ�������������ĺ�����¶�������������ɵ�˵����������ǡ�������˵���Ǹ�Ů�ˣ���Ҳ��һ���������ˣ���Ҫ���ˡ���
����������������������ġ�Ȼ���Ҳ���ͬ�������������ݼ���Ľ�ɫ����������صģ���Ӧ�ñ���������
��������Ȼ������˾ֳ��������������һ��æ��
����ʮ���¡�����ȡ��
���������ź���һ����͡�ѹ�ֵ���������ʲô�£���
���������������������������Ҷ���ϣ�����������룿�������Ҵ�Խ�����£���Խ�˺����Ǹ��ͳ��ĸ��д��Ե�̹�ʵ�Ů���������Ҵ���û��������ٴ���������
�������������������Ҷ�����˵����������ȥĦ���Ǵֲڵ�����߲����Ű塣
������������û�з�Ӧ�����DZߵ���ֻ��ŵ�����������֡�
���������������ҿ������·�һ��С���ӳ��δ���ʮ��·�ڡ���¥�ݲ������ȵ�һ�ˣ����������ȵ���һ�ˣ�û������˾ֳ���Ҳû�����IJ�Ī����å���֡�����Ȼѹ�����������Է���һ����͵������
������������������������ɭ����
���������ƺ�����һ����������������Ҳ����ֻ�Ǽ����ӵ�ʱ�䣬�����������ѿ�������һ���죬¶����һ�ŲĻ��˵�ױ����Բ�ε�������������������ͷ��Ϥ�����ɵ���ɫͷ���£�һֻ�����������Ļ���ɫ�۾��Ծ��������ң����ŵ�ס��ߵ����˵�˫����û��Ϳ�ں죩�ſ���һ�롣
������������֪���Ҳ�ϲ�����ѻ�Ů�����Ͽ���ʲô�𣿡����ʡ�
���������ſ��ô���һЩ��¶�����������������ϳԾ��ı��飬���·������Ȼ�������촽������������ƺ��뼷��һ��Ц��������ʲô����
���������������������ù�����档��
�����������������һ�����������Ƶ�ҡ��ͷ���������촽�ϣ��۾�����������ˮ�����߽����䣬�ѷ��Ź��ϡ����������ݶ��ˣ�����û�й�����������������ݣ����������ݹ���ᾡ�������һ����ʽ�Ķ����˶�����һ�����ɫ�Ŀ��ӣ�û�д�Ь���������������ˬ��
�������������˽��һ���֮ǰ����ֻ���ü�ע���Щ���������ر�ס�ң��ҽ�����ӵ���������������Լ�����Щ�������ҵ���ǰ����ţ�һ����һ���ỽ���ҵ����֣����������ľ���Ҳ����Ҳ�����ᡣ
�����������㵽�����������˵��������ô�ܵ�������������㵽�����̫����������
����������һ�������������˺ܳ�ʱ�䣬��ɬ�����ᣬ�������ƺ�û�о�ͷ�������������ѿ����ң�ֻ��һ��㣬�������ҵ��ֱ��У����Ի������ע�����ҡ����ƺ���˵���κλ����������ȵ��������ڳ��������
�����������ǣ����ٴ����ң��k�ҵأ���Ʒ��������ζ����Ȼ�������̧����ͷ��
�������������ŵ��������������˵������ָ����һ���İ�Ӳ�죬����Ҫ���ؽ����Ľ̹档��
������������Ц����������һ����������ͷ����˵������ɭ��������һ����ʦ���ܺú���Ȥ����
�����������Dz����������������Ҿ��������Ļ��������������������һ�����ķ��䣬�������������Ļ���
�����������������ͬ�ҵ����ƣ������м�������Ϊ���������ˡ������Ķ�����һ���൱�ƾɵ�����ɫ�Ĵ���ɫ����İ����η��ڴ�ǰ���������ھӵķ�����Զ�����ݶ���һ���ձ�����С�����ϰ���̨�����̻Ҹף��̻Ҹ����м��β��㣬���������ڷ�������������Ʈɢ���Զ��������ǰ�������������˵������Ҭ��ɵ�ζ������Ķ�����
����������Ҳ��ͬ���IJݱ��̺�����ڵ��ϵ�˯齣��Ͱ�����ľС������ڵذ��ϵ����档�¼��Ϲ��ż�����ʽ��������ȹ�����и��ӳ�����մ�������۵��ƾɵķ���Ƥ�пˣ�������ά�������Ҵ�ʥ·��˹���������ʱ�����ľ���������мпˡ��Ҽ����ǽ�ڡ�����������ױ�������ǽ�ڡ������ҵ�һЩ���ӿף���ʲôҲû�У����������û�б��˼��ӡ���������û��ʲô�ɵ��ĵģ��ձ����ڼ����������澮����ô���С�
��������Ȼ�������ǻ��ǰ�����ѹ�úܵ͡�
�����������㵽�������ʲô�������ʣ��������۾�ע�����ң��������۾���ı����ǻ��졢���ɻ��ǿ־壬�������ϵ۵ķ��ϣ��㵽���
�������������������𣿡�
����������û�У�����˵��һЦ����������û�С������е�����������촽���³��������ٴ�Ͷ���ҵĻ��С��ҽ�����ӵ��������Ȼ����˫�������������������ţ������ţ�֮������������۵�������
������������ΪʲôҪ�������������ʣ�����ѹ���ҵ������ϣ�˫�ֻ������ҵ������ƺ����������һ�������ˣ�����Ϊʲô��
������������֪��������˵�������DZ������ģ�Ϊÿ��һǧ����������
�������������������ҵ��·���ƽ���ش�Ц������
������������ֻ�Dz��ϳ��ϣ��Dz��ǣ���������ע�����ң�¶�������õ�Ц�ݣ�������һ��������ɵ�ϣ��ҵ�Ψ����ͼ����̽�Ƶ����Ȧ��Ϊ��һ��Ů�ˡ�
���������кܶ���������ѯ�ʣ���Ҫ�˽⣬Ȼ����֪��������Ҳ�������������⣬ֻ�Dz�֪��������𣬴������������Ǿ�����վ���ţ����������ţ�������˵������ԭ��ΪҲ����
����������ע�����ң������Ǵ�Ȥ�����飬��ʲô����
��������������Ҳ���б����ͬ����һ�𡣡�
����������˭����������һ��üͷ���������£����������������µļ���������ļһ��
���������������Ұ����������к����𣿡���Ц�ľ���һ���Ӵ��ҵ�����ð�����������й�һ�����Ӷ����ǰ����������ߴ������𣿡�
������������Ц��ֻ������һ�������ס�ˣ�������ָ�ᴥ��һ���ҵıǼ⣬Ȼ���ʣ���˭�������һ����ˣ���
����������������顣��
������������ꣿ�������ϵ�Ц������ˣ����Ҵ����ͬ��˯��������
������������һ���������ô������
����������������ǰ����һ�£������治�������Ǹ�ɵ�����ϣ���㲻Ҫ̫ʧ����ϣ�������Զ����������ֻ��Ϊ����һλ�������������������˵�ⲻ����һ���龪ʱ�����������ظ�����
������������ס������������������˵�������������ظ���Ȼ��Ҳ�������Ϊ�㺢�ӵĸ�������һ�����ǵĺ���Ҫ�������Ļ����ﳤ��
�����������J�������������۾���¶����������飬���˵�ͷ������ס�ҵ��֣������ߵ����ڵ��ϵ�˯�ǰ������������ȥ������˫�ˣ�����ӡ�ڰ�����Ϸ�ĺ��ӣ�˫�ֻ��ա�
������������Ц����һ˿����Ȼ������ɭ���ҿ������DZ���¡�
����������ʲô�£���
������������ԭ��Ϊ�Ǻ�����ԶҲ�����к����˲������������Ļ���������������Ļ����¡���
��������������ʲô��˼����
�����������������ҵ��֣�����ԭ��Ҳ��Ϊ�ǻ��У���ɭ���������ھ�������ҡ��ҡͷ��������������Ȼ���ź���������˵�������ߵģ��ţ�֢״�����Ƶġ���
�������������ֱۻ���ס�������������ҵ����ϣ�����ѡ����һ���������dz���Ůʿ����
������������͵�Ц����������ʲôҲû�ио��������ǰ��Ҵ���������ʱ���������������ú�������������õ����ҵIJ��Ʒ�չ��һ��ǧ�����������������ҽԺ��ס�˺ü������Ҳ�������ˡ���
������������Ҳ�������������������
����������ת����һ�����飬���²����ص��˵�ͷ����Ŷ���ҵ��ϵۣ��ǵ�����������ͬ������һ�����η��������������С¥�����ĸ�������Ż���η�������ֻ������������죬�һ����˹�ȥ��������ʱ���Ҳ�֪�������������Ժ�
����������������üͷ������ô˵�����Dz���Ҫ���ˣ���ʲôʹ����Եģ���
�������������ʼ磬���������Ǹ��Ҵ������������Ҳ���������������۾��������ң��ƺ�ֱ���˿��������Լ������Ҳ���һ����Ӱ�����㵽��������ʲô����ɭ��˭��������������ʵ�ð�յģ�G��P������
���������ҵ�Ц����ÿ��Ʋ�ס��˻�ƣ����������ǣ������������ˣ���������ǰ��Ȼ�����ֽ��˻顣��
��������ѪҺ������������ʧ��������ɫ�����ˡ�
�����������ˣ�����˵�����Һܱ�Ǹ�Ҷ�����²����������ô�����ԡ�
����������ûʲô����ֻ����֪�������Ѳ��ٰ����ˣ����Ҵ���Ҳû�а������������İ�����������һ�����壬��֪����һ�ִ��ϵ����������Ӧֵ�������Ҹ���Щ����
��������������ԶԳ�ʫ�಼������
����������������ȻһЦ������ָ��ס�ҵ����죬����ק�ţ��������˼�ǣ�����ʦ�����������ķ���ģ�˭�������ģ��������ɫ�ķ��ӣ���
�������������������Щ���ϴ��ǵļһ����˵����ɽķ���������ĸ���˽�����ǡ���
���������Ҹ�������������һ�У��ü��������������س����˸�Ҫ������һ���������Ǵη���ʽ�ĵ��鿪ʼ������˵���������˹����������������������ȫ����ʱ����������¶�����Ի���ֳԾ������飩������Ŀǰ�������ݰ��������;�����ʹ����������ֻ��ʡ��������˾ֳ������Ұ���¡�
��������Ȼ���ֵ�������������Ŭ����α��ձ�ս�����ɳ��Ĵ����ȫ���̣�������α�������һ���������еĵ��ϣ�������ҽ��ҽ����Ŭ���Ƚ���ˮ��ʱ�ܵ��ˣ�������α���һ���ձ���������ת�Ƶ���һ����;�о�������С����������ൺ�����������ൺ���ܵ�����˺�����һЩ�˵����ʡ������Ƿ����Լ��Ǽ����Ҳ���Ѱ����������ӽ��˺�����������˼��Ρ�
�������������ڼ�����赹�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