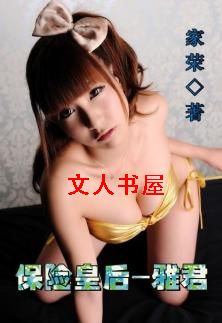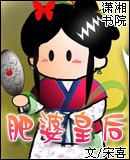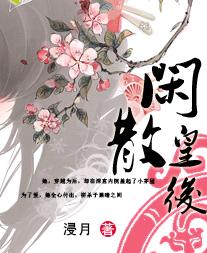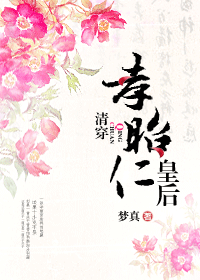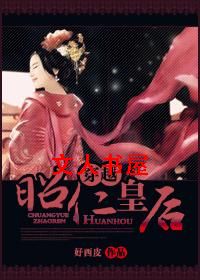长孙皇后-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十六章 帝后
半年,整整半年,若水再次见到了太宗皇帝,一身淡紫色的长袍,只在衣边用银丝勾出了龙纹装的图样,没有想象中的霸气凌人,反而显得风华高雅,但眉目前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容任何人违抗的尊贵。
若水一脸平和地与皇帝并排走着,眼眉微微低垂着,丝毫看不出手被紧紧扣住的不适。长孙无忌则跟在两人身后,一手牵着很是不安的明瑶,另外一边走着的两兄弟则比妹妹要镇定一些,安静,无比的安静。
山雨欲来风满楼,冬至的夜晚,长安的上空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
皇后的居室里同样还是一片寂静,许久未见的皇帝与皇后,这一对世上最尊贵的夫妻就这样隔着案几面面相坐,皇帝并没有发怒,只是直直地注视着自己的妻子,好似从未见过一样;皇后则稍稍侧着头,似乎正望着桌上的茶杯出神。
“陛下,皇后娘娘的汤药送来了。”门外传来广月的声音。
皇上没有回头,只淡淡道:“送进来吧。”
门被小心翼翼地推开,广月请过安,走至皇后身边,“娘娘,该吃药了。”
若水的嘴角微微一动,似乎说了什么,但随即便点头道:“先搁着吧。”
“可是娘娘,御医说药凉了便就没用处了。”
若水摆了摆手,没再说话。
广月见状,只好退下,在合上门之际,隐约听见皇帝的声音,“若水,怎么不喝?”
“苦得喝不下呢,陛下。”若水并没有再沉默下去。
皇帝似乎笑了一笑,“不喝药怎么行?朕还指望着若水快些好起来,好跟朕回去啊。”
“是若水的不是,不过人们常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陛下以为呢?”若水嘴角微微扯动,真是个不好相与的主。
“啊,那真是朕疏忽了,不过皇后觉得还得过多久才能回宫呢?今天,朕可是亲眼见着皇后的好气色呢。”皇帝的语气中渐渐带上了强硬之感。
若水没有回答,反而端起碗,一口一口地喝起药来,果然并没有一丝苦味,反而带了点甘甜的味道,不过样子还是蛮唬人的。
皇帝只是静静的看着皇后喝着药,眉头一挑,语带深意,“朕等得,可有些人似乎等不得了。”
若水一怔,微微呛了一下,放下碗,低头咳了几声,再开口的时候,声音便有点沙,“有陛下在,自然不会有什么大碍。”可语间似乎带了点嘲意。
皇帝听完,好似有些漫不经心的伸出手,越过窄窄的案几,撩上妻子方才散下的几缕青丝,“在其位,谋其政,皇后不是应该最清楚不过么?”
若水一时语塞,也顾不上对方略带不妥的动作,最后只搪塞道:“总得再养上一阵,陛下也不想一个病弱的皇后在宫中吧。”
皇帝嘴角含笑, “等到年三十那天,朕希望皇后已经在宫里呆着了,否则,朕瞧着,回宫养着也是一样的,皇后觉得呢?” 说着,手指间微微加上了几分力气。
若水轻声呼痛,抬手想要拯救自己的头发,不料,反倒手被皇帝握住,只好回道:“是,臣妾明白。”
皇帝凝视了她片刻,终于放手道:“等回宫后,朕再来每日帮皇后把头发绾起吧。”
若水顿时觉得呼吸一窒,半晌才勉强笑道;“那臣妾先谢过陛下了。”
“朕怎么觉得,若水唤朕二哥的时候更亲切些呢。”皇帝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
“二哥说笑了,夜深了,外边又下着雨,二哥还是住上一晚,明早再回宫吧。”若水苦笑了一笑,想扯开话题,顺便下逐客令。
皇帝的笑容里忽然带了点玩味,四周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后说道:“和立政殿比起来,这儿是小了不少,不过当初我们在太原的寝居倒也差不多是这般大小,若水可愿意和为夫分享一下?”
若水深吸了口气,嘴边扯开一丝弧度,“要是若水将病气过给陛下,那可就是若水的罪过了。”
皇帝不以为意地站起身,“若不是朕还得连夜赶回宫,若水可真的要与为夫分享一下了。”
见皇帝准备离开,若水暗暗松了一口气,口中还是随便应了一句,“外头雨下的大,皇上还是留上一晚为妥吧。”
“ 若水,不用着急,来日方长啊。”皇帝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妻子,临关上门之际,突然想到什么,说道:“明日,朕会派人来将承乾,泰儿和明瑶接回宫,没孩子打扰,若水想必会好得更快些呢。 对了,等若水回了宫,朕也才好缓出心思来想想该给承乾换个太子太傅。”
若水好似想要说些什么,犹豫了下,还是将话咽了下去,直到门被关上,才重重地坐在床边,沉思了许久。
“小姐,陛下可有说什么?”广月与淡云进来服侍若水洗漱。
若水抬了抬手,“快去把承乾叫来。”
“小姐,太子怕是睡下了。”
“那去看看,若是醒着,便让他赶紧过来。”若水想了想说道。
淡云答应着退了下去,不久便领着承乾进屋来。
“娘,父皇可是为难你了?”承乾焦急地看着母亲的脸色。
若水安慰地笑道:“别胡思乱想,只不过说了些要紧的事。明日,你们三个就得回宫里去。”
承乾失望地撇了撇嘴,“娘,我不想回去,想和娘在一块。”
若水摸了摸他的头,正色道:“傻孩子,娘过一阵也得回去啊,既然这是我们逃不开的命运,除了面对,别无他法。这么晚把你叫来,有些话娘一定要先和你说过才放心。宫里不比这儿,但也不用太过惧怕你的父皇,他也不是天生便是皇帝,这是其一。其二,太傅的课若是无趣,忍一忍便是了,等娘回了宫自有大算。其三,承乾你千万要记住,从此刻起,一定要开始要学会自制,在决定每一件重要的事情前,先想三遍,对自己是否有益处,对家人是否有益处,对家国社稷是否有益处,若是没有,甚至有害,即使你再想做,也要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欲望。这些可都记住了?”
承乾有些似懂非懂,可还是乖巧的点头。
“原谅娘亲,你这么小就要肩负起大部分人一辈子也不用考虑的期许和重担。”若水心疼地说。
“不会,娘亲教给我的都很有趣。”承乾摇摇头,“娘亲,外面雨下的好大,可父皇和舅舅刚刚走了呢。”
若水似笑非笑,“承乾,你的父皇和舅舅都是极有自制力的人呢,尤其是你的父皇,君主,有所为,有所不为,即是如此了。”
方才自己如何看不出李世民竭力压抑着自己内心的情绪,或许他当时最想做的不只是大声地质问自己,甚至想把自己立刻带回宫,可现在并不是自己回宫的最佳时候,所以他忍耐着,想到这里,若水无意识地喃喃道:“年三十?”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么?
承乾听见了,问道:“娘,你过年前会回来么,好想和娘一起过年呢。去年的时候,娘都跟在父皇身边,忙着大小的皇宫宴席,都没什么空和我们在一块儿。”
若水顿时醒悟过来,却不动声色,低头亲了儿子一口,“好了,快去睡吧,明日还要早起呢。”
这时的皇帝与大舅子一起坐在回宫的马车里,皇帝闲闲地问道:“无忌,你怎么没坐金辂回去呢?”
“请陛下治臣的不敬之罪。”无忌没有分辩。
“不敬?”皇帝凉凉地笑了下,“你思妹心切,朕怎可怪罪,不过你出现的也真是时候,朕可是很好奇皇后的答案呢。”
长孙无忌依然平静如故,“陛下与皇后原本便是是佳偶天成,皇后自然也不会有别的答案。”
明知道自己的大舅子今天习惯了睁着眼睛说瞎话,他还是继续问道:“说起来,无忌,你可曾见过若水象今天这般模样?”
不算太大的空间里静了一下,“臣刚才想起过去家父还在世的时候,常常抱着若水和臣说,等到天下太平,边疆再无隐忧的时候,便辞官带着全家人回乡间过平常日子,那时若水便回道,如果世间真有个象桃花源一样的地方,她便永远也不出来了。”长孙无忌话语间带着一丝涩然,“其实,若水才是最象家父的一个。”
皇帝久久没有言语,最后似乎自语着说:“若是长孙将军还在,想必不会将若水许配给朕吧。”
第十七章 听政
对大唐的大部分子民而言,从贞观二年末到贞观三年元月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登基已满两年的皇帝英明睿智,又爱民如子,尽管天灾还时有发生,不过生活还是从隋末的战乱中渐渐恢复了平静。而对于那些身处庙堂高处,后宫深处的男人与女人来说,不过四十多天的时间却是暗潮汹涌,让人措手不及。
在皇帝陛下从天祭回来后的第二天,太子,四皇子与长乐公主便被毫无征兆地从别宫接了回来。这原本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望与怀疑,不过皇上随即下的第二道命令,可就造成了宫中极大的不安,原本在宫中各有居所的皇后的三个亲生子女被安排住进了甘露殿,由皇上亲自照顾。
皇家有皇家的规矩,不过即使不是皇室,那些贵族世家的孩子也大多由乳母,下人照料,亲生父母反而极少自己抚养,更何况当今皇上登基不久,正值日理万机之时,这一行为直接传递到旁人的眼中造成的流言便是,皇后似乎已拖不了多少时日了,故而皇上将亲自负责孩子的教养,以此来宽慰皇后之意。
而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发生在翌日的早朝上,群臣们竟然发现太子殿下换上了只有在大典中才穿过的太子朝服跟在陛下后边,随后面色平静的跪坐在皇帝的左下方。
早朝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说话,而是都拼命想不留痕迹地向国舅长孙无忌和太子太傅李纲望去,谁知两人一个是气定神闲得立着,目不斜视,另一个却表现得同样诧异。
随后,只听见皇帝波澜不惊地说了一声:“从今日起,太子每日早朝随朕在两仪殿听政,用过午膳后,再由太傅在书房授业。”
这完全只是一句告知而非询问,甚至连一句形式上的“众卿家有何异议”都略去了。
即使在太子出现之时,不少人已有猜测,但是当皇帝明白无误的说出“听政”二字时,众人还是惊愕不已。皇权是独一无二的,而如今皇帝的边上出现了另一个人,即使是国之储君,未来的天子,但今上正值盛年,子嗣承继又毫无隐忧,那么如今让年近八岁的太子殿下如此郑重的出现在群臣面前,其宣告的又是什么呢?是明召天下太子的地位无可动摇,还是……?无人敢继续深想下去。
在位于三公之内,可以参加内朝的的官员中,尚书左、右仆射,房玄龄与杜如晦,皆与长孙无忌相交甚深,对皇后也极为敬重,自然不会对皇帝的举动有所异议。
而侍中王王圭再看了一眼魏征后,还是没能忍住心中的疑惑,不过还是用了比较委婉的语气出列谏言,太子尚还年幼,蒙童授业还未齐备,听政似有所不妥。
皇帝不以为然道:“朕幼时擅于骑马,好弄弓矢,而读书甚少,而后方对史籍兵略多有涉及,皇后年十三婚配于朕,不久时逢太穆皇后早逝,家族内务疏于掌管,皇后代为管之,谨言慎行,公正宽厚,众人无一不服。太子身为朕与皇后的嫡长子,又是将来的一国之君,书中确有圣贤,但仍应及早涉于朝政,才不至于将来只懂得纸上谈兵而祸及家国。”
下臣均再无二言,开始正式论及朝政。
房玄龄先上书道:“起禀圣上,自贞观元年七月山东大旱,皇上免其一年租赋,可今年关东各郡县仍少雨多旱,庄稼收成甚少,关东的地方官奏请圣上望朝廷能否再免其一年赋税?”
皇帝接过郑吉递上的奏则,仔细看过后,便交给太子过目,随即便开口道:“各位卿家有何建议?”
魏征最先进言,认为应当予以免除,天灾无可避免,若君王无所行为,百姓无所依靠,则必将造成人祸。
不过,马上就有人反驳道,魏征本为关东人士,如此言论多有偏颇,且关东今年并无太过严重的灾情,若是再免其一年的赋税,对其他地方岂是不公?
在一片争论声后,皇帝依然没有表态,反而转之向太子相询对此事的看法。
起初,所有人都没有太过在意,尽管他们敬服皇上的雄才大略,皇后的贤德仁厚,但对他们的儿子,尤其是一个处于懵懂之年又颇有些顽劣的八岁小儿大多是不以为然的。
乘乾恭谨地起身向父皇行过礼后,方才出言相对,“儿臣早前听说魏大人曾上过一道疏奏上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此也正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意,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现今关东地方官既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