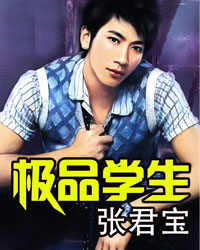女中学生三部曲-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曾惠夹起虾说:“不客气了!”她看着显得柔和忧郁的庄庆,心里又升起一种与其有种沟通的奇怪感觉。教导主任又告诉过她在广场墙上发现过金剑的图案还有女中的签名,广场的纠察老头说有人在广场打过架,是两伙小流氓,教导主任急得要命,恨得要死,曾惠觉得她是拼命忍着才没在自己面前说出“世风日下”的话。曾惠看着庄庆,不相信她会是不良少女。但是她们中午风风火火跑到哪儿去?不上画图课了,藏着黄色蜡笔干什么?然而,十七岁的女孩去打架干什么?这偏僻得差不多被废弃的广场既不影响交通也不会是要道。曾惠不得其解。
“你看见没,我的桌上有个金剑。”曾惠剥开虾皮,随意说了一句。
“看见。”庄庆说,大口往嘴里扒了口饭,两腮被饭撑得鼓起来。她看着曾惠。
“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是以前坐我们这桌子的人留下来的,我们这张桌子是上次全校大扫除从别的班拉来的。”
曾惠“哦”了一声,心里却明镜一般:果然是庄庆!教导主任早说过这学期开始就没大扫除过,而金剑的出现是这学期不久的事情,一个谎话。剑要刺谁?
“你怎么想起这个来了?我们桌上还有一个外国人像呢,也是用小刀刻的,还上了蜡笔彩。”庄庆说,把红烧肉上的肥肉颤巍巍地夹下来扔在桌上。
“我觉得好玩,我上课也喜欢无聊时候画画,全是画小人,从来没想到画剑这种东西。”曾惠说,甚至还微笑了一下,心里却鼓一样地敲。凭那句话,也许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破绽已经出来,剩下来的审讯可以让教导主任去做了。曾惠心里有点为庄庆凄然,眼看阴谋就要暴露。她突然心里又泛上来耻辱,她审度自己刚才的心情:也许所有的犹大,都有这种凄凄然?心里有自己十七岁的声音在说,多么卑鄙啊多么卑鄙啊。这心情像雨前的云一般扩大起来。“你喜欢佐罗吗?”庄庆突然问。
“喜欢。最喜欢他骑在马上遮着脸,用鞭子在墙上划乙字,啪啪啪!’曾惠用筷子比划着说,有半粒米饭从嘴里喷出,落在桌上。
庄庆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她这突然明媚的脸却狠狠抽了曾惠一鞭。曾惠感到有两个曾惠在身体里争吵,一个年轻,一个成熟,她并不知道,一个女人的每个不同年龄都是分裂开来的各自不同的人,互相也不能理解,互相憎恨。那个年轻的曾惠穿着永远的白衬衣向她暗示着她忘记了的秘密通道,能绕到这个阴谋后院,去看一眼后院裸露着的东西。一个成熟的曾惠怀着好不容易完成到新单位的第一件重要任务的欣喜,无以名状的惭愧和困惑不解。
离开餐厅回到寝室,推开门,迎面扑过来一股女孩子群集处的温馨暖洋洋的气味,这气味又一次提醒了曾惠。
庄庆拿出自己的小录音机,倒出英文带来用手轻轻拍拍听得很旧的盒带,说了句:“安息吧,阿门。”拿出同样一盒听得很旧的盒带插进去。寝室里响起了一个男人声音很厚很安静很孤寂的朗诵,音乐浪潮一样神秘而孤寂温柔地扑面而来,淹没了那男人的声音,鼓重重敲着。庄庆跟着渐渐升起的歌声轻声吟唱,她的变声期听来已经过去,声音又轻又紧,但有种深深的东西在这样的声音里汩汩流出。曾惠心里万分惊奇,她觉得十七岁这么个单瓣兰般的年龄不该唱这样的歌也不该这样唱歌。临睡前,曾惠问庄庆:“你不回家你妈妈不着急?”庄庆只是笑了一声,说可能她会过得更舒心一点,回家只是给她添乱。但庄庆心里知道母亲一定寂寞难耐,独自坐在电视机前。庄决心里有一点为母亲遗憾:大学英文系的六五届最好的学生,有学问,有风度,最后也没逃脱。庄庆想,如果没有父亲和自己,其实母亲是一天也过不下去的,她恨她中学教师的工作,她的人生只有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庄庆常在心里这样分析四周的大人,用她那个女孩单薄而犀利的眼光和纯洁热烈的心情。天完全阴下来,月光突然不见了,屋里一片漆黑,庄庆感到黑涌动着扑过来了,她挣扎不去央告曾惠开灯,把自己紧紧用被子包住,渐渐睡去。
庄庆觉得自己在一片昏暗的树林里徘徊不停,树林正在落叶,声音低而清脆,树林间仿佛擦绕着一阵阵淡紫或淡蓝的雾气,树枝看不清楚,地上有水连,水洼里放着蘑菇般的碎红砖,作为通往树林昏暗深处的小路。庄庆就在水洼旁徘徊着,隐隐约约还听见上铺曾惠翻身的声音,她感到自己就要做那个梦了。那是个平静无声的恶梦,每次自己走到这儿,就是要接着走进那恶梦里去。庄庆央告自己不要再往前走了,但脚步还是往前走去。
梦境变了。眼前出现了一大片波浪粼粼的湖水,倒映着湖岸上郁郁葱葱的林木,宁静得没有一丁点声音。突然,像听到了什么召唤,庄庆回过头来,看到灌木落叶如雨,从灌木丛中突然闪出一个穿古怪长袍的老妇人,满脸皱纹,脸很和善而意味深长。她手里古怪地捧着一个小孩玩的白色皮球,向庄庆微微露出笑意地走来。她的脚步飘浮一般。突然庄庆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巨大恐惧,转身就跑。但湖边全是沼泽,踩下去如踩在厚厚的棉花里,老妇人却慢慢地不能阻挡地通过来,手里的白皮球轻轻转动。庄庆挣扎着逃开老妇人伸过来的看样子温暖的手,手背上皮肤白而松弛,指甲是很可爱的粉红色。但庄庆从她身上感到一种没顶般的压迫。突然,庄庆发现老妇人没有了,湖那边有一只白色大鸟渐渐飞起,雪白的翅膀扑扇着,美丽异常,天蓝得要命,湖也变得蔚蓝,大鸟就在那儿,在蓝天蓝湖之间翅膀无比美丽地滑翔。大鸟越飞越近,越飞越近,翅膀扇起的风拂动了庄庆的头发,洒下来一种温暖和阳光照射的气味。眼看湖那边又有灰色的小鸟飞来,庄庆向湖边走了几步,这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灰色的石阶上,仿佛是一个楼房的废墟。灰鸟越飞越近。乌长着一张人脸,脸微笑着一晃而过,而翅膀上鲜血淋漓。庄庆心里充满了不祥而焦急以及某种预感,果然人脸转来一看,是宁歌的脸。宁歌遗像上的脸,拿眼深深地看她而不说话。庄庆觉得自己大叫一声,但却一点也没听见声音。宁歌看了看她,跌跌撞撞地飞到树林里。庄庆拔脚就追,但是走一段,就被灰色台阶绊一下,跌跌撞撞怎么也走不动,腿变得比铅还重,怎么也抬不起来。灰鸟转过脸去,非常失望非常孤独地飞进树的阴影里。
庄庆觉得有手掀开她的被子从她脸上滑过,她大叫一声睁开眼睛。寝室里亮着灯,曾惠打开了她的蚊帐,穿着件格子衬衣坐在她床边。曾惠半个脸让枕头压得红红的,惊异地看着她说:“你又做梦了吧,叫得好吓人噢!’
庄庆这才彻底从那熟悉的恶梦中醒过来,寝室的明亮灯光使她感到十分安慰。她看着曾惠,曾惠突然穿出这么件她从来没见她穿过的旧绒布衬衣,衣服又肥又大,敞着的领口露出了一截细细的脖子,她感到曾惠十分像宁歌的模样。
曾惠奇怪而关心地注视着庄庆,她开始感到除了金剑党,这女孩心中必还有一个秘密的王国,骚扰她,陶醉她。曾惠冷得打了个寒战,说:“你没事吧,我得关灯上床了,冷死了。”
庄庆连忙说没事了,一个恶梦。
曾惠重新关了灯,床吱吱嘎嘎摇了一通,曾惠说:“庄庆,你怎么老做梦?上次也叫得好吓人,还哭。”
庄庆仰面躺着,说:“我老做一个恶梦,高一开始就做这么一个恶梦。”
曾惠说:“我在一O一中的时候看过同学里面传着看的弗洛伊德的书,叫《释梦》。专分析梦的,我给你圆圆?”
庄庆惊喜地嚷了一声,她从高一就被这个怪梦所困扰。她一五一十地说湖,树林,大鸟和老妇人,说到老妇人满是皱纹的脸上呈现出来的表情,庄庆声音颤抖了一下,还有宁歌。
曾惠却是做梦都没想到这女孩有着这样一个忧伤和渴望,恐惧和美丽交融混杂的内心世界,弗洛伊德的工具在曾惠脑子里怎么也组织不起来,庄庆却静静地在下面等着她说话,庄庆怀着女孩子的虔诚心情一声不吭地等着。
“那老妇人,老妇人好像是和你生活很密切的一个年老的妇女。”曾惠迟迟疑疑地说。
“我妈妈!”庄庆却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叫起来,“我害怕我妈妈,她总轻视我喜欢的东西,她什么都不爱,也不爱我。她那样子好像全世界都欠了她东西没还。”
庄庆停了停,最后倾诉的心愿借着遮掩一切的夜色爆发出来,她说:“高一的时候,洛阳一个军事学院来招生,我从小喜欢当兵,想去参加现代战争,我满心想去,但我妈不让去,说我昏了头,放着上海的大学不上,到山沟子里去,将来连脑袋都保不住的营生,把别人的事业叫营生。硬去招兵的女军官那儿把我的名字划掉了。从那以后,我和妈妈的关系就变了,好像压迫和反压迫民族一样,第三世界崛起。”庄庆咕地笑了一声,她感到自己一下子说得太多,不知不觉就把心打开了。她惊慌起来,拼命回忆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这个年纪,想说和警觉、自尊永远在一颗心里战争着。
白色的夜雾在玻璃外变幻着。
被庄庆鼓舞起来,曾惠又说:“你好像老在找一种纯洁而且光明灿烂的完美的东西,但找不到,而且怀着堕落的恐惧。”
“这倒不是。”庄庆沉默了好一会儿,生硬地回答。
曾惠等了一会儿,庄庆在下面一直没有出声。她轻轻叫了一声,在庆含含混混地应了一声,曾惠也就不说话,但她睡意全无。窗玻璃上有水珠急急打来,下雨了。庄庆并没有睡着,她闭着眼睛听着夜雨,刚才她觉得自己的最后一层衣服被曾惠的话挑开来,突来的裸露使她惊讶而且恐惧。她觉得活着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数不过来的困难。但她总是在找,因为寻找和倾听,活着便越发艰难;因为没有人帮助,活着成长着也越发艰难。她不明白她在渴望着什么,那心在半夜梦醒后竟是这样不宁。
突然屋里一闪。亮得白昼一般,紧接着一声撕裂般的巨响响起,是春雷动了。这声巨响撕开了冬天和春天,震醒了冬眠的万物,大雨如注,闪电频频,一个个雷紧接着滚过来。寂静了整整一冬的耳朵猛地听到雷声,还茫茫然,紧接着,曾惠感到心里也有什么东西被震醒T。
春雷隆隆地响,万物都睁开眼睛。
第二次醒过来,是听到了急而愤怒的敲门声,敲在门玻璃上呼呼响。庄庆从被子里跳出来,问:“谁啊,谁?”
“庄庆,庄庆开门””
庄庆脸腾地红起来,对愣怔的曾惠说是我妈妈来了。庄庆一边应着,一边提过毛裤来穿上,收拾整齐了再去开门。曾惠坐起来,又躺下去,不知道该怎么办。庄庆的母亲站在门外,眼里最初的探究和焦急正在退去,恼怒火般地在她白净的,保养得很好但又显出凋败的脸上燃烧起来。她沉默地站在那儿,庄庆垂下头,扣着衣扣低声说:“进来呀。”
母亲轻而稳重地走进来,从包里拿出粉红的饭盒,打开,里面装着结了油的红烧鸭翅和排得整整齐齐的生煎馒头。瞥了一眼躺在上铺的曾惠,说:“这屋里人味真大,你们就这么星期天享福啊。你知道我怎么为你担心的吗?我在床上坐了一夜,你也十七岁了。”母亲的声音很脆很甜,宛如少女,但话里有一种被教养压迫了的愤怒。
庄庆低着头。
母亲的怒火被这沉默和不交流煽起来,她低着声音问:“你为什么不回家?”
庄庆轻声说:“要在学校做功课。”
“家里不能做吗?听英文有录音机,做功课有你单独的一间房,这儿到底有什么抓着你,男朋友?”母亲讥讽他短促地笑了一声。
庄庆脸喷红地猛抬起头来:“我没有男朋友,这点你是明白的。”
母亲在与庄庆四目相对的瞬间张煌地调开眼睛,抿抿薄而线条秀丽的嘴唇,继而强硬起来:“你为什么不回家产’
庄庆听到上铺曾惠轻轻的呼吸声,她被母亲逼迫得浑身燥热起来,被母亲当众责骂,特别听着母亲渐渐失去教养的约束,变得尖利起来的声音,庄庆感到羞愧难当。她调过头去看窗外,窗外经过一夜春雨,万物都清新而且蕴含勃勃生机,那风那阳光,像唱着歌跳着舞的孩子。从窗缝里挤进来清冽的空气和声音,那声音遥远遥远的,像满含着一时难以听清的含意。庄庆本来紧张羞愧的心里突然空旷起来,充满了一种倾听呼唤的企盼,她几乎忘记了妈妈满腹埋怨地盯着她。
母亲看见庄庆脸上又显出惯常的出神来,母亲懂得女儿那个反抗的不服管教的心已经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只是由于母亲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