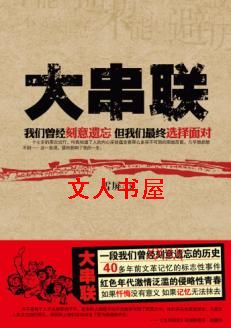死于青春-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我依然亲着你满是胡茬的脸膛,我多么惧怕多么憎恨多么理解你的愁眉不展。你竭力掩饰着两难的心境,携我去了东潮去了西郊游遍了晴川所有的公园名胜村野小景。为了能使你我双双返城,你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你指引着我小心地涉入了你的兄弟姐妹的社交圈,你不想让我孤独寂寞和这家庭格格不入。
那时期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已经告别过去,走向新生,心中既幸福又慌恐,因为新的生活圈子常常令我紧张拘束,而过去的一切,却不知为什么总在我心头索绕着一股淡淡的温暖和难舍的忧愁。
它总是使我忽然夜半梦醒,眼前浮出毛京紧锁的眉头。
还有我的女儿,我日思夜想的心头肉。
他也为我在一家服装厂领到了一张临时工的出入证。我们计划着在播种时节回山里去,告别乡亲,取回行李。
下第一场春雨的那天晚上,大康家的“政治沙龙”里挤满了兴致勃勃的时代青年,桌子上摆满了当时很不好买的啤酒和汽水,两个穿旧军服的青年如宠儿一样被众人簇拥着,高声谈论着他们在军队工作的父亲即将复出的消息。那时正值温都尔汗事件发生不久,几人弹冠相庆,凡人不堪回首。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把那个晚上的青年们弄得兴奋不已,我帮他们在厨房里操作,进进出出地拼凑着虽简单却不失知识分子调子的晚餐,并不去留意他们的高谈阔论。当我刚刚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摆放杯著的时候,一个迟来的客人忽然惊讶地唤我。
“刘敏作是刘敏吧?Y
是个女客。
我认出了原来是肖琳。
这是我回到晴;后碰到的第一个熟人,我本不想碰到任何熟人,{奇。书。网}和肖琳的邂逅使我忽地一下把本来希望永远遗忘的过去,过去的一切,都缀连起来了。
肖琳从餐桌后面绕过来,极惊喜地拉住我的手,大声叫着:“真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你怎么也来了?”
我惶然不知怎样回答。
“告诉你,几个月以前你猜我见到谁了,我见到毛京了!”
晴天霹雳,我瞪大眼睛,刹那间不知是悲是喜。
这时厨房里有人喊我,我下意识地退了一步,然后逃命般地向厨房奔去。
厨房里弥漫着热气,弥漫着一股极其压抑的湿闷。做饭的阿姨向我嘱咐了一句什么便端着菜出去了。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嘈杂枯燥的热气中,甚至没有察觉就流下了眼泪。肖琳默默地进来了,她默默地搂过我抖动的双肩,只有力量没有语言。我竭力把咸咸的泪水吞下,我不知道该不该再回首当年……
“我跟毛京说了,说你等着他呢,我告诉他你生了个漂亮的女孩儿,你和孩子都等着他呢。唉,毛京还是毛京
炉子上烧着一个砂锅,发出惨噬作响的焦糊味,肖琳帮我把砂锅端下来,放在地上,她吹着手说:“等吃完饭,我慢慢再跟你谈。”她说完用力楼了我一下,出去了。
毛京还活着,他已经知道了女儿的降生,这碎然而至的消息使我激动得几乎喊叫起来,又茫然不知该怎样选择,我失去了女儿,毛京会不会责备我?
那时我发疯似的想念我的毛京,恨不得立即与他重逢,哪怕九死十八难,也愿承当!但是突然回首,我惊惶地发现了大康堵在厨房门口的阴沉的身影。
大康冷冷地说道:“你哭什么,我为你做了一切,也没见你湿过一回眼睛。”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虚弱极了。
“女人?女人就是从撒谎开始的!’
大康凛冽如冰的目光表明了他已不肯饶恕,给人深深的恐怖。我带着绝望的战栗从他身边走过,我走出厨房走出这沉抑的湿闷,我穿过走廊里的安静和暗淡,穿过客厅里漫出的盛宴将即的嘻笑和灯火,大康没有喊我,他在我身后恶狠狠地沉默着。我满目泪水满腔凄凉,这时我吃惊地看到前方不远,一块紫色的天鹅绒门帘飘飘扬扬,上方亮着“太平门”三个红红的大字,而门外的休息厅里正弥散着薄纱一样的阳光,腰肌中我看见毛京修长的身影,雕塑般面对我默立凝望。我不顾一切地向外走去。我看到天尽头一片摇曳的白烨,白烨林边的餐厅在凄厉的夜雨中忽隐忽现,穿过雨幕我浑身发冷,迫切地扑向那温暖的石头房,不管房门已经破旧斑驳,但那斜出窗外的烟筒,却哈出淡淡的青烟,青烟游移在屋檐下依依恋恋,终被冬日的北风无情卷去。我小心地走进那熟悉的房子,我惊喜地发现屋里的书架依然干净,书架上排满雄文四卷等等等等政治书籍,雪白的墙上,依然挂着彩色的剧照,一个英姿勃勃的大春凝目远方,相片的旁边,依然是亮晶晶的弹簧拉力器,床上的锦缎被子依然如军营般方正整齐。一只猴子,端坐在老式留声机的“盖子上,见人进来便上前拉住你的手,孩子一样乖态可掬,不知是留声机里还是遥远的天外,总有人声轻轻吟唱:“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愿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爱人上战场。…”歌声回荡;。雾笼罩了一切。我眼前只剩下毛家集房东家暴露着橡木材秸的房顶,和抖动在房顶一角的暗淡的蛛网。我感到了分娩时撕肠裂肺的阵痛,我听到了自己因为孤独而绝望呻吟,我眼前飞快地飘过十八年缠绵不断的苦痛与梦想,我紧紧追随着那老太太和母亲一样颤巍巍的背影,期冀着梦境成真!那老态瞒珊的女人引我辗转向后台走去,我清晰地听到前面台上,歌声乍落,掌声即起,紧接着一片女孩子欢快的卿喳声自远而近。我看见我的女儿一身淡绿,随一群伴舞的少女翩然而来。
第八章
深秋。
清晨。
远山阴郁。
婉蜒跌岩的小路在沉沉的瘴气中若生若死,张弛如弓的山地在秋叶飘零中似醒似睡。几只麻雀从山门古庙的瓦檐下飞出飞入,瓦檐滴着清冷的露珠。
农舍半间,蓬扉微敞。青白色的阳光在门前阴暗的地上,投下一个长长的光影。
灶膛里的火苗刚刚燃起,小敏用力拉着风箱,火光在她青春早褪的脸上一闪一闪。她一声不响地往灶膛里填加柴草,像一个真正的山里姑娘那样妇熟麻利。
门前长长的光影一动不动。
小敏蒸上早饭,手脚不停地拌起猪食,准备着下地的工具。
门前惨白的阳光突然一暗,映出一个臃肿的人影。小敏墓然回首,吃惊地望着倚在门口的粗壮汉子,那人神态阴沉,四十岁模样,行囊简陋,脸很脏。
灶膛里余烬微红,陌生汉子把一根柴草伸进去燃起火苗,点起一根皱巴巴的纸烟。小敏收拾着桌上刚刚吃净的饭碗,探询的目光不时向灶前瞟来。
那汉子终于开口了:“你这儿可真不好找啊。”’
小敏焦急地:“毛京收到我的信了吗?他没让你带信来吗?”
“他去排哑炮,是个玩儿命的活儿,他自己要求去的,结果有个哑炮响了,当时我离他不到十米远,差点连我也玩儿进去。后来我们把他往医院送,在路上,唉,这小子太弱,在路上没熬住,就在我怀里咽气啦。”
小敏终于嘤嘤地哭出声来:“难道他不知道我在等着他吗!他不知道吗!”
那汉子无动于衷地看着门前那不知什么时候萎缩起来的光影,梦吧般喃喃自语着:“这小子,直到闭眼的时候才告诉我什他还有个老婆在外面呢,我们都不知道这小子这么大点就有老婆孩子了,他跟谁都没说过,连政府都不知道。所以他把这个秘密一说出来,他那眼泪珠子往下一滚,我们就知道这小子准是活不成啦,他准是知道自己没救啦。唉,可惜呢,他说他还没见过他那闺女哪。这小子的心眼儿挺不错,模样也挺招人。好人不长寿啊。我看出来了,他是真不想死,他是太想能活着出去,出去找他的老婆孩子,可错呀。”
毛京死了。
为了再看一眼毛京的足迹和遗物去寻找远在天边的采石场,我是在那个刑满释放的犯人带着噩耗的第二天启程上路的。那时天空中隐约飘着雨,雨渐渐沥沥带着咸味,不见太阳。
初冬的采石场看上去非常单调,单调得有几分荒凉。山脚下婉蜒着早已变成锈色的红砖围墙,围墙上盘桓着黑色的电网,青灰色的天空衬着青灰色的山岗,我几乎想象不出毛京那样一个多感而透明的性格,在这样刻板、肃杀的环境中,怎样了得。
这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管教干部们听到毛京这个名字时神情冷漠,由此我更加明白了毛京死时的孤独。他就那样孤独地无声无息地去了。没有遗物。
只是在我返程的时候,一个上了年岁的干部站在采石场空旷的路边,他衔着一只奇形怪状的烟斗,看着我从面前走过,长叹一声:
“忘了他吧,人死如灯灭啊。”
十几年过去,这声长叹一直在我心中留下经久不息的回响。我知道,一个青年来到世上,后来他不幸,后来他死了,后来人们把他遗忘,没有任何悼念,谈不上身后衰荣。这是个多么平常的故事,也许任何一个导演都不会满足于这故事的简单和原始,任何一个导演都要把这故事的主人公描绘得更完美更丰富更戏剧性,我满心以为他也喜欢了毛京,愿和我一同回顾,因此相聚与谋,其实他有他的看法和盘算,这些天倒是我一直在自作多情。
怪不得我常常觉出这个世界已经老了,在这世界上挣扎跋涉的人们已是风霜满面,尘垢满身,已经让虚伪、欺诈,贪欲和冷酷素得麻木。当这时我回想起毛京,我青年时的伙伴和恋人,想起他那天真明亮的双眼,他的纯洁无邪的灵魂,就禁不住感动得热泪迸流。
他是那样一个绝顶聪明、富于激情,又柔弱如水的青年,他跳舞跳得真浪漫。他多像歌德笔下的那位诗一样的少年,所不同的是少年维特由于爱的绝望而丧失了生活的力量,导致心灵的枯死和肉体的自灭,而毛京则把一线遥远的温暖看得那么迫切和重算他是带着对也没和未来的愿花购银牌椰风击白。
导演有四五天没露面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肖琳疲惫不堪地回来了,她带回一张四天后的火车票。我们挤在闷热的厨房里,我烧饭她替我摇着扇子,我说我知道北京火车票非常难搞,上次路过火车站还看见公安局约正在抓、“票员?..但肖琳似是另有心事,神色不属没有谈欲。晚饭的气氛也莫名其妙地有些沉闷,我看出她吞吞吐吐欲言不言食欲不振,于是笑问:
“想你爱人了?他什么时候回国?”
肖琳也笑笑,却笑得吃力而且无味,她放下手中的筷子,迟疑着说:
“今天,今天中午,孙导演请我到新侨饭店吃午饭……”
“啊,我说你现在怎么吃不下了呢。”
“他们制片厂的一位副厂长也去了。”
肖琳严肃的面孔使我紧张起来:“是不是,我的剧本不行?”
“呕——,差不多吧,孙导演是说了这个意思。”
“已经决定不用了吗?”
“用还是想争取用,但是得做较大改动。孙导演这几天已经着手帮你改了,他是希望你能同意……”
“他改了什么?如果要我同意的话,为什么不当面和我商量,而要请你去?”
“他要你同意由他和你一道担任这部片子的编剧。”
“什么?”我愣住了,刹那间似乎也明白了。
“当然,著名的排列上,还是你在前面。”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看来在今天的“工作午餐”上他们已经听起来几乎是别人对我的一种恩赐。我尽量克制着问:“那位副厂长呢,他是什么意见?”
即便我不问,肖琳也要说到制片厂的这位领导了,“副厂长说,孙导演在怎样提高剧本质量方面确实动了很多脑筋,不但和原作者多次商讨主题和情节的安排,4他说,名字还是原作者排先,稿酬怎么分配可以商量,钱是小事。孙导演的修改本这位副厂长已经看了,他觉得修改本融进了孙导演对生活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提炼,比你原来的剧本更丰满更成熟了,主题也更鲜明了,基本上已接近上马拍摄的水平。当然,他也说,你对孙导演署名如有意见,也可以提出来,甚至拒绝。但是孙导演在剧本上的艺术劳动用什么形式给予承认,厂里也要考虑,在没有考虑出方法以前,恐怕暂时不能列入拍片计划。”
“有意思,”我冷笑,“能把恐吓说得这么道貌岸然,也是一种水平。”
肖琳避开我的直视,“我觉得,我觉得,”她迟疑抬眼,“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我感到一种落水似的冰冷,我坚决地摇头:“不,我不同意他改,钱可以给他,但这个故事是我生命和青春的回忆,要改哪儿,得和我商量。”
“你不让他改,他就不拍,你怎么办?”
“我另找人拍。”
小敏,事情到这时候千万天真不得了,有了这个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