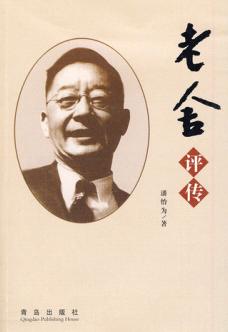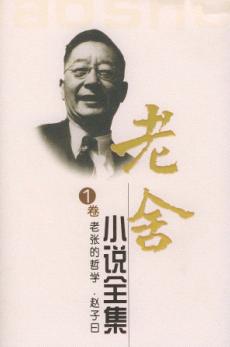怀念老舍-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当年就传出来一句话,这句话不胫而走,到了有心人耳朵里,牢记不忘。确实有过这么句话,老舍听了意见,说:
“那就配合不上了。”
老舍老在配合,配合婚姻法,配合选举代表,他是要宣传从“莫谈国事”到“参政议政”的。若照艺术家们说的写下去,配合什么呢?
现在看来,他那不少“配合上”的戏,都不能上演了,上演也没有观众了。偏偏这个“配合不上”的,还在舞台上放光采。这句“配合不上”的话当年为什么流传开来,为什么入耳还入脑,恐怕不单单是有些人敏感一些,对配合“具体的直接的临时的”政治任务,觉着有碍文艺的创造。那样的配合,其实是图解,图解会产生公式化概念化。说到图解,却又不简单。到了新时期;我们不去图解政策了,为什么还会去图解别的思潮、新来的观念,那也是一种配合。当前市场经济的浪潮起来了,文艺上努力配合的表现还少吗?“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提出来的问题,是这篇文章前后提到的这个那个之中,最有琢磨头的事。稍稍深入几步,就会碰着形象与观念,感性与理性,老舍自己当青年教授时候斥责过、当老年作家时候奉行过的文以载道,这些麻烦的原理能躲闪也好,只怕有躲闪不开的时候。
八十年代也匆匆过去了。九十年代之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五十年代上演《茶馆》的一代一台演员,在几十年磨炼中,都得到应得的表演艺术家的盛名。但也正如一句戏词上唱的:“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白了头。”他们大都退了休,有的已经不上舞台不上镜头多年。但是《茶馆》呢,他们抖擞精神,为《茶馆》来了个告别演出。多棒!
有没有新的一代一台《茶馆》演员?还没有亮相。当我们由本世纪走进新世纪的时候,《茶馆》会不会还是保留节目?会不会还照着老世纪的规范演出?老规范会不会还受新世纪欢迎?《茶馆》当年,只有北京人艺独家上演,会不会永远只有这一代的一台了?目前,我们只好“念天地之悠悠”吧!
——我们吃下午茶去!
百年老舍
文/柴福善
老舍,顾名思义,应是老屋。京城丰富胡同19号,很传统的一座三合小院儿。虽然才修葺一新,但修旧如旧,依然是老屋。主人于49年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以100匹布买下的。再前是准呢?早不得而知。这座老屋,风风雨雨,经历了百年沧桑,事有千般巧合,这座百年老舍,其主人名字,恰恰就叫老舍,而且诞辰百年。值此之际,将百年老舍辟为纪念馆,来纪念文学家老舍先生。
纪念馆没有特殊标志特殊建筑,不显山不露水地悄然隐于一片普通民居中。我来时天又下着雨,虽不暴,也让我好一阵踅摸,才踏进纪念馆门槛。展厅里展示着老舍的生平,也展示着他各种版本的著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享誉海内外。其中那本《出口成章》,为老舍生前最后编的一本书,是文学语言的论文集,有些观点、见解甚至是他一生写作经验的总结。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再版时买到的,当时,才走出农家小院,正在文学小路上蹒跚学步,有满腔热情,而不知如何下笔,渴望读书,又盲目的不知所读。在这茫然之时,我读了《出口成章》,简直如获至宝,一读再读,使我基本明白了怎样运用语言。说到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应该有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语言表现要写的东西,用自己的嘴去说自己的话,文学毕竟是生命的叙写与心灵的抒发。老舍主张,“句子短,用字活,”“写东西,写一句是一句”,“这一句到底说明什么,表现什么,我希望每句都站得住。”到现在我写文章,依然习惯于短句子,不能不说师于老舍。还有,要亲切,少用虚词,使文章更加精炼,气韵生动等等。书中,老舍多方面谈了文学修养问题。这本薄薄的小书,也许算不得作家的代表作,却值得初学写作者潜心一读的好书。作为语言大师,没有端着学问家的架子,而是献身说法,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现在,动辄就“高深理论”“时髦词语”的境况,这样普及读物似乎少有人作了。我深知,一个作家,艺术上的成功,恐怕最终要体现在语言上。而老舍书中的言,够我慢慢领悟一生了。
老舍非常喜爱花,也爱养花。他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因此,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再意,只要开花,对花他很有感情,看到一棵好花死了,会难过的流泪。所以,注定他无奇花异草,多是易活而不用精心管护的花。当然,不等于不管。不付出劳动,一棵花也不能养活。尤其他写作累了,把花鼓捣一番,便是极好的休息。每当秋天,他养上好多菊花,次第开放了,就热情邀请请朋友来,一同观赏,分享开放的喜悦。喜悦中,会把心爱的花拱手送人,毫不吝惜。其实,这一切都是老舍热爱生活的具体体现。在院内,他亲手栽下两棵柿树,一方水土下,一抹阳光里,已然枝繁叶茂,一嘟噜一嘟噜柿子,坠弯枝头。老画家于非闇曾为老舍绘“丹柿图”,并题语:“老舍家有菊花,见丹柿满树,亟图之。”清秋时节,地上菊花盛开,枝头柿子彤红,上下交相辉映,确是壮观,难怪触动了画家情怀。后来,老舍夫人胡青女士称这小院为“丹柿小院”,是否缘于此呢,仅是我揣测而已。
记得几年前我在平谷城街头,购得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由青年出版社印行,当是今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吧,标价人民币16,000元,1951年版。当时觉得版本有收藏价值,便随手买下了。回后发现盖有印章“舒”,刀工功力深厚,应是篆刻大家所刻,非是街头刻字者所为。下有签名“舒济”。仿佛老舍文章中写到过:在山东济南住了四载,有了第一个孩子,便起名为“济”。经联系,我终于见到舒济,原是老舍长女,现任老舍纪念馆馆长。她接过书,端祥半晌,说:“是我的,是我的。”当年风华正茂,而今已儿女成行,年过花甲,鬓角飞霜了。使我不解的,即是老舍家中之物,怎会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流落京郊街头呢?或许“文革”浩劫中散失,这多年来,不知又转了几人之手,最终总算物归原主,且保存完好,也算一桩奇迹了。细想那“舒”字,何尝不是老舍的名字?他曾在给别人的信中写到:“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姓。以姓作名,舒字拆开来,是舍予,意思是‘无我’。我很为自己的姓名骄傲,从姓到名,从头到脚,我把自个儿全贡献出去。关键是一个舒字,舍什么,舍的是‘予’。我写书用的笔名老舍,也是保留一个‘舍’字,不是老‘予’。以姓为名,以名构成姓,都是围绕这个意思,这是我一辈子的信念。”其实,老舍的一生,就是舍掉自我的一生。无论抗日战争中,他舍掉自己的小家,参加抗战工作,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是新中国成立,舍掉国外的优裕生活,参加新中国建设;直至最后,面对造反派的污辱,为维护人格尊严,毅然投身太平湖,舍掉了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的诺言:“我至死守着这个‘舍’字,我的名字象我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了正义,为了真理,老舍终归是老舍,而家人继续着他的诺言,把这座小院及老舍遗物一并捐献给国家,才有了这座纪念馆,我才能今天站在这座小院里,向大师致意。雨依然在下,屋檐淌下一排晶亮亮的水帘。我想,对于小院,是百年老舍,一道凝帝的风景,将永远屹立于北京街头;对于作家,是老舍百年,以其人格以其作品,将永远镌刻于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心头……
老舍的“俗”与“白”
文/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老舍最初是抱“写着玩玩”的心态写起小说来的,那时,他还“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只好“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特别是人物描写上,有明显漫画化的趋向。这在他最早的三个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中,多有体征。不过,若撇开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不谈,单论以纯熟的京白写小说,老舍1925年在伦敦写的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几乎就是上世纪20年代最好的北京口语教本了。直到今天,那些纯粹却略有失纯净高贵的京腔韵致,依然会从许多老北京人的嘴里不经意地飘出来。
我想可以说,老舍以书面的形式提纯了许多北京人口语的日常表达,而北京人许多约定俗成的大白话又一经老舍的点拨,也变得有了文化。如果细分,正像老舍的文学与北京的文学是有区别的一样,老舍文学的北京口语,与北京的老舍文学之外的口语是有区别的。老舍的特色绝不仅仅在于他的“京味儿”,他的文学包含了“京味儿”,而“京味儿”却远不能涵盖他的文学。
也许是因为老舍前期创作在语言上过分强调了保持生活化口语的原汁原味,而使一些批评家在几十年之后仍觉得他是贪呈口舌之快,难免显出北京人特有的“贫嘴”,相对缺乏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风的严谨讲究。其实老舍从一开始就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写《老张的哲学》时,因明显感到“以文字耍俏本来是最容易流于耍贫嘴的。”到写《赵子曰》时,便有意力图使文字变得“挺拔利落”。无疑他是有意识地尝试用“顶俗浅白的字”造出“物境之美”,“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作为艺术家,他追求的是“用最简练有力的词句道出最高的思想和最复杂的感情。”
也就是说,老舍在“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作言语!”“我还始终保持我的‘俗’与‘白’”的同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蕴藉在人物灵魂深处和潜隐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剥去了故事的外壳之后便所剩无己,它就是一副没有骨肉的空架子,其价值便只在用故事去填充世俗的情趣时空,是没有艺术灵魂的;而倘若它有一个宏大而坚实的内核,并闪耀着壮阔而高贵的思想精神光芒,它就会有着永久的艺术生命力。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不朽。老舍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看作是用文字构筑的全景展现北京人情市井、世俗风物与历史文化的俗白的“清明上河图”,既是艺术的集大成,更是人文思想的剖面图。
老舍几乎是中国现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好看,在有限的篇幅里,用幽默激活讽喻,用诙谐撩拨鞭挞,用人物和故事穿透时代和历史,超越了纯粹“京味”与“满族情结”的精神文化意蕴。
老舍的不解佛缘
一
从时间上来说,佛教是诸宗教中最早撞击老舍心灵的;从交往的程度上来说,老舍与佛教的关系似乎也更为密切一些。然而,当老舍刚刚开始接触佛教时,却是被动的,不自觉的。换句话说,老舍是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中,最早与佛教结缘的。
当探讨老舍所受到的佛教影响时,联想到的第一个人,毫无疑问的便是“宗月大师”了。
关于“宗月大师”的情况,目前掌握的较少。只知道他姓刘,名德绪,字寿绵,是西城粤海刘家的独生子。粤海刘家是内务府人,因祖上曾在广东负责过海外贸易,所以冠以“粤海”二字。刘寿绵家产万贯,好善乐施。1925年出家当和尚,拜当时北京西四广济寺的住持现明和尚为师,法名“宗月”。后来,“宗月大师”本人也曾经做过北京鹫峰寺的住持。
老舍小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就读的机会,完全是由于“宗月大师”信佛向善的结果。就老舍当时的家庭条件来说,是根本上不起学的。他的上学,完全得力于“宗月大师”乐于助人的鼎力帮助。老舍在回忆中曾经这样谈到“宗月大师”送他入学的情况: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