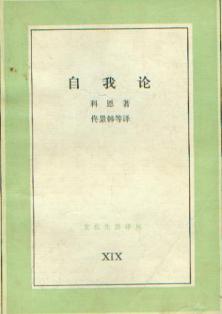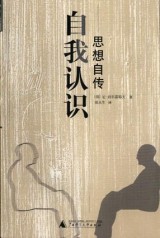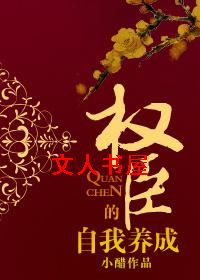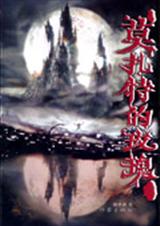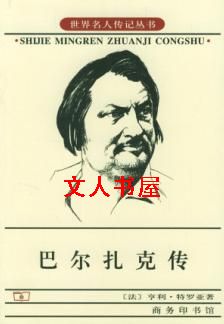自我的挣扎-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然病患的发展并非一定是如此趋于极端,但每一心理症患者(纵使表面上他被视为正常人),当他自己发生错觉时,也不愿用实证来加以禁制。他之所以会这样,乃因他若对此加以制止的话,他就会宣告崩溃。每个人对于外在的律法与规章所反应的态度,彼此均有不同,但他总易于否定自我所立的律法,拒绝了解心灵问题的原因与效应的必然性,或者,拒绝探测某些相辅相承的因素彼此间之必然性。
他有无穷的方法,用来不理会那些他不愿知道的事实。他忘记,因为它是无关紧要的,它是意外,它是由环境所造成的;或是因为别人激怒了他而造成的。他爱莫能助,因为它是“必然的”。我不曾看过如同哈维所说的:“我与现实奋战二十年,终于克服了它”,那种公然反抗现实而未能使之感动的人。或者,再引用一句病人的老话:“要不是现实,我将是完全公正的。”
荣誉的探求与正常人的奋斗间,其差异仍旧是清晰而显著的。表面上他们看来是如此的相像,以致其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看来好象心理症患者只是较具雄心,比正常人较关心权势、威望与事功;一若其道德标准较常人为高、为坚固;一若其比较自夸,或以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罢了。但事实上,有那个人敢截然的划出界线而说:“这就是正常人的终点,却是心理症患者的起点”呢?
在正常的奋斗与心理症的驱力间有其相似之处,因为这些相似处在特殊的人类潜能中有其共同的根源。人类经由智能的使用而有了超越自我的能力,与动物相较,他能想像与计划。在很多方面,他能渐渐地扩展自己的能力,且如历史所示,人类已具有如此的表现;对个人的生活而言,这种说法是真确的。对于他所过的生活,他所能发展的品德与能力,他所能创造的的东西,并无固定的界限。考虑了这些事实后,人类并无法确定他的界限,因此易于将目标立得过高或过低,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事。这种现存的不定性正是“探求荣誉”之所以能发展的必要基础。
正常的奋斗与追求荣誉的心理症驱力,其差别主要乃在于推动他们的力量彼此不同。正常的奋斗起源于人类天性的习性,而用以发展天赋的潜能。“相信天生的成长冲动”已成为我们理论上与治疗上所依赖的信条了【在介绍《我们的内在冲突》时,我曾说过:“我个人相信人类具有发展潜能(protentialities)的能力与欲望……。”同时请参考Kurt Goldstein所著“人性”(Human Nature)一书(1940年哈佛大学印行)。但Goldstein并没有区分“实现自我”(self…realization)与“实现理想化的自我”之差异,此种差异对人类而言是重要的。】。尽管更新的经验会再三出现,但此种信仰仍是历久不衰的;唯一的改变在于利用更详明的系统来说明比种信条。现在我坚决地认为(诚如本书首页所述):“真我的活力”驱策个人迈向“自我理想化”。
另一方面,荣誉的探求乃源自“为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需要”,这点差异乃是根本上的,因为所有其他的差异都是由此衍生而来,因为“自我理想化”本身就是心理症的解决方法,而且具有强迫性,所以一切由它而生的驱力也是一种强迫性的需求;因为只要心理症患者必须依附于他的错觉时,他就无法了解“有限性”(能力的限度),所以荣誉的探求将会陷于“无限”的追求中;由于主要的目标在于荣誉之获得,所以他对学习过程、做事过程或“按步就班”便不感到兴趣──且具有轻蔑这些过程的倾向。他不想爬山,但却想矗立于山峰之上,因此他不懂进化或成长的意义,尽管他也会谈及它们。因为创造理想化的自我,最后只有牺牲“真我”方为可能,所以实现理想化的自我,需要进一步地扭曲事实,同时也需要“想像”的作用(想像乃是为达实现理想自我的最忠实臣仆)。因此,在人性发展的过程中,他多少会失去对事实的兴趣与关怀,也会失去分辨真伪的知觉──就其他方面而言,这乃是一种损失,这正说明了他之难以区别存在于他自己或别人间的真实情感、信仰、奋斗以及类似这类情感的“膺品”(潜意识的伪装)。同时强调的重点也从“实质”转移到“外表”。
于是,在探求荣誉的过程中,正常的奋斗与心理症的驱力二者间的差异,乃在于一为“自发性”,一为“强迫性”;一为承认有限,一为否定有限;一为专注于荣誉的最终结果的幻想,一为进化的感觉;一为外表,一为实质;一为幻想,一为真实。由上述的比较可知正常人和心理症患者之间的差异,前者不可能专心一意地去实现真我,后者不可能完全被驱策而去实现理想的自我。心理症患者亦具有“实现自我”的倾向;如果心理症患者不曾具有此种奋斗倾向,那在治疗上对于病人的人性发展,我们将变得束手无策。然而,虽然正常人与心理症患者在这方面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但真实的奋斗与强迫性的驱力(表面上固有其相似处)间却具有质(特性)上的差异。【本书中,当我提及“心理症患者”时,我就是指那些“心理症的驱力”(neurotic drives)战胜了“正常的奋斗”(healthy strivings)者而言。】
我认为因追求荣誉所引起的心理症过程,其最恰当的象征,就是“魔鬼协定”此一故事中观念化的内容。魔鬼或其他邪恶的化身藉着给予无限的权势,而引诱被精神或物质烦恼所困的人,但这种人只有当他出卖自己的灵魂,或下了地狱时,方能获得这些权势。此种诱惑力可发生于精神内涵富有或贫乏的任何人身上,因为它代表了两种权力愿望:对“无限”之渴望会引申出便于脱离烦恼的法子。根据宗教的圣传,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佛陀与基督就曾经验过此种诱惑,但他们“自我”的根基甚稳,认出那乃是一种诱惑,此种诱惑是能够加以弃绝的。此外,在与魔鬼的协定上所约定的条件,便恰当地表示出在心理症发展中所该偿付的代价;就这些象征性的词语而言,通向无限的荣誉的捷径势必也通往“自卑”与“自苦”的心狱。个人如果真循此径出发,最后他必会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他的真我。
第二章 心理症的要求
理想的幻像与有限的“实我”之间永远存在偌大的差距,心理症患者惧于面对此种差距,而潜意识地向世人提出了要求,在“想像”中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且具有不劳而获的优越权,于是将一切责任推卸于他人;然而,建立于自己意念中的一切要求,却导致了有关生活方面的许多惰性……而使他们生活于虚构的世界中。
心理症患者在荣誉的探求中,迷失在幻想的、无限的与无边的机遇王国里。显然地,外表上他可能会过着像他家人或社区中人们的一般正常生活、工作并参与消遣活动。他并不了解自己正生活在两个世界中(至少不了解它的程度)──隐秘的私生活与公共的生活。这两种生活是无法协调的;再重复前章所引用病人的话:“生活是可怕的,满布现实!”
无论心理症患者多么不愿意面对现实来反省自己,“现实”却已把他强分为二;他也许很有天分,但本质上仍像其他人──除具有一般人的缺陷之外,还具有很多个人所须遭遇的困难。他的实际情况无法与他如神的想像一致,外在的现实也不曾将他当神般地看待。对他而言,一小时只不过是六十分钟而已;他必须像其他人一样排队等着;计程车司机或老板也待他一若常人。
个人感觉所受的轻蔑,可以很适当地用病人于孩提时代所能忆起的小事故来做为象征。有个三岁的女孩,当一位老伯伯学着她,而打趣地说“唉呀!你的脸真胖!”时,她曾幻想着成为一位美丽的女王。她永远忘不了因自己的无能所感受到的愤怒。像这种人便几乎会会时常面对矛盾、困惑与痛苦。他做什么呢?他如何去说明它们呢?如果反应?或如何除掉它们?如果他个人觉得加强自己的权力乃是绝对必要,却又苦于无此能力时,那他只会推说这个世界乃是有毛病的,它应该是不同的;因此,他并不解决自己的错觉,反而向外在世界提出了一种要求,他有权利按照他自己的崇高意念,使他或他的命运获得另眼看待。每一个人应该迎合他的错觉(要不然,他就会觉得一切都是不公平的),他有权利享受更好的待遇。
心理症患者感到自己有此权利去享受他人特别的照顾、体恤与尊重。有关“敬重”的需求是相当广泛的,而且有时表现得相当明显。但他们只是那种更广泛要求中的主要部分──即所有因禁忌、恐惧、冲突及解决法而产生的需求,都应该得到满足或适当地为人所敬重。此外,无论他感觉怎样,思考什么、或做什么都不应有不利的结果。实际上,这意味着精神法则所不该应用于他身上的一种要求,因此,他不需去改变他的困难,继之,解决他的问题不再是他的责任,而别人则应该了解这些困难并不会使他感到困扰。
德国精神分析学Harald Schultz…Hencke,是现代分析家中第一位发觉这些心理症患者所怀藏的要求,他称此为“巨大的要求”,且认为它在心理症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当我熟思他所提出的有关这些要求的重要性意见时,我的观念在很多方面与他有所不同。我认为“巨大的要求”这术语并不适当。它易使人误解,因为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在内容上是过度的。的确,在很多例子里他们不只是“过度的”,而且是纯属于“幻想的”;然而,在其他的例子里却显得相当合理。于是曾将焦点集中于“要求”内容的过分这一点上,而忽略了辨别那些存于自我以及他人中看来似乎合理的要求。
举个例说,有个商人因为火车不按他方便的时刻开车而感到十分愤慨。但一个知道在得失攸关之际事事都不应过分介意的朋友,就会指出对此他实在是太苛求了,这位商人也会报以愤怒之语,认为这位朋友并不了解他所谈的内容;他是个忙人,希望火车能在可预知的时间开,对他而言这无宁是合理的。
他的愿望确实是合理的,有谁不希望火车按方便自己的计划时刻来开车呢?但事实上,我们没有权利去左右它。这使我们认识到一种现象的要素:一种本质上相相当可理解的愿望或需要,转变为一种要求,此“要求”如不应该,就会使他觉得这乃是一种不顺利的挫折或攻击(因此,我们有权利对此发怒)。
需要与要求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不过,若心灵所隐伏的情绪已改变其状态,则心理症患者非但不知其差异所在,而且会对此加以逃避。虽然他实际上是在希冀某一要求,但他所谈及的,却可能是一项可被了解的或平常的愿望;他觉得他有权享受那些(靠明确的思想能够告诉他)不一定是属于他的东西。譬如,有些病人为了停车需买票,而勃然大怒,当然仔细一想,这种想“通过”的愿望是可理解的,但事实上他们却无权免费通过。有这种想法并非指他们不懂法律,而是因为他们争论者:既然别人能够通过,何以他就不行,这乃是不公平的。
心理症的要求完全是由心理症的“需要”演变而成的,它们是无理的,因为它们假定了一项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权利或资格。换言之,把它们当作是种要求而不单是心理症的需要,这种看法是过度需求的特别内容,据特殊心理症的需要,而有细节上的不同。一般而言,病人会感到有权去得到任何对他而言是重要的事物──即所有特别心理症需要的满足。
当我们谈及一位富有需求的人,我们通常会考虑他对别人的需求。人性关系的确是构成心理症要求的主因。如果我们如此限制他们,那我们就太低估要求的范围了,他们正被导向人为的风俗,甚至于超越此而达于生活本身。
就人性关系而言,一个行为显得相当胆怯与退却的病人,内心可能会提出一种全面的要求。因为他对此种要求并没有澈底的了解,所以他便为普遍的惰性及无法开发自己的机智所困扰了,他说:“这世界该帮助我的,我不该被困扰。”
一个根本就惧怕怀疑自己的女人,会具有如上同样广泛的要求,他觉得她有权利去满足自己所有的需要。“那是极其不可能的”她说,“我所希望爱我的男人,会不爱我?!”她的要求可以说是起源于宗教的术语:“每一件我所祈求的东西都会得到。”就她的情况而言,其要求具有相反的一面。因为若愿望无法满足,那么这将是不可思议的失败,所以她制止了大部分的愿望,以避免承受“失败”
![[HP]我是扎比尼夫人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2/299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