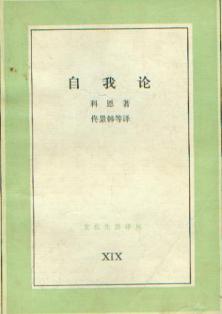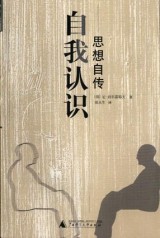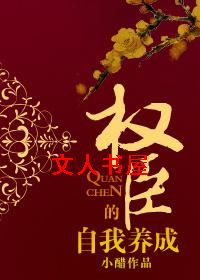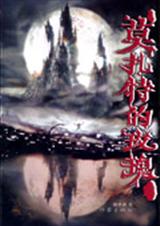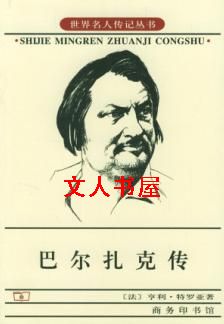自我的挣扎-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做的、或应该做的实况或可能的情况。它成为一种用以判断本身的“知觉”以及用来测定自己的测量棒。
站在不同的观点,我主张称“自我理想化”为“广泛的心理症解决法”──不只用以解决个人的冲突,而且可以满足在某一特定时候所发生的内在需要。此外,它不但可以摆脱痛苦与不堪忍受的情感(感到失落、焦虑、卑下及分裂),而且还可使他获得他本身或生活上的惊人成就。无庸置异,在他发现了这种解决法后,为了他可贵的生命,他会去坚守它的;同时,用适当的精神医学名词来说,它会造成一种“强迫性”【当我们对于此种解决法的过程做更进一步的了解后,我再讨论“强迫性”(pulsiveness)的真义】。在心理症中,“自我理想化”之经常出现,乃是由于在易于造成心理症的环境中所养成的“强迫性需要”,经常出现的结果。
我们可以经由“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点,来探讨早期人格发展的合理(必然)结果,与未来发展的起始。它对未来的发展必定会具有深运的影响,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步骤,没有一步比“舍弃真我”更合逻辑。其“革命性的效果”主要是由于“实现自我”的精力被转移到实践“理想自我”之上所致。此种转移正是整个个人生活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改变。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对人格具有“塑造力”的转移方式。其作用在于避免“自我理想化”始终停留于“内在的指使”,而使其能溶于个人的生活圈中。果能如此,则个人会希望──或被驱策──去表达自我;亦即希望表达理想化的自我,并用行动在加以证实。它突破了他的渴望、他的目标、他的生活行为以及他与别人的关系。基于此一理由,“自我理想化”必定会产生一种更为广泛的驱力,我拟用一个较适合其性质与范畴的名称来为它命名,即是探求荣誉(search fro glory)。“自我理想化”依旧为其核心,其作的组成元素,虽然因人而有其强度与知觉上的差异,但多少总是存在的;那就是为求完美的需求、心理症的雄心以及报复胜利的需求。
在为求实现“理想自我”的驱力中,“需要完美”乃是最根本的;它的目的在于将整个人格塑造成理想的自我。就像萧伯纳作品中的匹格玛琳【匹格玛琳为希腊雕刻家,与他所刻的雕像发生了恋情,于是后人逐称病人与自造的物体热恋为pygmalion】,心理症患者不只企图修饰自己,而且还要将自己改造成理想形象中的完人;他藉着一种复杂的“应该与禁忌系统”,而力图达成此一目的。因为这种过程既重要又复杂,所以留在本书第三章再加以评论。
“探求荣誉”其组成元素中,最明显的是“心理症的雄心”,这是一种追求外在成就的驱力。此种追求“现实的优越表现”的驱力颇具普遍性,它还遍及于追求任何事情的优异表现,但通常它常有力地被应用于那些在特定时间下,易于表现优越的事情上。因此,这种雄心其内容在一生中是多变的。譬如,在学校里,有人会觉得在班上拿不到最高分,乃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慢慢地,他会情不自禁地与最种爱的女孩多次地约会,然后,也许会为了赚更多的钱或想要显名政界而感到困扰,这些变化便甚易产生“自欺”的现象。一个在某一时期曾决心做个体育健将或战地英雄的人,在另一时期可能又决心做个最伟大的圣人,然后他可能会相信他已“失去”了雄心,或者,他会觉得在运动场上或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并非他“真正”想要的。他不知道自己依旧驾乘着“雄心之舟”,只是改了航程而已。当然,个人必须详细地分析在某一特定时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改变了航程。我之所以强调这些变化,是因为由此看出了一项事实──受雄心掌握的人们,往往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漠不相关,而只注意到“优异”本身。如果无法认识这种“不相关性”,则许多变化将会变得令人无法理解。
为了这项讨论的目的,特别的“雄心”所垂涎的特殊活动范围是较少引人注意的。而其特征乃在于自己是不是众人的领导者,最出色的健谈者,拥有音乐家或探险家的美誉,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是否为名作家或是最擅长穿著者这类的问题。然而雄心的目的为何,系根据个人所渴望的成就种类而异。简而言之,它可能是在于增加权力(管理权、次于王权之权、势力或操纵力),或是增加威望(名誉、赞赏,声望或崇拜与专宠)。
这些“雄心的驱力”,比较上来说,乃是夸张性驱力中最为实际的;至少由下述意义而言,此说乃是正确的:于此有关的人们会将他们的实力投注在“优越感”的终极目的上。而这些驱力似乎也来得较为实际,因为很幸运的,拥有此种驱力的人们,都能确实地获得所渴求的魅力、名誉与势力。然而另一方面,当他们得到了更多的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后,他们就会开始觉得此种徒劳追求所带来的整个震击力。他们变得无法确保心灵上的平静,内心的安全感,或生活的情趣。为了补救他对“荣誉幻想”的追求,于是内在的压力仍如往昔一般笼罩着他。这些并非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意外”结果,而是必然的趋向;或许可以较为正确地说,对“成功”的一切追求乃是全属虚幻不实的。
由于我们系生长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所以上述的评论听来有点格格不入。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很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应凌驾于他人之上,而且精益求精,改善自己,所以我们会觉得这种倾向乃是“天性”。然而,在竞争的传统习俗下,所引起的对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事实上,并未减少人们的心理症特质;甚至于在竞争的环境 下,其他的价值观──特别是成熟的价值观──就大多数人而言,仍比与他人竞争的卓越感还来得重要。
“探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元素,远比其他元素更具破坏性,那就是为得到“服复的胜利”的驱力。它也许和追求“实际的成就与功名”的驱力具有密切的关系;如此,则其目的必在于使人蒙羞或藉着给人事功而征服或战胜他人;或藉着达到卓越的地位以获取权力,或将快乐建筑在那些受辱者的痛苦上。另一方面,为求优越的驱力,也许会归于幻想,而且这种“报复的胜利”的需求也会自然地表现于人际关系上,而产生使人降服,挫折、智取或打败他人的这些不可遏抑的冲动。我称此种驱力为“报复性的驱力”,即因此种驱力乃是为了要洗雪孩提时期的耻辱,所采取的报复冲动而来──此一冲动在晚期“心理症的发展”中更为明显地增强。这种晚期的增强,可能系为使“服复的胜利”的需求变为追求荣誉的因素而发生的;此种驱力的强度,以及人们对它的“知觉”其间差异甚大。大多数人只在短期内知道或认识此种需求;它有时会公然出现,但后来却变为隐含于生活中的主动动机。近代史上的希特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他曾经有过耻辱的经验,因此他幻想着将生命专注于打败人群这一点上。在这例子里,那种不断在增加需求的恶性循坏是易于为吾人所了解的,其中一种恶性循环乃因他只注意到“胜利”与“失败”而发展出来的。由于对失败发生了恐惧,遂使他决心在下次非获得胜利不可,而每次的胜利都会增加他的伟大狂傲,此种狂傲感又使他更无法忍受那些不赏识他伟大的任何人或国家。
还有许多与此略同的病症或故事,现在我们单从现代作品中举出一例。有一本书名叫《注视火车过去的人》。故事中有个正直的伙什,困服于家庭生活与办公室里。很明显的,他除了尽责之外不思他念,有一天,当他发现了老板利用欺诈的手段导致公司破产的事后,他的价值尺度便猛然崩溃了。那些拥有一切的在上者与像他那样只有正当行为的窄径可行的下位者间的区别,因此粉碎了。他知道他同样可以变得“伟大”与“自由”。他也能够拥有一位女主人,甚至于是老板那迷人的太太。此时,他的自负已变得如此夸张,以致于当他亲近她而受到拒绝时,他遂扼杀了她。后来当警察极力要逮捕他时,虽然有时他会感到一阵害怕,但他的主要动机却在于胜利地击败了警察,甚至对于他之企图自杀而言,这仍是一种主要的激发力。
这种“胜利的报复”之驱力常常是隐藏在暗处的,实际上,由于它本身所拥有的破坏性,它在荣誉的探求中乃是最为隐密的,或许只在相当“疯狂的雄心”中才会变得明显一些。在分析中,我们就能发觉得到些种驱力乃是欲藉着凌驾他人以求打败或侮辱他人的一种需求。对于“优越”较无害的需求,乃是能够除去更具破坏性的“强迫性”,这样可允许人们按其需求而行,而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乃是正常的。
了解个人“追求荣誉”倾向的特点,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是必须予以仔细分析的一群特别集合体。但我们无法了解这些倾向的性质与震击力,除非将其视为“连贯实体”中的一部分。阿德勒是第一位将它视为“可理解的现象”的精神分析学家,并且指出它在心理症中的重要意义。【请参考本书第十五章阿德勒与弗洛伊德观念的比较】
对于荣誉的探求乃是一种“可理解的”与“连贯的实体”,此一说法,已有各种不同的实证。第一步,举凡上述的多种个人倾向,通常会同时发生于一个人身上。当然,其中某一种元素也许会较占优势,致使我们说他是一个有雄心的人或梦想者,而这种说法并不够精确。但这并非意味着其中某一元素的突出就表示另一元素的缺乏,此种具有雄心的人也必有他自我的崇高形象,而梦想者也会希求实际的霸权;尽管后者也许只有当自己的自负为别人的事功【因为个人的人格或个性,看来常与较占优势的倾向(prevailing trend)不相一致,所以大多数人甚易将这些倾向视为独立的实体。弗洛伊德将与此略同的现象视为分立的“本能驱力”(instinctual drives),此种驱力具有个别的来源与特性。当我首次试图列举出心理症中的“强迫性驱力”时,我同样以为这些驱力是种分立的“心理症倾向”。】所冒犯时才显得明朗化。
此外,所有涉及到此一问题的个人倾向,彼此间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因此,那种较占优势的倾向在各人一生中常会有所改变,他会将迷人的白日梦转变成为一个完美的创始者或主人,然后,再变成永恒的最伟大爱人。
最后,那些倾向具有两种共同的特性,经由整个现象的发生与作用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特性;经即“强迫性”与“幻想性”。此二者吾人在上面都已提过,但更完全而简明地加以阐述仍是有必要的。
此种“强迫性”乃是起源于“自我理想化”(整个荣誉的探求过程即为比种发展的结果),这是一种“心理症的解决法”。我们所以名其为“强迫性”的驱力,乃意味着它违反了自然的愿望与奋斗,后者乃是“真我”的表现;而前者则为心理症结构的内在需要。个人必会不顾真实的愿望、情感或兴趣而固守着它们,以免陷于焦虑中,或是被冲突所伤害,为罪恶感所击溃,抑或感到为人所拒绝……等等。换言之,“自然的”与“强迫的”二者间之区别乃在于“我想要……”与为了“为了免于危险,我必须要……”之差异。虽然个人可以意识地觉察出他所“想要”达到的那些雄心与“完美的标准”,但事实上他却是“被驱策”地去得到它们。“荣誉的需求”使他陷入它的掌握中;因为他本身并不知道“想要”与“被驱策”间的差异,所以吾人便需要在二者间建立一个区别的标准。其中最明确者乃是──他全然不顾自己及自己的兴趣而被驱策去求取荣誉。(我记得有某一个例子。有个十岁的女孩,她宁可用功到眼睛都弄瞎了,也不顾失掉在班中独占鳌头的头衔)我们有理由知道,是否有更多的人生──真实地或假借地──是为了其他的理由而不为求荣誉而牺牲的。约翰·加百利·勃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当他开始怀疑他达成天赋的确实性及可能性而去逝时,有一真实的“悲剧元素”参与了这幕情节。如果我们能为自己以及大多数正常人所肯定的的人类价值而牺牲自己,这虽为悲剧,但却是极具意义的,若我们连自己都不知其所以然地沉滋于荣誉的幻想中,且耗损了我们的生命,那将是一种悲惨的浪费──生命所蕴涵的价值愈高,则此种浪费便愈大。
追求荣誉的驱力之强迫性,其另一标准──一如其他强迫性的驱力──为“不辨善恶”。
![[HP]我是扎比尼夫人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2/299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