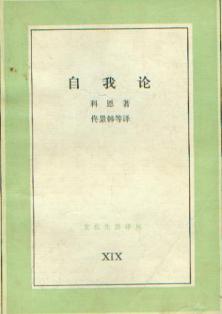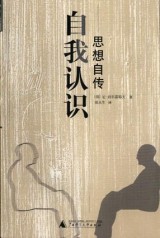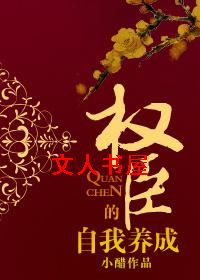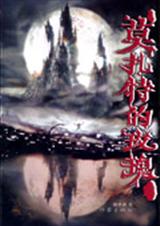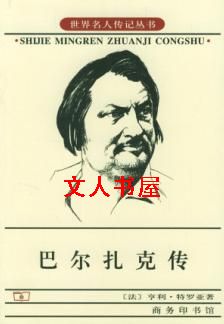���ҵ�����-��1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ұ鼰����������Ļ����Ȼ��Щ���̿����ƺ�����ͬ�ģ�������֮����������Ҫ�IJ������ڣ��⼴�ǣ�����֢���������������أ�����������Լ��������е�һ���ӣ�û������ġ������С�����ֻ���������������Լ���������
��Ȼһ���˻�����Ϊ���������������ľ���������Ȼ������Ŀ����������������������ͨ���Ⲣ��������ر���Ϊ�Ǹ��ñ������������ϰ����⣬��������Ϊ�������ü����ձ飬ͬʱҲ��Ϊ�������Ϳ���һ�ִ�ͳ����ʽ���������ڷ����߱���Ҳ�����ڴ˲����¡�����һ�ּ�������ʱ�����ڿ��Ի���һ���ˣ���Ϊ��ʹ�˱��һ��Ͷ���ߣ�����ƻ��˸��˵������ԡ��������������ģ��෴�أ�������һ�����ص��ϰ�����ʵ�ϣ���ֻ�ᷢ������Щ�����Ҽ�����Զ�������Ը��㷺���ֵ��������ϡ�
���⣬����֢���Ը�ɢ���ڸ������������������еġ����ԡ��ϣ��Լ�������Щ����������������Ӱ����ˡ����ⷽ������֢�Ը������Ա�ø�Ϊ�����ˣ�����֢���߲�����������Ϊ�˶�����������֪�������Լ��Ĵ��������ǾͲ����������Ը�����������������ȱ����е������ˡ��������ڶ�벻���Լ������е��ŵ�Ϊ������Ҳ��ֻģ���ؾ��쵽���ǣ���Ҳ���ܻ���ķ����ǡ���ʹ������ϳ��Լ���ijЩ�ŵ㣬����Щ��������Ҳ������Ҫ�ԡ�Ʃ�磬���������������ע���������ϵ���Խ�����������������������ֳ����ļ����Ը���ָ��������ʹ���������ѩ�����Ҳ����д��һ�����飬����Ҳ������ʵ�ػ�װģ���������ʼ磬����Į�������Ƶؽ��������ʵ���֮���⡣���ر�����һ���Ͷ����������Ʃ�磬����Ը����Ϊ������ո�Դ�����Ŭ������Ȼ��������ϵ�Ŭ������ͼ�����������ҡ�
��ѧ���ײ������µıȶ������أ�Peer��Gynt��������һ����õ�ʵ�����������ر�ǿ�����Լ��кܶ���ʲ����и߳����ǻۡ���ð�յľ����Լ���ǿ������������ȴ������û�е�һ���©������������������Լ���Ϊ������ʵ�ϣ����������������������Լ����������뻯�����ң����������ġ����ɡ�������Ȩ������֮�����ѽ����ġ��������ġ���Ϊ����е�����������
�����ǵIJ������кܶ���ȶ�������������ˣ����ǿ���������Լ���Ϊʥ�ˡ���Ϊָ���ߣ��������о��Ե����������ȵȻ��룻��ֻҪ��������Щ��������ƫ����Ǿͻ���÷·�ʧȥ�ˡ����ԡ�һ�㣬���ܡ�����Ӧ�����Ƿ��棬�������ػ�������ϵļ�ֵ����Ϊ����ʹ���������������ߣ���������ʵ�йص�潼˼����ˡ����˵�Ȼ����̸������ʵ���ڡ�����ֻ�Ậ����˵����ʵ������Ʃ���и����ˣ�����Ҫ����൱��ߣ���ˣ����������˶��ܹ���æ����������ԡ�Ҫ�����ֵ������൱��ȷ���ᶨ����Ϊ�����ǻ��������Ƕ���ġ����������ָֻ��������Ը�����Ϊ��Ҫ�����ǡ���ΰ�ľ������������������Ҫ������������Ѿ���û�ˣ��������е��Ը�ȡʤ�ˡ�
�������ģ��Ը������ر����������Ǹ��������еľ�����̣����������ԡ�����־��������֢������Ϊ�Լ������е������������Ͼ�ֻ�ǡ���˼֮�������ѣ�������Ϊ�棬�����������Ի��������Ϊ�������뻯����������������IJ������������ҹ�����βŻ�����ġ�������������DZ��ʶ����ϵ������ţ����Ǿ��ɺ��������绤�����������Լ���ͻ����֮�ͽ⣬��ά�ָ��˵��鹹���穤������֮����Ѱ����ʹ����ķ�չ������ԭ����ͬ��һ���������Լ�����Զ����������������ü�����ʵ����һ�����뿪���ҵ�˼��Ͳ������ڣ����뿪�ҵ�˼�룬��Ҳ�������ڣ�����Shalott����һ���������Ǿ��ɾ��ӣ�����������ֱ��������ʵ���Լ�������ò�ġ�����ȷ��˵���ھ�������ֻ�����������Լ��Լ��������˵ġ��뷨���������Ϊʲô�й��������������˼����Ը�����ֻ��������Щ������������ˣ������ᷢ������������֢�������ϵ�ԭ��
����֢���ߡ��Ծ���ȨҪ����������Ȩ��Ҳ����ֳ������Ը���Ʃ�磬������һ����õġ����ܱ�����Ϊ������������ԣ�����ζ����Ӧ��δ���������κμ������κ���������ˣ��;�������ԣ���ζ��δ���е����˺�����������Щ�˿��ܻ��������Լ��ھ�Ժ�б��������Ӱ�������Ϊ�������磬��Ű������δ���ò�����Ӯ�ˡ���Զ��ʱ�������˵ȣ���������������Ϊ��֮�¡�
������֢�У�����Ч��ά������Ȩ���Ҫ���ȷ���Ը�����Ҫ���⡣��Щ������Ȩ���Ͷ�����ˣ�Ҫ�������ܲ��ݱ��˽����Ǯ��Ϊ���dz����ѹ�Ӧҽ�����ƣ������ǻ�����Ϊ��������������֧������������ˣ�Ҫ���������������˲�����������ǵ��Ҹ棬�����Ⱦ������ǵ����ɶ������������£������ǵ��Ը�����ܵ����������һЩ�ˣ�����ֻҪ���DZ�ʾ���Լ�����������������Ȩ������ý��ѡ�Ȼ�����ǻ�������֮�ܱ���ͬ�����ˡ����������������Ծɶ����Ǵ�ë��ã����������ϻ��б�ð���ĸо���
����֢����Ϊ�����㡰���ĵ�ָʹ�����������Ը��������Ͽ����Ƽ�ʵ������ʵ��ȴ�������Ը�һ������������Ϊ���ض��롰�дǡ�����ӡ�һλ���ܳ�Ϊ������ĸ��Ϊ��������ͨ��ֻ���������л�����㣬һλ���Լ����صij�ʵ����Ϊ�����ˣ������������Ե�˵�ѣ���ȴ���ᱻDZ��ʶ�Ļ����ʶ����թ�����������š���Щ�Բ���˽Ϊ�����ˣ�Ҳ�����ṫȻ���������ȴ���������ǵ�������ʹ�����ƭ���ˣ��ҽ����������й������ġ���ǿ����������Ϊ�ǡ�ǫ���������¡����⣬�����Լ��ġ�Ӧ�á�ֻ��һ�����۵ļ�ֵ������ǵ�������֢��Ŀ��ȴ�۵ļ�ֵ����ˣ�����֢�����Բ�Ҫ������κΰ���Ϊ����ȴ�����������Ƿ��Ϊ���ǩ���������Ṥ����һ�����������⡣���ߣ���Щ�˻���̸����һ������Ľ���Ϊ��������Щ��ȴ�����෴���Բ�ռ����Ϊ���������˿����ǵ������DZ��������ڻ�ʤ��һ�����������Ǿ����Լ���Ӧ����˽��������
�����Ҳ��ֻ�Ǵ�������Щ���Ը������ֵġ�ǿ���Ա����������еĸ߰����������ԡ��˽⡰�ơ��롰��ʹ�����Ծ���Ϊ����һ���ߣ������߸����ǵ�����������ƻ���ͻ����ϵ�һ���ܱ��ƶ�һ�㡣����֢���������൱��ߵı�ʹ�������Լ���ʵ������Ϊ������������һ������Ϊ���ĵ�����ͯ����Ҳ���Ѿ��ڷ������˽������������ƻ��Կ�����ʵ�Ķ۸��Լ����Լ��ı����ģ�����Щ˿��Ҳûʹ����ø�ǫѷ��������������������Ϊ�Ǹ߳��ĵ����ߵĸо�����Щ��ʵ��ȱ��������������������Ա������е��¶������������˽��ˡ���Ӧ�������Ρ����е�������������������ʱ�Ե��˽�����֮���棬��������ʱ�ᾪ��������������ԣ����������ڶ����ҵ�������ȴ���������Լ�����ͷ����Ȼ�����ܿ࣬�������кι�ϵ�أ�����ʹ������������߳��ĵ������֮��һ֤�������ά�������Ը��ƺ���ֵ�õġ�
�������ɸ�������֢����Щ��ͨ�Զ���չ����������ʱ��է��֮�£�һ������·��������ġ���ֱû��һ�²����Ը�����Χ��һ���˾��������Լ����Ե��ŵ㣬����һ�˿���ȴ���˿ɳܵ�ȱ�㡣һ���˴ֱ�����ȴ����Ϊ��������һ��ȴ�Դֱ�����Ϊ�ܣ������ʴȴ���Ϊ����һ��������������������Ϊ��������һ��ȴ�Դ�ţΪ�ܡ���Щ�������ű���Ϊ�٣���Ҳ���˵������Բ�������Ϊ�������������ȵȡ�
��ЩDZ��ʶ�Ĺ��̳��������������ײ�����lbsen����Ƥ�������ء�һ���еľ����ǣ������Ƕ��ԡ��ڿ��������ǰģ���ľ������ģ���ľ���С�ģ�������ľ����ǽྻ�ġ�������Ȥ�����ײ�������������ͬ�ķ�������˵�����ּ�ֵ�ĵߵ����ײ���˵��ֻҪ����������ȶ������ص�������λ�������������ʵ�ضԴ����Լ����λ�����ʵ֮�䲢��������ͨ�����ǵIJ��������������κ���Э������ֻҪ������ʵ�������������������ΰ���������ġ��У�����ͻ�ӻ���ļ�ֵ����ļ�ֵ�߶�Ҳ�ͻ�����Щ���˵ļ�ֵ�߶�һ���ĵߵ���������ص��DZ��������۹���һ�������Ҫּ��������һ�뿪������̽�����ǾͲ��ٹػ������Լ������ࡣ����֢���Ը������۳��Ժ�����ʽ�����Ǵ�����Ը���
���������˽��ˣ�ֻ����Щ���Ը�����Χ������������ʵ���������ҵ�����ԭ��֮������������Ҫ�����ȥ�����Щ������Ϊ�����̶����������ŵ�Ҫ�أ�����Ϊ�ص�����ۼ�ֵ������ص��������ص�����֢���Ը�֮�䣬�ƺ�����һ���Ĺ�ϵ��ֻҪ֪�������������е���һ������߾Ϳ���ȷ�����۳���һ���ؿ�����ʲô��ͨ�����б���һ��������ע�����˲����ڷ�������֮���������Լ�ڽ���Դʻ�ʹ���˴��۵�Ȩ����¶�������Ը�����Ȼ�����ߵ�ʱ�����˽�����ضԲ��˵�����Ϊ�Σ��������������۳�������������֢�������ݵ���Ҫ��ɫ��ʲô��
�����߽����˽�ÿһ���������е������Ը�����������ƶ����DZ���ġ�ֻҪ����DZ��ʶ�ػ��Ծ�����������̬�ȡ���ӦΪ����������Ȼ��������ΪӦ�ø����������⡣Ʃ�磬��������֪���Լ������Ի���ȡʤ���˵�����ʱ�������߾ͻ���ò�֤�����ģ������Ǹñ����Ҳ�����ñ��˷���һ������������Ϊ�����߿����˲�����������Ȥ���ڡ���֪�����������ǿ���ԣ��������Թ�ϵ����������ϰ��������������н�����Ŀ�ĵľ������˷ѡ����⣬��
��ʹ����Ϊһ����Խ�ߣ�������˽���Դ�Ϊ�١���ˣ����Է�������ȡʤ�ġ����㲻����Ȥ����ֻ���ĸ�������ɡ���ȡ������Щ���ء�ֻҪ���������ϵIJ�����Ȼ���ڣ���������벡�˽���ֱ��ڲ�ͬ��Ŀ���������������ݵ����ƶ���������������������ؽ��з�����
����˲��ȵĻ���Ϊ����������֢�Ը�������ֽ��һ���IJ���̣�������������������֮���������Ҹ��˵����۾�����ԣ�����֢���Ը�ʹ�˱�����ܹ����������ǵ������Ը�����ס֮ʱ�������Ը��������ⶼ�ɱ��˺����Ը����������������ֵ��ͷ�Ӧ���߳������衣Ҫ�����ǽ��С�˼����о�ijЩԶ�������Ը�������ʱ�����DZ��Ծ��ظе��߳ܡ�������������˺������Ը����£������������ǵ��Ը�������������Ҫ�����Ǿͻ���������������衣�����κ��ƺ�����ƻϵ���ʱ�˵��߳�������ķ�Ӧ�����Ƕ����Ȼش��������������⣺���������������������ַ�Ӧ����������ĸ����Ը��ܵ����˺�������߾������еĹ�������ȴ��Ѹ�ٻ�ý��Ʃ�磬������Ҳ����֪����Щ��������ź����ġ����е�̬�ȵ��˶��ԣ������������������ȵ��߳ܣ���������һЩ�˶���ȴ���ӷ��ԡ������������߳ܵ������ƺ����൱���������������������Բ�ͬ�˶��ԣ�������ζ�����Dz�ͬ���£�������������֪�������������йص������о��������������߳��йء���Ϊ�����밮�����룬���Զ���ijЩ���˶��ԣ�������ζ��һ���˻�������Ϊ���Ƿ��������õ���������Խ������������ֻ�밮������Ӱ������һ�������������Ĺ��⣿����ָ�������˾����κ����������ڼ��̵��˶����ǹ������ҷ���������ָʧȥ���ҿ�����ֻ���������ܹ��˽���Щ�����벡�˵������ʱ�������ܼ����ʵڶ������⾿�������Ը������������˺���
�һ�����һ���ӣ�������˵�����ȷ�����ܼ߳����������ı�Ҫ�ԡ�����δ��Ů�Ի���ӵ�а��˶�������ӣ�����������DZ��ʶ��˼���������Ƕ�ô�ز�Ը���ϰ�ס��������ֲ���������Ҫ����Ҫȷ�������Ը��Ƿ��ѱ����İ������˺��ˣ�������ˣ��������Dz�����Ϊ���İ��˲������˻�ר���������أ�������Ϊ������̫�����أ�������̫���������أ����������İ����йص�ȴ�������˵��������˸�֮�����أ�Ҫ����ˣ��ǽ�����������һ�����������⣿���а��˵����������ǿɳܵ��벻�����˵�֤��������Ӧ�������Ĵ�Ůһ����Խ������֮�ϣ�
ͨ��ͬһ�¼�ȴ���
![[HP]������������˷���](http://www.aaatxt.com/cover/2/299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