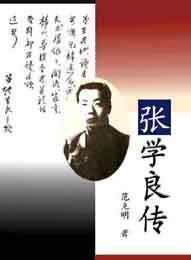张学良传-第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汉卿。彭很犹豫不敢答应。
我当即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彭才勉强答应。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他的爱人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
……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他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⒁
张素我文章除写张学良外,着重谈了她对赵四小姐的印象,她说:
赵四小姐人也很直爽,可惜身体不太好,瘦得可怜。
她穿一件藏青呢的旗袍,一双自己做的鞋子。她是一个爱漂亮的人,这十年来居然能过这样俭朴的日子,也真难得。她告诉我们她年轻的时候是怎样因爱漂亮而拔去几个牙齿,以致口腔发炎,弄得没有办法,竟将牙齿全部拔掉,镶上假牙。
今天可说是我们到台湾后最悠闲的日子,当父亲和张先生畅谈时,同去的各玩各的。我和母亲、斌妹、赵四小姐沿着小路上山去散步,走到一架一百五十米长的空中吊桥,斌妹和我毫不在乎地放大步子走了过去。赵四小姐有心脏病,简直不敢动一步,慢慢地叫一个人扶着,走了一节竟头昏眼花心跳不止,只得缩回。休息了一会,她见我母亲也平安地走了过去,于是她鼓起勇气,仍叫人扶着,勉强走过桥头。她说,到井上温泉已一年多了,从未去看吊桥,今天非常兴奋,竟能走过去,在她自己认为这是很足自慰的一件事。⒂
不过,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不同,那时他目力虽已不如从前,但身体还算强壮;而且他是有胆量的,他不仅登山、过桥如履平地,对蒋介石对他的监禁,对蒋介石的威风,他也是无所畏惧的,当时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张学良来台时,已丧失自由十年了,如今又软禁在这孤岛上。张学良居住的地方是一座平房,山峦环抱,树木葱茏。山林的鸟儿叽叽喳喳地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张学良看着飞鸟,心里浮起人不如鸟的感慨。于是,他捉了一只鸟,又买了一只笼子,把鸟放在笼子里,派人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收下了那只鸟笼,派人送来了一个更大的笼子,并捎来一句话:“你再捉鸟吧,我有的是笼子。”这就是著名的“鸟笼事件”。蒋介石直到临终的时候,也没忘记这件事,留下遗言:“不可纵虎归山。”张学良届时七十五岁,一位被囚禁了四十年的高龄老人,在蒋介石的眼里仍然是一只“虎”。……⒃
另外,据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得知张学良希望得到自由时,还曾给他送过两样东西,这就是一本1936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拖鞋。蒋介石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这便是: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对他的不敬,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十年的刑期虽然一开始就未成立(一边宣判,一边下令特赦),即使那赦免是假的,他从那以后的实际被关押时间也已超过了十年,抗日战争也胜利了,可对张学良他并不打算释放,对他的幽禁还要继续拖延下去。可能有人会说,蒋介石的报复性也未免太狠毒了,这确实是一点不假的。可是,如今蒋介石不是已经死了十多年了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还得不到解决呢?过去人们都觉得奇怪,但前不久在美国举行的一次西安事变五十周年讨论大会上,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教授汪荣祖一语道破天机,他认为张学良之所以被长期软禁,是因为国民党不愿让他自由地讲话,以免影响蒋介石的形象。也有人说,是因于凤至在伦敦存有蒋氏“九·一八”事变时给张的十余件不抵抗密电,杀张或放张都会导致泄密,致使张终身软禁。这些看法有道理。
当然,也有人说,从1959年开始,张学良在台湾已获得“有限度的自由”,对他的监视已不是那么严了,但这也正如汪荣祖所说的,再松弛的软禁仍旧是软禁。所以他在台湾始终是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来的。但在1963年夏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台北他曾有幸会见了与他们父子均有渊远情谊的沈鸿烈。当时年已八十二岁的沈鸿烈(当年粤奉联盟时,他曾充任张作霖的代表。后任青岛市市长,山东省主席),因心脏病住在台北荣总医院,病室门上挂有“谢绝访客”的牌子,一般是不见客的。但他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竟被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据曾任沈鸿烈部参谋、现为民革成员的宁修本先生根据沈氏之婿宫守义从美国寄给他的文稿整理的文章谈,那次相见,两位老人还都慨叹不已,难舍难分呢!文章说:
一日,随侍家人外出,其婿宫守义奉侍午餐,略事休息,即扶榻午睡。宫守义方阅读杂志,忽闻叩门声,恐扰病者清梦,即急趋前开门相迎,客问:“沈先生在否?”答:“正在午睡。”问答间客已径入,向病榻连呼:“成章!
成章!”来客年约五、六十岁,仪容端庄,服装整饰,身体亦颇健壮。按说对曾任高职之人,纵已离职,仍宜以旧衔相称。沈氏退居后,见者多呼“伯”,“公”或“成章兄”。其婿忖度,来客差沈氏两旬,竟直呼其号,于礼似非允当。又念既肯来访,必是旧契。遂缓步轻声禀达:
“有人来访!”时客已近榻,沈氏侧身注视,未审何种动力,不待扶协,即跃然离榻,握手抚肩,不知所可。俄而蹙额叹曰:“公何得来?又何知我在此?”客答:“(蒋)经国相邀来晤。”既坐,沈氏指客告其婿曰:“此乃‘张副司令’。”由于午睡方醒,语音较低,其婿未听真切,误为“张副师长”。按副师长年、职当属晚辈,今沈氏竟尊如父兄,而两人相见,殷切备至,当时甚为诧异。沈问:“经国怎知我来此间?”旋而又自释曰:“前日曾留一名片。”来客说:“今日为经国初度,饭时告我来此。”沈氏问:“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客未经思索直谓:
“溪口把晤,已二十六年。”其婿忽闻溪口,联想语中经国,又谛视来客面容风度,始晤此人即儿时听说的张学良将军!
随汉公同来之人,入室即静立门侧,缄默自矜。如为汉公随从,应待主门外;为朋友,当介绍入座。既知客为“张汉卿”,始悉此人之特殊身份,及其特殊任务。
汉公先问沈氏病况。继谈及多年来历任公职转折,所言概有所闻,慨叹之情溢于言表。沈氏述及对汉公处境,无能为力,今老病缠身,此生已难为报,言之怆然,悲不能抑。汉公表示生活起居,尚无不便,坚嘱沈老安心养病,勿以为忧……⒄
上述事实,清楚地说明,张学良是个重感情、重友谊、特别是非常讲义气的人,不论是对朋友对部下,他都是满腔热情的。另方面,也可看出,他虽然也可以会客访友,但却总是有人“陪”,有人“随”,对他的“保护”也可说是无处不有时时有的。有人说张学良在台湾是自由的,只是不能到外国去,这是否属实,笔者没有调查。不过,近读张魁堂发表的文章,实际情况与上述说法完全是两回事,我想,结论还是不要下得过早为好。张魁堂谈了这么一件事:
王冀先生曾来过北京。他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研究西安事变史的。他说,张学良住在台北,只有很少几个人可随时去看他。一是蒋经国,他没有当“总统”的时候,曾有时去看望,当了“总统”后就很少去了。一是三张一王聚会,即张群、张大千、张学良与王新衡。还有一个是何世禧。西安事变时,何是东北军五师炮兵营长。以后当过联勤总司令,在台湾是“国策顾问”。一般人要见张学良,先得经过王新衡。王冀先生与王新衡熟识,曾提出要见见张学良。王新衡知道王先生是研究历史的,同意他去但又不敢向蒋经国报告。王向蒋说王冀是王树常(东北军高级将领,曾任河北省主席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儿子,是教授,研究历史的,想见张学良。蒋经国反问王新衡:“王冀去见张学良有必要吗?”此事告吹。
王冀先生谈到此事时说:“如果张学良罪重,就应该判死刑,既不判死刑,却又关禁了50年,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傅晶女士写了一本张学良生平的书,她为找一张张学良的近照,去年10月,去了台湾。以前她曾请求见张学良,结果是泥牛入海,杳无消息,这次,她索性去闯门。10月23日中午到了新北投路70号张的寓所,一按电铃,门未开,门对面房子里却出来了一个彪形大汉,挺胸凸肚,问她找谁。傅一看,对面房子挂着“警务处”的牌子。傅说:“找张学良。”大汉问她:“事先联系过没有?”傅说:“没有。”“没有联系过不能见。”傅说她从美国来并说明来的目的,还掏出了证件。但一概无效,只准许她在门口拍照片。看那大汉的神气(见照片——在发表此文的右上方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显示那是一处林木茂密的偏僻街道,旁边有一宅院,门挺宽大,但却是关得严严实实,中立一位穿连衣裙的女士,也许就是傅女士吧,靠边上那位双手叉腰、挺胸凸肚的男子,想必就是作者所说的那位彪形大汉了——笔者),就可想象张学良能有多少“自由”了。⒅
每当想到这些,就更增添我对张将军的同情和思念。“渊沧壑暗蛟龙失,雨复云翻猿鹤愁”,将军何日归故里,将军何日得自由?
每当想到这一切,田汉那首感人的诗,也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某公近从息烽过,带来将军消息多:
挑灯辛勤读史记,下笔辄复成新歌。
使君学圃岂得已,子牙垂纶空蹉跎,
独疑胜利复员日,长系壮士将如何?⒆
……………………
①③⒀ 陆军、杜连庆:《拳拳爱国心,真情等诗魂——张学良将军部分诗作谈》,社会科学季刊1986年第3期。
②④⒆ 刘经发:《子牙垂纶悲蹉跎——田汉和张学良狱中诗》,载1983年4月2日《团结报》。
⑤⑦ 凭记忆据有关回忆资料提供的情况来写的,原文题名与出处不详。
⑥⑩ 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载《文史通讯》1981年第5期。
⑧⑨ 《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郑文蔚等文,晓欧摘编,原载《文摘报》第460期。
⑿⒀⒁ 张治中:《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载《文史通讯》1981年第5期。
⒂ 张素我:《我们见到了张学良先生》,见1981年12月12日《团结报》。
⒃ 赵锡滨:《张学良在台点滴》,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⒄ 宁修本:《张学良在台北访沈鸿烈》,载《青岛文史资料》第四辑。
⒅ 张魁堂:《“张公馆”外有暗哨》,载1988年1月19日《团结报》。
张学良传……在台点滴
在台点滴
时光如水,张学良是在三十六岁的英年被幽禁的,在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囹圄之灾后,当年叱咤风云的少帅,而今已届望九之年,“乌发已成了白头。我们在《西安事变》电影的序幕中看到:他微驼着背,满面愁容地在特务密布的河畔垂钓,仍然,仍然——过着被囚禁的日子。这是何等残酷的人间惨剧!”①
在漫长的幽禁中,张学良忧愤交加,精神上一直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摧残,无所寄托,就阅读书报。据当年曾经担任过看守张学良的“警卫”人员回忆,在囚系中张学良是爱读书的,赵四小姐也爱在房间里看书,每次搬迁,光是书籍,就有好几箱子。所以人们说他晚年潜心研究明史,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在与人谈话时否认此事,显然是出于谦虚;另方面,这与他的处境也不无关系,他怎能随便议论历史和时政呢。但后来,他还是“很不心甘情愿”地接受过一次记者的采访,并谈到了他研究明史的情况。他对记者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