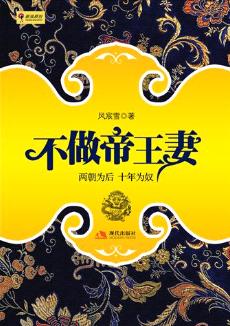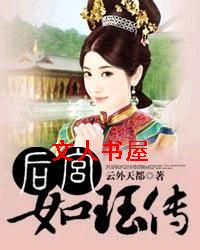王阳明大传-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种智慧才能救得了他。自然也只有这种超越了时空的思想智慧才是现代读者感兴趣的,能给现代人智慧的话题。而且是从失败中挺立出来,再造辉煌的智慧。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的真正的人生智慧。所有的哲学或思想都是为了养育这种智慧。
阳明一直寻找的也正是这种智慧。无论是兵家还是道家和释家,现在百川汇海,万法归一,通道必简,凝聚成一个也是所有的问题:怎样将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得既有效又正义?那些经传注疏只是从不再智慧的思想中搜寻各种角度和说法有什么真切的指导人生的意义?那些智慧经过长时间无智慧的解释已经退化为习惯。
“君子勤小物,蕴蓄乃成行。”他此时感到了讲玄虚空寂的释道两家在面临尖锐的生还是死,以及如何生与死时,几乎全无用处………“静虚非虚寂,中有未发中。”他现在开始拈出后来心学普度众生的修养法门了:什么“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忘,是故意去寻找无念头状态。助,是人为地来“拔苗助长”。王氏本人区别于其后徒的一个“指标”是王始终坚持“事上练”。找“忘”是坐枯禅。既要在事上练,还不能堕入缠执之中。不是一般的做什么事成什么人的问题,而是在做事中体悟存在,既不能在做事中遗忘了存在。也不能在体悟存在时反对做事,不会做事,败事。用他的话说即“践形乃无亏”。在这个意义上,他主张“愿君崇德性,问学刊支离。”
后儒将朱子“派”为“道问学”,将陆九渊“派”为尊德性,并强解析为水火不容的两派。至少此时的阳明并不反对“道问学”,只是要求在问学时,去掉溺于支离破碎字词析义的毛病即可。
“无为气所役,无为物所疑。”
“生人不努力,草木同衰残。”
7.北风送南雁
他是在料峭春风吹人冷的时节,离开他本要大展宏图的京都的。
汪抑之,湛若水,崔子钟等人为他赋诗以壮行色,他也在他们的呵护中渐渐复苏了精神的活力与信心。虽不能说失败的打击与痛苦已被彻底克服,但基本上是莫予毒也了。他〃南游〃走了不到十几天,就再次赋诗申述前几天答诗的未尽之意,并且在梦境与他们重逢。毫无风刀霜剑的威逼感,并且再三念叨他们要在衡山结庐,共同研究《易经》的约言。经典,必然是他这种如〃惊鹊无宁枝〃者的家园。心学家是热心肠思想家。
但是刘瑾是冷心肠政治家。于公开打击之外,他增加了超法度的暗杀。他的逻辑很明确的黑社会规矩:要么是我的朋友,立即升迁;要么是我的敌人,必欲置于死地。王阳明本是可用之才,但他既然不为我所用,就尤其要杀之而后快。因为他有才。极可能是王出狱后的活动使刘瑾感到腻歪,才在阳明出京之后决定追杀他。要不然,是不必大老远的非到钱塘江才下手。王惹恼刘的地方大约是他又与文人诗酒唱和,不老老实实,〃悔过自新〃,还乱说乱动,尽管王留下来的诗中没有直接骂宦官的句子,但刘瑾是最腻烦文人结团的,象日后的任何大独裁者反对文人抱团一样,如张居正,清政府。自然,他把干掉王的计划交给下面的杀手去执行后,他本人就忙着搞财政改革,取乐去了。大人物不总记着小人物的死活。象阳明这样的六品主事,只要不抱团,永远也翻不了刘瑾这个大船。
为什么非选择钱塘江?不定在芦沟桥,或沙河,黄河?也许是在那里才追上。还有一个刘瑾的党羽在哪里更得力的问题。自然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此事的真伪。因为,锦衣卫杀人是肆无忌惮的,会兜那么大的圈子,费那么大的劲?更主要的是在阳明当时的诗文中没有这种刀光剑影的丝毫痕迹………这自然也不足为没有此事的证据。从来就有两派:毛西河等认为“谱状乃尽情狂诞”;冯梦龙的「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则详细如小说家言,写锦衣卫二校胁迫阳明投江,阳明在别人的帮助下骗过二校,假装投江,然后趁船至广信,等等。二说都是以意为之,不足深信。
所以,我们还是不妨按《年谱》及查继佐的《王守仁传》来复述这个故事。〃故事〃说:锦衣卫杀手追到江畔,阳明虑难得脱,急中生智,用上了当年习学侠客的那一套本事,将衣服鞋帽或投至江中,或搁置江畔,成功地布置了自杀的假现场,骗过了那些职业杀手「这其实很难。江水滔滔,杀手们看见江中衣帽须距离很近,距离近则能看见真相。距离远,走到跟前则看不到任何现场。再说锦衣卫的人岂是等闲之辈?」然后,他偷偷地爬上一条商船,船是去舟山的,并忽起飓风,他们一日夜就到了福建界面。他爬上武夷山,如惊弓之鸟,一气窜入深山之中。
刚刚复燃的希望之火又蒙兜头一盆冰水,他实在是不想再出山了。情绪再稳定的人也受不了这么不稳定的现实的冲击,更何况他并不是个稳定的人。当然,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找个安身之地。深山之中只有寺院,到了晚上,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寺院,请求容纳,但人家不收留他。一个面色发绿,神色荒凉,来路不明的中年男人,不容易被相信。他没法,只好在附近的一个野庙里落脚,躺在香案上睡着了。
这个野庙是老虎的家。那个不给他开门的和尚以为他已喂了老虎,来拣他的行囊。却见这个风餐露宿,爬了山的人睡得正香。这个势利的和尚以为他一定不是个凡人,就又把他请回寺中。
无巧不成书,当年他在铁树宫谈得特投机的那个道士,象正在这里等他似的,拿出早已作好的诗,其中有:
二十年前曾见君,
今来消息我先闻。
似乎是专门为来点化他的。
阳明问他该怎么办?并把自己刚下定的〃将远遁〃的决心告诉他。可能还给他看了刚写的与家人〃永别〃的诗:
移家便住烟霞壑,
绿水青山长对吟。
道士说:你父亲现在朝中,你不屈不要紧,刘瑾会把你老父亲抓起来。你是隐于深山了,但瑾会说或者北投胡兵了。或者南投海盗了,给你定个叛国投敌的罪名,你下三代都抬不起头来。
阳明知道他说的对,但一时难已回心转意。道士为他占了一卦,卦得《明夷》,虽是光明受损伤之卦,但可以有希望的等待着,会有圣主来访。这给了阳明信心和勇气。人,就是这样,只要有希望,就可以忍受………心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希望哲学。是阳明在〃动忍增益〃中锤炼出来的自救救人的智慧学。他本人也是有了希望就有了豪迈的气概:
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其实,他只是刚刚不滞胸中。尽管如此,这位心学大师毕竟魄力蛮大。他又毅然出山,重返充满荒诞和希望的人世间。
他毕竟不是无名小辈了。在京城流传着他自沉于江水,至福建始起的神话。还有他自己的诗为证:
海上曾为沧水使,
山中又遇武夷君。
信以为真的人告诉湛甘泉,湛哑然失笑,说〃此佯狂避世也〃,他同时也笑世人喜欢〃夸虚执有以为神奇〃,哪里能懂得阳明这一套虚虚实实的艺术。湛还作诗总结王的这种〃艺术〃:〃佯狂欲浮海,说梦痴人前。〃他是显然不相信阳明沉江至福建复出的神话的。几年后,他们在滁州相会,连袂夜话时,阳明向老朋友吐露实情,的确是在英雄欺人,果不出弱水所料。莎士比亚说:人生尽管充满喧哗与骚动,却如痴人说梦,毫无意义可言。痴人说梦自然是一踏糊涂,但阳明是给痴人说梦,说梦者是有意为之,也算有意义吧。
据「年谱」说,他从武夷山下来,到鄱阳湖北上,去南京看望因受自己牵连被刘瑾给弄成南京吏部尚书的父亲,但没有别的证据。有的学者从他赴谪的时间,路线,及沿路的诗作推测,他不可能到南京去省亲。但也没有他未去的直接证据。假若,他真去了,算是他重返了〃祖宗〃轨道,可以坦然地来见家大人了。嫌小阳明太调皮的王华倒对大阳明相当满意。父子相见,尤其是经历了几乎是生死变故的重逢,当然会感慨万千。父不会怨子惹事,子不怪父不救;因为刘瑾几次让人传话,只要王华去瑾那里修好,父子二人均有好处。毒蛇一样的刘瑾还有个优点就是爱才,状元王华的大名,他很重视。越是独裁政权越需要名流点缀。但华的风骨是有口皆碑的。大概父亲支持儿子的选择,让他忍耐一时,二人可能都洞察到了刘瑾灭亡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不会象马基雅维里那样去讨好一个即将垮台的权力班子,弄得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遇。再说明朝的官员升沉起浮具有极大的戏剧性。不必为一时的失败而毁弃终生。详情因无确切记载而难知端底。
他在北新关看见了他的几个弟弟则有诗为证,他喜不自禁地说:
已分天涯成死别,
宁知意外得生还。
此时又只怕这骨肉重逢是梦。同样是梦,有时唯恐是真的,有时唯恐是假的:〃弟兄相看梦寐间〃。当然,既然已经生还就与真死了大不相同了,哪怕是差一点死了,但没死就是没死。所以感叹唏嘘之后,〃喜见诸弟〃的喜是主要的。
虽然是贬斥到边地去作小吏,但没有限时限刻的死日期卡着。再说刘瑾忙得很,没有必要盯着一个小小主事。他可以从容地走走停停。正赶上又病了。这是大难过后的必然反应。如果他未去南京,则无重返杭州之事,而只是从北京下来时在钱塘江畔住下来没走。现存赴谪诗证明他在杭州住了好些日子。先住在南屏山的静慈寺,应该是从春至夏都住在这里。起初还有兴致游南屏山,再后来,又移居到胜果寺。
杭州,是他的老朋友了。现在是〃湖山依旧我重来〃。他这次过的这个春天和夏天是舔伤口了(〃卧病空山春复夏〃),胜果寺可能更凉快……〃六月深松无暑来〃。他得的是肺病。只宜静养。他现在既需要用静心的沉思来〃洗心〃,也需要用高质量的空气来洗肺。他从心眼里喜欢这个风水宝地。在这种人间天堂的环境中过心魂相守的宁静的书生日子,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望。再用颜子的内倾的精神境界来比论一番,就更心安理得了。〃把卷有时眠白石,解缨随意濯清漪。〃这种冰雪文字是心存富贵的功利人写不出来的。〃便欲携书从此老〃是他真实的心声。他若没有这种淡泊的心境,也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功业。因为淡泊养〃义〃,因义生的〃利〃才是好〃利〃。此时还算进修,在深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功夫。当然,只有这样养心,才能养病。
《年谱》将这一年定于〃在越〃,极可能是在杭州养得病接近好了,便回到绍兴。虽然无诗可证,但基本可信。而且有〃大事〃发生:就是余姚徐爱,山阴蔡希颜,朱守忠,正式举行拜师礼,在当时只有举行了这种礼才算正式入门为弟子。否则,只能算私淑,算业余的学生。这三个人,至少徐爱,早已从阳明问业。就是两年前阳明在京〃门人始进〃时,也可能就是他们。
今年,阳明36岁,干支记年则岁在丁卯。记年文有《别三子序》,开头大讲师友之道:〃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举业之习,圣学几于息矣。〃将圣学的存亡与师友之道的兴废因果性的联系起来,是在批判官方的做法,将圣学〃异化〃为进身仕途的应试教材,儒学的精义遂彻底被遗忘了(参看拙著《新评新校》《与中国士文化》)。显然,师友之道是用师生链的形式保持着原儒之士子儒学的真本色。经过主试山东,以及后来的这场风波,阳明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自己另起炉灶,创立自己的学说和〃干部〃队伍,才有可能甩开官场那套混帐王八蛋做法,使圣学真正复兴起来。
所以,他虽身处逆境的极点,但偏要开〃顶风船〃了。正式接受徐爱等三人,做起〃导师〃来。这毫无虚华之意,倒有切身的反面感受:〃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悔也;求友于天下,而与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于天下,二三子之外,藐乎其寥寥也。〃现在收获了这三个弟子,他无比欣慰。但三人同时被举荐为乡贡生,就要到北京去了。他告诉他们,到北京后,找湛若水,就象跟他学习一样。
他坦白地说,这三个同志的离开,使他有失助的遗憾。他们自然是在哪儿都一样学习,〃而予终寡乎同志之助也〃,他是要准备做点什么了,〃同志〃一词,在此具有它最神圣的本义。就是要与自己一起与地面垂直相交,〃出身承当,以圣学为己任〃。
这种态度暂时还只是内倾性的一种人生姿态,它一旦有了广大同志,便是实体性的社会力量,就精神变物质了。阳明当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只能是〃沉潜〃期,也当然只是〃潜龙〃在〃勿用〃时期的沉潜。他语意深长的教导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