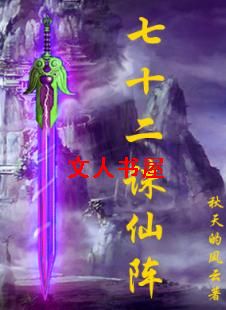七十七街安魂曲-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个孩子。麦克说,他再也不准备结婚了,但要是孩子生下来的话,他准备接受下一次挑战。
我有种感觉,我的妻子不准备再让我走进家里。
我们整个晚上都坐在那儿。直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才有人来检查那辆车。那个星期天的清晨,在太阳升起来之前,我们三个人又说了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那个晚上,我感觉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麦克和道格与我贴得更紧。”
海克特从睡椅上站起来,走出了镜头之外,屏幕上变得黑乎乎一片。
“还有更多的吗?”我问。
“我不知道。”吉多说,“他在一次采访的末尾录下了这段东西。我必须把所有的带子看一遍才能知道。”
麦克9点之前回家了。我到门口迎接他。他看起来非常疲惫:衣领敞开着,领带松松垮垮的,上衣搭在他的右手上。他左手拿着一叠厚厚的还没有分拣过的信——它们已经在桌子上压了几天了。
吻他的时候,我感觉他的脸颊粘糊糊的,还有一股特别的药味。
“吉多找到一盘海克特自己录的带子。你应该看看。”我把手伸向他的上衣。
“带子上有什么?”他问。
“海克特谈到了弗兰迪死后的那天。”我拿走了他的上衣,发现麦克的右手手掌上裹了足有两英寸厚的纱布!我的胃一下子痉挛起来,但我只说了一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宝贝。”
他看起来十分胆小:“安东尼·刘易斯不想出来。我必须把他带的一把刀抢过来。”
“缝了几针?”
“两针。”
“你哭了吗?”
“没有。我一整天都在工作。”
“你在安东尼的屋子里发现什么了吗?”
“还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搜查令。但不管怎样,我可以把他关押到对他的活动有个更好的控制为止。”
“拉斯孔怎么样?”
麦克笑了:“我有点喜欢与那个小子一块工作了。他给了安东尼漂亮的几拳,把他从我身边拉走了。”
我透过纱布的边缘瞧了瞧,看见手掌的中央放着一点黑色的药:“伤口看起来很干净。”
“这不碍什么事。”
“你想这会让你逃脱洗碗这差事吧?”
他笑了起来,把我拉近:“如果我可以洗碗,那么我也可以洗个澡。”
“完全可以。”我吻了吻他的下巴。
吉多插进来了:“叫什么道尔的打电话找你,玛吉。她说她找到了你要的枪。”
16
拉斯维加斯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
在赌徒云集的商业中心外面,越过那些闪闪发光的回屋顶和令人赏心说目的宫殿式的建筑,是一大片空地——这足以让任何大城市都感到汗颜。这看起来更符合那些逃犯、难民们的口味。
一条新建的商业街占用了莱斯特·奥尔斯沃西家的废物旧货栈,也许就永远埋葬了那个故事——1976年的冬天,罗伊·弗兰迪的左轮手枪是如何出现在这的。芭蒂·海斯特、比尔和艾米莉·海瑞斯这些共和军成员曾经住过的汽车旅馆,已经被一个正在扩建的县级医院收购了。
我站在废物旧货栈上面的停车场里,对准吉多摄像机的镜头,大声读着道尔·伊赛尔顿找到的拉斯维加斯警察局里的报告:“阿妮塔·奥尔斯沃西夫人报告道,她在整理她去世的丈夫莱斯特·奥尔斯沃西的财产时,发现了一把38毫米口径的史密斯·文森牌左轮手枪,编号是328414。奥尔斯沃西夫人说不知道她丈夫是怎样得到这把枪的。拉斯维加斯警察局保管了这把枪,并给奥尔斯沃西夫人一个财产收据。
“财产科对枪的号码作了一次例行检查,证明这把枪为洛杉矶警察局罗伊·弗兰迪的个人财产,但资料说这把枪早已被盗了。”
资料中最后一条注释表明:弗兰迪的枪在被认出来之后,就移交给联邦调查局了。
在镜头前把这一切都说清楚后,我走出了镜头的范围以便吉多拍摄背景。
这时的气温是摄氏39度,到现在我们连早饭都还没吃。
吉多和我碰运气在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的最早一班飞机上找到两个座位,天亮后不久就抵达了,道尔·伊赛尔顿就在飞机场找到了我们。
“我打电话给奥尔斯沃西夫人了。”道尔说着,在租来的汽车里伸着懒腰。“她答应见你,但是她说只记得把枪交上去了。那事过去很久了。”
“我们会试着用一点点现金帮助她恢复记忆力;我可没时间和她逗着玩。”我接过道尔给我的一大瓶可口可乐,“我预定了中午去奥克兰的航班。在那儿我有一个不想错过的约会。”
道尔穿着一身白色的凸纹布衣服,看起来很精神。她伸过手来,帮我理平了我的蓝衬衫的衣领:“我们今天很倒霉是吗?”
“今天太阳打西边升起了。”我说着,把冰冷的杯子放在我的脸的一边,“拿这个报告资料费了很大劲吗?”
“小意思了。”她一脸的不屑,“我在这个城市里干过很多事——城市里的建筑物一天天增多,有很多东西也进进出出的。我只是‘开发了’一下我在这儿的警察局资源,给他们买了几瓶酒,事情就搞定了。希望没耽误事,只是这个报告太老了,它还在档案库里。还有,没有更多的记录,真糟。”
“太糟了!”我应道,“你能查出联邦调查局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吗?”
她摇摇头:“你把找枪这件事告诉我后,我就打电话问我的男人。他提醒我,所有的资料注释都交给了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
“那个给我暗示的联邦调查局官员也说这是一桩死案。”我摇了摇杯子里的冰,“我有一个经验,有时候你觉得毫无出路时,在另一端也许还有一些可走的路。”
“上帝啊,再次与你合作真是有趣。”道尔笑着,她那黑黑的眼珠闪闪发亮,“如果我半途而废,我将一事无成。对吗?”
吉多加入了我们的对话:“我们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吗?”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然后说:“还不行。”
奥尔斯沃西夫人家的惟一一块阴凉地是屋子旁边的快腐烂了的帆布活动小屋。但我们必须待在外面,她说,因为屋子里乱糟糟的。虽然她家的窗户上挂着一个空调,我却并不想和她争吵。如果这个院子比房子里更赏心悦目的话,那么不管里面有没有空调,我都不想进去。从小院子的景象来看,她把她死去的丈夫的一点点废物带过来了:修理工具,用坏了的家具,一箱箱的旧杂志,还有手臂那么高一摞的各式各样废物,都与停车线平齐了。
吉多脱下他白色的T恤,把它浸泡在漏水的花园水管下。在他扛起摄像机之前,又把T恤罩在他的头上。小屋那边的沙漠反射着刺眼的太阳光,吉多一个劲地抱怨着这么高的温度会破坏他的录像带。与此同时,奥尔斯沃西夫人和我清理出一块地方来,摆上了两张折叠椅。
我坐在奥尔斯沃西夫人旁边,两条大腿紧紧地夹住一块冰,躲闪着穿越千疮百孔的帆布小屋射来的光箭。这些光箭里居然还夹杂着一丝微风。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她家小屋旁边的温度计表明阴凉处的温度已是摄氏40度。15分钟后,当我们开始谈话时,已经有41度了,而且还在往上升。
“我的丈夫死后,我必须卖掉一部分财产。”奥尔斯沃西夫人的手在那罩着她白色卷发的发网上摸了摸,“我猜,那把枪成为他的东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的。”
“你为什么把枪交到警察局去?”我问着,给吉多的摄像机一个侧身。
奥尔斯沃西夫人直视着摄像机,口齿清楚地说:“我把枪交上去是因为法律的威力。”听起来她好像正在背诵一段古老的箴言,“上帝啊,因为我不能说谎。”这样的回答对我来说真是太正确不过了,但却毫无用处;我花了钱,所以我不能这么客客气气地对待她。
我猜她该有八十多岁了,但我没有问。早上8点我们敲门时,她已经穿戴好了,正在浇仙人掌。她很勤劳,我想。谈论起她的孙子孙女时,她兴致高昂;但问及她的丈夫时,她很害羞,充满了警惕。
我又试了一次:“吉多和我就站在你家的废物院子里面。他们什么时候建起这商场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她的目光越过沙漠,似乎莱斯特的地方还在那儿,“十年吗?也许是十二年。那个商场比莱斯特的废物院子不知要漂亮多少倍。”
“告诉我你丈夫做的生意。”我说。
“它就像另外一个废物院子。”她用一块纸巾轻轻地拍打着她那扑了粉的脸颊,“卖一些小玩意,杂货。”
“他从哪儿进货?”我问。
“进货?”她笑了,“你是说,他的废物?”
“所有东西。”
“他走出门在街道上找到的。或者有些人给他一些东西交换或让他代销的。找到那些废物不成问题,找到买主才是问题呢。”
“他经常买卖一些火器吗?”
“不。”她说着,变得警戒起来。“莱斯特留了几把枪以作防身之用。但他不是这种商人。他没有卖枪的执照,连一把枪也买不起。”
我向她靠近了点,看见吉多把镜头也对准了我们。“莱斯特是怎么得到罗伊·弗兰迪的手枪的?”
“我不能说。”她又把目光投向沙漠。“当然,那把小手枪也不是我那天上交的惟一一把枪。还有一把卢格牌手枪,一把机关枪。”
奥尔斯沃西夫人还说,她也记不清楚她是否遇到过掩护芭蒂·海斯特那些共和军成员的汽车旅馆老板。二十年的时间太久远了,人总是很难再记住往事。
道尔开车送我和吉多去联合大厦。与每个东部的城市一样,那些房子都特别的新。从那个同意与我交谈的地方官员身上,我一无所获,从其他人身上也一样。虽然道尔在一旁鼓动,但一个死去的洛杉矶警官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
带着一些我认为有趣的电影胶片,带着一个有着太多遗失的碎片的谜,我离开了拉斯维加斯。
我对谎言感到了厌倦,甚于任何可恶的东西。
17
我坐飞机到了奥克兰,然后开车从旧金山的海湾地区高速公路到了伯克利。
像拉斯维加斯一样,伯克利的商业中心也是由一条一条的街环绕而成,但是面貌却大不相同。拉斯维加斯极尽繁华奢侈、富丽堂皇;伯克利却多多少少是由很多东西组成的和谐的“混合物”。街上有摆小摊的嬉皮士,有乘车过桥直达旧金山的衣冠楚楚的雅皮士,还有大批的学生,他们和谐地相处着。
夏塔克大街、电报大街、本克罗弗特路,这几条环绕着校园的主要街道,在我到达的那个暖和的星期五都是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加利福尼亚大学秋季学期刚开学几周。我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中,听着这熟悉的、我深爱的街头声音,就像听着我爸爸的摇篮曲一样,陶醉在其中。
每个新学年的开始,我最爱看的集体莫过于大一新生了。他们在开课前的一星期到来,大部分都是他们原来所在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们被家里送入这个大家庭,内衣内裤里还绣着自己的名字。在他们回家过感恩节之前,他们的新衣服都变成了一样的红灰色,因为谁也没有时间去洗衣服。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理、脑袋里装满了刚学完一半的课程,这足以让他们形成自己半成熟的观点。他们昂起头,准备向他们的父辈坚守的东西发起进攻。在5月末他们的第三个学期结束后,他们有所分化,或变成在学习上失败的人,或成为新生中的优秀人物。
天气炎热,但比起我刚离开的沙漠,它又太温和了。我在冷饮店停了下来,买了一杯新鲜的水果雪泥,这也让我找到了一个逗留的理由,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我脱下我的亚麻布茄克衫,披在肩上;把那溶得很快的雪泥举在前边,以防它滴在我的衬衫上。
我姐姐住的小型医院在校园的西北部,离我家不到半里远。我走上夏塔克大街,准备抄最近的路穿过校园。也许我可以在物理系停一下,向几个老朋友问声好呢。但我还有充裕的时间,于是我绕道而行,踏上了校园南边的宾尼大街。我在2603号前面停了一下,芭蒂·海斯特就是在这儿被绑架的。
路旁的香柏木表明芭蒂曾经住过的屋子年代久远了,但它的状况仍然很好。对于大部分学生,乃至年轻的老师们来说,这样的房子都不是他们住得起的。
我现在可以理解,芭蒂这种舒适的生活何以会激起那群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人的愤怒。绑架芭蒂的人既不贫穷,也不疯狂。他们和她一样,都是那种中上层阶级家庭娇生惯养的孩子。
四周特别安静。据说1974年芭蒂,海斯特与绑架者在晚上搏斗并大喊大叫的时候,四周的邻居一副冷漠无情的样子。就像罗伊·弗兰迪死的那个晚上,西部八十九街122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