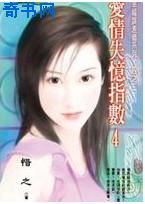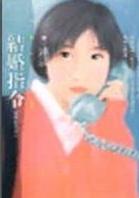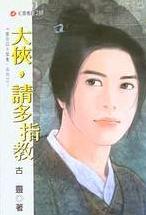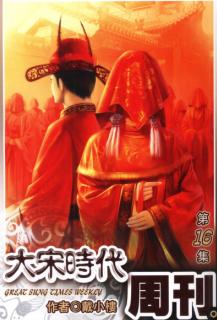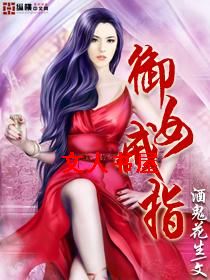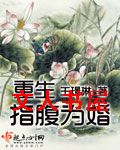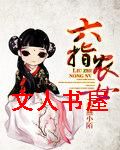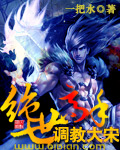大宋金手指-第29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透过那层青纱,只能隐约看着她脸部的轮廓。
如今大宋女子若是抛头露面。几乎都会戴着这样地小洋帽儿,最初时还有些老学究跌足大骂世风日下,但随着女子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增多和她们自己地经济收入足以支撑起一个家庭,这种骂声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
抱在女子怀中的小孩大约三岁左右,乌溜溜的眼睛不停地眨着。紧紧盯着窗外,满脸都是好奇。
“先生请了。”或许是因为无聊,也或许是因为胡幽总盯着他们打量,这一家三口中的男主人开口向他招呼,因为在车上缘故,礼是施不周全的。他只是抱了抱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先生若是不嫌弃,可否与在下一叙?”
胡幽这边,除了他之外,就是他地一个亲卫。作为大宋水师的战舰设计师,同时也是目前博雅楼学士之一,他走到哪里,至少都会随身带着几个亲卫。因为此次回临安不欲声张,他和亲卫都穿的是普通人服饰。听得那家男主人相询。胡幽点头笑了笑,也拱手还了一礼。
在他们这批人当中,胡幽年纪与李邺相当,如今已经是三十出头,多年海上生涯,使得胡幽有一份水员特有的豪气,而他这十年来的刻苦专研,又为这份豪气中增了分饱学之士的儒雅。他留了胡须,看上去也很成熟,身边地亲卫才二十出头。两人在一起时象是长兄带着幼弟一起出游见识世面。
“在下姓贺。单名俭,子朴。原是绍兴人氏,如今在金陵冶炼厂,不知兄台高姓贵籍?”
“小姓胡,名幽,字静水,泉州人,如今在华亭府。”胡幽微微一笑,这个叫贺俭的男子二十三四岁的模样,看上去有些健谈,虽然已经成家有了孩子,却还保持着一颗少年之心。
“胡先生在华亭府高就?那定然是在江南制造局了,那地方好,那地方好!”
听得胡幽是在华亭府,贺俭面上露出敬佩的神情来,立刻猜到了胡幽从事的行当。这也不奇怪,华亭府最重要的产业便是江南制造局,如今江南制造局除了生产船舶之外,还生产诸如自行车、机械钟表之类的民用产品,销售得非常好,整个华亭府的产业都是围绕着江南制造局布置开的。
华亭府建设从炎黄元年便开始了,到现在已经发展了五年,无论是工业发展还是民生设施,都比较齐全。最早一批江南制造局地工匠管事,如今就算不是腰缠万贯,数千贯的身家也是有的,故此贺俭听得胡幽之语后立刻露出羡慕的神情。
“你们金陵也不错,今后还要靠你们照应着呢。”胡幽笑着说道。
耶律楚材知建康府也有近四年时间了,他通过聚财三策,自民间收敛了大量余钱,借钱生钱之下,金陵的工业发展非常迅速,冶炼厂已经向大宋铁路局提供合格的钢铁,金陵至徐州的铁路铁轨,有七成都是在金陵冶炼厂生产的,而徐州至汴梁的,更将是百分之百金陵产。除此之外,金陵冶炼厂还负责向江南制造局提供钢板,供应制造局所用。
“哪里哪里,不过是跟着江南制造局混口饭吃罢了,对了胡兄,我在厂子里听说,江南制造局定购了大量的钢板,准备制造铁甲船,不知可有其事?”
铁甲船就是胡幽此次回临安地原因,听得贺俭问及此事,胡幽笑了笑,没有作声。这是大宋绝秘消息,却不知道这个贺俭从哪儿听到地,看来回去之后,大宋的保密工作要继续加强了。
“这位先生也太言过其实了,铁甲船?自古以来水沉于铁,铁又不是木头,如何能浮在水上?”胡幽不回答,在贺俭身后一人听得二人对话探过头来道:“学生虽是不才,也曾拜读过智学之书,知道木头浮于水上是因为比重轻。钢铁比重大,放在水中必沉!”
“我看倒未必,若是给木船加铁甲,只需铁重量不超过船自身浮力,便不虞船会下沉,家中长辈说二十余年前在沿海制置使有这种铁甲船。我听说江南制造局便有船用钢材做龙骨,胡先生。是否有此事?”与那人同座者也插言道。
以钢材做龙骨倒不是什么秘密,胡幽笑着点头:“确有其事。”
“还有以水泥为船地我便在长江之中见过。”那第二个插言者得到肯定答复甚为高兴,向胡幽、贺俭点了点头,然后兴奋地道:“水泥既然能为船,钢铁又如何不能为船?”
越来越多的乘客都介入这个话题之中。贺俭甚为健谈,说得口沫横飞,他的妻子与儿子只是盯着他,明显对他有些崇拜。
从华亭到临安,不过是八个钟点的路程,他们说得兴起。不知不觉中便忘了时间,直到半空中传来雷声,他们才惊觉过来。胡幽将脸贴在窗玻璃上向外望去,只见天空中重云叠影,黑得象是夜晚,银蛇一样的电光在云层间钻动,晃得人心生敬畏。
“要下雨了。”贺俭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声。随着他这声话语,天空中响起一声巨雷,紧接着暴风倾盆而下。天空象是被捅开了一个大窟窿一般。风也大了起来,打着旋儿将树叶、羽毛、砂石等一切它能搬动的东西卷起,狠狠地撞向火车。为了安全,火车地速度放慢了,胡幽皱了皱眉,这情形,只怕火车要靠站避雷,不会冒雨前行。
这是大宋铁路局的硬性规定,风雨或者其余恶劣天气之下,若是出行有危险。那么火车便要停靠在开阔地避险。毕竟火车速度较过。一车之上干系千余人性命安危,不得不谨慎从事。
果然。火车最终停了下来,乘务员到各车厢安抚乘客,而乘客对于这突如其来地恶劣天气也无可奈何,只能是抱怨两声。外头风很大,吹得木制的车厢不停的摇晃,仿佛随时可能散架一般。胡幽发现贺俭的小孩儿满脸都是惊惧,抓着母亲在瑟瑟发抖,便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了一把糖果,将之放在那小男孩面前地桌几之上。
“乖,别怕,小小男子汉,应该保护娘亲才是。”胡幽对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他的小孩儿笑道。
那小孩儿见着糖果,果然不怕了,看了胡幽好一会儿,确认这是给自己的之后,立刻伸手一把抓住。他人幼手小,全力去抓也只能抓着三个,握拢时还有一个从他手是落了下来,于是他又伸出一只手,想要将剩余的糖果也抓起来,但仍然未成功。他抬起头,向母亲求助,母亲却轻轻地责备他道:“就知道好知,还没有谢谢这位伯父呢!”
“多谢伯父。”小男孩倒挺大方,奶声奶气地道。
胡幽眯着眼睛笑了笑:“这孩儿挺聪明的,叫什么名字?”
“单名一个爽字,用地是他恩公之名,只是尚未经他恩公允许。”贺俭笑道:“这孩儿顽皮,曾将头摔得一个大洞,若不是恰好神医秋爽应耶律学士之邀到得金陵,他这条性命就保不住了”
“看,看!”听得父亲说起自己的“英雄事迹”,小贺爽将头伸过来,露出右边头上的一道不明显的伤疤。听得秋爽的名字,胡幽笑了笑,心中隐隐有些怀念。
与秋爽也有两三年不曾见面了吧,这厮仍在主掌流求事务,还在流求与举国名医进行医学探究,据说他用一种被称显微镜的新式仪器,发现所有生物都有细胞,还发现了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却影响人体健康的“细菌”。他年纪还不到三十,但已经是了不得的名医,便是贺俭这样地平民百姓,也敬称为神医了。
“胡先生在江南制造局,当与流求省相熟,不知是否去过流求。”贺俭又道:“区区这两年一直有个心愿,便是领着这孩儿去流求拜谢秋神医,也请他允许我这孩儿用他的名字。”
“海路艰难,带着这么大的孩儿怕是不易,便是到了,他忙碌不休,只怕也没有时间见你。”胡幽摇了摇头:“为何不寄封信去,我倒是知道秋神医的通信地址。”
胡幽说秋爽忙碌不休是有原因的,秋爽如今几乎是一个人当四个人来用:要管理流求的日常事务,虽然下面有数以千计的大小属官,但重大事件都需要他个人拍板决定或者上报天子;要进行医学研究,对于细菌和如何杀灭对人体有害的细菌,他正在进一步研究;亲自为人诊病,作为一个郎中医生,为人诊病乃是积累经验之必然;与来自大宋各地特别是原先中原地区的名医进行探讨,如何用传统医学理论解释这两年来的重大医学发现。这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让一个才智超群者耗尽所有时间,可秋爽不仅四样齐上,还面面俱到。
这背后,自然离不开赵与莒地指引,有些东西,虽然赵与莒不知其所以然,但却知道如何去研究去探寻。
其实胡幽自己也是如此,他们这六期地义学少年,大凡学得本领的,都同时兼任某项职务和从事某种科研。
“这般大风雨,今年地秋收只怕有些艰难了”他正思考之时,忽然听得一个声音叹息道。胡幽回过头去,是离他不远处的一个儒生,这人不过三十左右,生得甚为英挺,衣着华美,腰间还佩着剑,看那剑模样,应是重达近一斤八两的真剑,而不是那些手无束鸡之力的书生们用来装饰的轻剑。
听他提及秋收,胡幽心中又是一动,众人此时只是担忧自己行程,想得远些的还担忧这趟列车的安危,唯有此人,却关注的是农业秋收。
“这位兄弟,请教高姓大名,不知能否一叙?”胡幽向那人拱手招呼道。
“在下姓秦,名九韶,字道古。”那人道。
秦九韶虽然回应,却没有拱手,显得相当倨傲,胡幽也不以为意,而是问道:“秦先生方才说的秋收艰难,不知从何谈起?”
“区区随父在临安宦居数载,前些年作为太学生去流求学智学,这个月才回临安。”秦九韶说到这里,看了贺俭一眼,然后又道:“我观流求施政,以农耕为本,每年耕地播种之数,各府县俱有定数。区区原以为流求工商兴盛,对这农事并不甚关注,到了流求才知,原来越是工商兴盛,农事便越来重要。”
他停了一下,看到众人都在侧耳倾听,不由微微露出自得之色:“以如今大宋最兴盛的纺织、酿酒诸工商业为例,丝麻棉花,玉米麦稻,尽数来自农耕,农耕若是不保,不仅百姓口中无食,工厂里机械也无料。”
说到这,他又冷笑了声:“天子圣明,躬重农耕,田亩稼穑,皆有定数。听闻如今有人宣扬,大宋富有四海,若是本土缺粮,自可自海外行省调运,若是海外行省调运不得,还可自周边诸国购买,这等见识浅陋之徒,若让我见了,必啐其一脸唾沫,要他见识我腰间三尺龙泉是否锋利!”
胡幽只觉得微微有些发热,这秦九韶扯得也太过了些吧。
(修改加入:继续请求月票,虽然更新速度慢了,但写的时候其实更用心了些,还请列位读者将《金手指》保持在分类月票前十五名之列,拜谢了。)
注1:西元1611年克卜勒提出复合显微镜的制做方式,165年虎克发现细胞,1683年李文赫克发现细菌。此时大宋科技已经相当于英国1830前的水准,生产出合用的显微镜不是难事,批评区区说又给小赵同学机器猫时空口袋的看官,不知可接受作者说辞否?
注2:西元1203年,秦世辅造铁壁铧嘴平面海鹘战船;在船舷包裹上铁甲。
注3:秦九韶在原本的历史上于绍定四年(1231)考中进士,史载他为官时颇为“贪暴”,为人“喜奢好大嗜进谋身”,区区以为或许其人功利事业之心重了,故此有不恤民力之举,而且因为先后投靠贾似道与吴潜,故为掌握历史话语权的某些人不喜。
第一卷、朝为田舍郎 二九四、花开花落两不同
更新时间:2009…7…3 9:49:41 本章字数:5337
“那秦九韶真是如此说的?”
博雅楼,只有赵与莒与胡幽二人对坐着,龙十二站在赵与莒身后,只是在胡幽进来时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招呼,然后就一本正经地公事公办。在龙十二看来,似乎全天下人都有可能对赵与莒构成威胁,都是他要提防的对象。
“确实如此,陛下,此人倒是个趣人,在流求学了三年智学,却非要回来走科举之途。”
这几年赵与莒在选拔官员上有两个渠道,第一个也是最多的还是科举,那些科举出身的仕子,在升官之时仍然如同以往一般优先;第二个便是选择流求学堂毕业的仕子,包括那些去流求进行中短期培训的原来太学诸生,往往被直接任命为各部门的官吏。科举毕竟还要三年一次,流求学堂年年都可以毕业,故此有些士大夫不无嫉妒地称之为“蓬莱近道”,恰与“终南捷径”相对应。
“唔这个秦九韶倒是有几分意思。”
事实上,秦九韶的名字赵与莒并不陌生,在后世他以一个数学家的身份被载入史册,不过他现在手中拥有的精通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