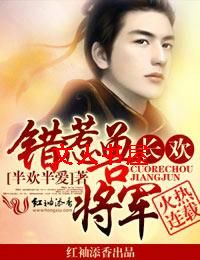中国近卫军-第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羽于是单刀直入:“我这次回来就是跟肖大戎办离婚手续的。”
郦英带搭不理:“这还要看两家是否同意。”
小羽更带搭不理:“我没征得两家同意,就把肖大戎的孩子做掉了。”
直到小羽转身离去,郦英的嘴巴还没合上。
贺小羽决定取消原来的摆平计划。要像中国一样,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决不仰人鼻息。反正孩子在自己肚子里,目前还看不出异样,由他们怎么说去。策略服从目的,离!
杨红刚让护士给夏德厚输上液,麦宝和蒙荷就热汗淋漓地进了病房。
蒙荷举一束鲜花给夏德厚看,说夏大队今天要修改战评材料,下午才能过来,这束花既是他的也是一、二中队全体官兵的心意,祝夏大爷早日康复。那花以红色康乃馨为主,中间高挑一枝鹤望兰,两边斜插了几朵素雅的百合。杨红夸奖说,这花配得好,该不是麦宝的眼光吧。蒙荷说,他那素质是讲实惠的,要买冰糖葫芦和羊肉串呢。实际是,麦宝主张送点实用的,联络小燕在小范围里凑了些钱,买了些时鲜水果。杨红让蒙荷留在夏大伯这里,让麦宝跟她到其他病房看看,昨天陆续送来好几个上访农民,大多是中暑。
昨天杨红带战士们把夏德厚急送到武警医院,经抢救夏德厚很快脱了险。杨红诊断夏德厚是疲劳和焦虑引起的脑痉挛,不碍大事,正好休息几天,做个全面检查。夏若女直到撤除任务才赶过来,对杨红十分感激。他给父亲讲石书记怎么接见上访乡亲,又怎么请乡亲们到礼堂听会,土地补偿金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夏德厚听了唏嘘不已,懊恼自己关键时刻没撑住。
贺东航把贺小羽拽上摩托艇,未等他俩站稳,架艇的小伙子一声唿哨,艇就像箭一般射向湖心。贺小羽朝后猛一趔趄,多亏那小伙子搀扶才没掉下水,她气恼地朝贺东航吼,你要带我到哪儿去?由于马达声音很响,贺东航也使劲喊道,到湖心亭,见个老朋友!
贺东航接到母亲的紧急呼救就安排了这次行动。母亲说可不得了,出大事了,要他赶紧上医院。他以为是父亲出事了,停下一个会议立即赶去,见父母俩满面愁容相对而坐,是被小羽离婚的事搅成这样的,才放了心。
母亲已经和小羽直接冲突。知道小羽堕了胎,对她自然没有好脸色,说话也戗人,小羽能躲就躲,有火只能冲娇娇发。她忽然找不着了政治部开的离婚介绍信。问母亲见了没有,连问三声母亲才说,我怎么会看你那个见不得人的东西!她最终在床底下找到了信的破片,湿漉漉的,闻着有异味,她判断是狗尿,便嚷着追打娇娇。娇娇按预案撤进奶奶怀里。小羽控诉了娇娇的劣迹仍要打,母亲终于忍无可忍:“连只小狗你都团结不好,能团结好男人吗?看自己一朵花,看人家豆腐渣,大戎这样的丈夫你再上哪里找?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到时候哭死吧你!”
………………………………………
《中国近卫军》第二十五章(2)
………………………………………
父亲不解的是,贺小羽不愁吃不愁穿,肖大戎不打人不骂人,双方的父母又都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为什么要离婚?毫无道理!他认定有第三者插足,这样的电视剧打开电视机就是。他多次警告社会,这种戏剧导向不好,没想到居然腐蚀到他的家里。他最无法容忍的是,这丫头竟然背着家里打了胎,把他和肖万夫的这点隔代骨血毫不手软地消灭了!他愤恨地问,这是一般的胎儿吗?这是我和肖万夫同志的后代,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的领导为什么不管?不是说打胎工作有专门机构负责吗?贺东航说,她怀孕了又不说,她自己打掉了谁知道?组织上管的是计划外怀孕。
父亲深感没教育好女儿,做出这种丢人输理的事情无法向肖万夫和易琴交代,嘴上却把责任推给贺小羽的领导,说现在这些干部不知是干什么吃的,自己的下级有了第三者不知道,怀了孕不知道,打了胎不知道,他娘的该知道的都他娘不知道,不知道他娘的知道些什么?他抓起电话要找龙振海,问他武警的政治思想工作究竟是怎么搞的。贺东航忙说这种事情就别惊动龙副司令了,我先了解了解再说。母亲也担心把事情捅大了,搞得小羽无法工作,她现在搞的是中国最伟大的水力工程,还是模范呢。
贺东航决定搞个“2+1”会谈,作为他挽救小羽和安慰父母的实际行动。他给肖大戎打了电话。大戎情绪低落,说小羽电话里都说了。贺东航要他立即回来,三个人一起谈谈,再做做小羽的工作。大戎很感激。
冷云这些天入睡晚,醒来早,睡了跟醒来差不多。跟贺远达的那段事总在脑子里撞来撞去,不知是梦还是在回忆……
本来一进洞房她就惴惴不安,贺远达带有古老民族特色的祭祀活动又搞得她挺害怕。她正在思考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冷不防他从侧面抱住了她。她要挣脱,却听见男人在抽泣。他并没有要推倒她的意思,就依在她的肩上哭,哭声很压抑。她感觉到肩头很快湿透了,就有点慌。不知怎的,她就像平时劝慰伤员一样,用尚能活动的左手拍拍男人的一只胳膊,轻轻说,别哭,有什么话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她趁机抽出身,给他拿了条热毛巾。
他听了劝,顺从地坐在床沿上,开始了令亚敏惊心动魄的叙述……
贺远达说,我今天不敢想他们,他们吃苦比我多。我今天喝酒,吃肉,娶老婆,心里有愧。他们都是在中央苏区当的红军,都参加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也都是从于都桥开始长征的。电话班出发时有14个人,湘江战役牺牲了6个,人员没有补充。
安顺场是大渡河边的一个小镇子,是个过河的渡口,我的家离安顺场不远。1935年5月初,一连几天城里城外都闹哄哄的,传说共产党的队伍要来了,他们都是红头发、绿眼睛,要搞“共产共妻”的。我不怕共,我一没有产,二没有妻,谁知我也倒了霉。我给财主家放的牛走失了一头,那头牛偏偏是财主儿子娶媳妇的定礼。财主很恼,捆上我一顿饱打。我正哭叫的时候,来了几个穿灰衣服、操外地口音的男人,他们夺下财主手里的树条子,放了我。打头的是个瘦高个子,湖南口音,他就是蔡石班长,正带着架线班给团指挥所架电话。那天红军没住下,继续朝安顺场方向急进,蔡班长他们撤了电话线也要走。这时我做出了这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当红军去,因为不走还要接着挨打。蔡班长嫌我小,我从他手里抢过几个后来知道叫线拐子的东西,说我能行。
那一年我13岁。
这是我的第一个战斗集体,红一军团前卫团电话班,加我全班9个人。
起先我还吵吵嚷嚷要下战斗班,没过几天就知道了电话班的任务非同寻常。部队宿营,我们要开通团部到各营的电话,还要试线,排除故障,休息很晚。部队转移,我们在后面撤了线还要赶到前头去。遇有战斗,要立即架设团部到各营指挥所的电话,战斗中还要随时抢修线路,保证指挥畅通。我很快就能单独完成任务,但班长总把我带在身边,给他打下手。我们到团部架电话,团长、政委见了我还开玩笑:这不是蔡石的传令兵嘛!
全班都拿我当宝贝,处处疼着护着。我也惹人喜欢,架线、收线能顶个大人用。班里对拿我当儿子还是当弟弟展开了争论。蔡班长说当然是小弟弟嘛,红军战士亲如兄弟。副班长刘文才说不行,得当儿子,上阵父子兵嘛。他是江西瑞金人,30多岁,老婆孩子都留在中央苏区。他又说这伢子太小,鸡公还没有毛哩,喊你们什么也不要强求一致,你们喊他弟弟,他喊我爹。大伙上去就把他掀翻了,都争着让我喊爹。
刘文才想老婆孩子,连我都能看出来。宿了营,架完线,他躺下就发呆。我问他又想娘了吧?他说刚忘记你又提起来。他晚上搂着我睡,说老子搂儿子。他常对我搞“策反”,让我执行任务跟着他,别给班长当传令兵。那时饿饭是常事,饿得睡不着就数星星。他常说我面相好,是个后福绵绵之人,他看不错的。到全国都变成苏维埃了,要我娶个老婆,不能到老还是童子鸡。我说我不娶。他说,傻崽,娶了老婆你就腾云驾雾做神仙了。你有那一天一定告诉我哟,那时候你就是营长了,营长也不能忘了爹。其他人也跟着起哄:要娶的,要告诉的……
………………………………………
《中国近卫军》第二十五章(3)
………………………………………
今晚我不想说长征多艰苦,战斗多残酷,今后有时间。我只告诉你我们班这八个同志现在在哪里。
在哪里呢?在从泸定桥到六盘山的一万多里路上埋着,他们一个一个都牺牲了。
最先去的叫王玉文,湖南人,他精力过人,能连续几天不睡觉,走路打个盹还能撑半天。他在泸定桥南端架线时,被敌人从对面打来的迫击炮弹击中,埋葬在营盘山一棵松树下面。第二个牺牲的叫老曹,名字忘记了,他是去夹金山的途中,在一个叫化林坪的地方遭敌人阻击牺牲的。徐西林长眠在一座看起来并不高的雪山——沙窝山上,他抢了我的线拐子先上去,我到山顶时见他和几个人围着火堆取暖,叫不应,过去一碰就倒了。我们用雪和冰块埋了他。
出了毛儿盖便进了草地,又倒下我们两个同志。闽西人齐冬生喝了沼泽里的水,水有毒,他喝了就拉肚子,一直拉死。刘文才护着我过草地,我背的三个线拐子被他夺去两个。那天一阵大雨下过,我噗哧一声陷进泥水里,一挣扎,大半个身子陷下去了。我抓住一把草正扑腾,多亏刘文才离我近,把我拽上来,拉着我继续走。还叮嘱我,伢子,陷进潭里千万莫慌,赶快躺倒身子打滚,这是前卫营传授的经验。正说着他就一头栽倒了。他和齐冬生都没有埋,死掉的其他同志也都没有埋,用什么埋?哪里有土!后续部队不用向导,沿着一具具尸体走,就能找到宿营地。
长征最后一场硬仗是攻打天险腊子口,老战士周大光牺牲了,他是在抢修电话线时被流弹击中的。这时是1935年9月中旬,自安顺场参加红军至今刚四个月,全班八个老同志死掉了七个,只剩下班长蔡石了。这期间团里几次为我们补充人员,补充进来的同志也有牺牲,牺牲了再补。
班长一天比一天黑,一天比一天瘦,身上的线拐子一天比一天多。过雪山以前我就发现,他时常用线拐子抵住右肋部,眉头紧皱,头上冒汗珠,经常整夜睡不着,但一有任务总是一马当先。过草地的那三天,每当我饿倒下的时候,蔡石总能找出点食物救急。开始是一小把青稞,以后是几小块肉干,再后来是一小把野韭菜花。虽说都是一点点,但每次都给我夺回了命。
到了哈达铺,部队进行整编,补充给养,我以为大苦大难过去了,谁知蔡石班长没能离开哈达铺。回回出发都是蔡班长叫醒我,这次是我叫他,没叫醒,一摸,人凉透了。以后我想,蔡班长是累死的,饿死的,病死的,他常用线拐子抵住的那个地方叫肝区。你是医生,你该知道……
亚敏终于听完了他憋在心里十几年的话,他积攒了十几年的泪水也终于破闸而出。他无遮无拦地恸哭,直哭得八根白蜡闻声起舞,热泪涟涟。
她那颗19岁的芳心被震撼了。以她当时的年龄,对战争的感受还是虚幻的,多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式的咏叹。对敌人的印象是昆明上空的日本飞机,脑子里的沙场英雄是李广、霍去病、张自忠。而眼前这个已经成为她丈夫的孔武男人,不仅亲历了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而且能一口气说出死在他身边的八个有名有姓的红军战士,仅此一点就使她震颤不已,她的潸潸清泪也无法自抑地融到男人的混浊泪水里。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拥抱了这个男人,说了些连自己也没听懂的宽慰话,那男人的哭声渐断渐续,身子也像哭累了的孩子一样绵软下来。但她很快就发现,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兴奋,就像一个负了伤的战士,刚刚包扎了伤口,聚集了弹药,又跃出堑壕追击残敌一样。她被他搂紧了又推倒,推倒了又搂紧,他的两只手忙乱地但却是目标明确地做着该做的事情,离她很近的两只泪痕未褪的眼里,燃烧着一种吓人的渴望……
那天晚上是酒精浸泡着大悲大喜。贺远达拥着身下的亚敏,又一次折回他的记忆……
他感觉他又在攀登那座看似不高却终年积雪的沙窝山,漫山的白雪向他敞开着,明晃晃的反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奋力向上爬,空气少,透不过气,他用刺刀在雪坡上挖着踏脚孔,一步一喘,一步一停,刮起了好大的风啊,直刮得雪柱倾倒,玉粉飞扬……他感觉他又在跋涉草地,草地一望无际,开满了野韭菜花,绿茸茸的水草全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