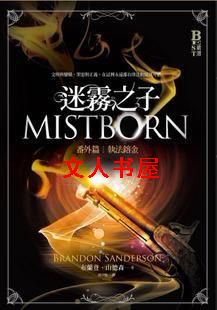林中迷雾-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让我看看。”她说。
她丈夫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但仍然走到窗前,站在她身边。这次,她拉起丈夫的手,紧紧握着。那个留胡须的人已经把轮宋推走了。约克敲敲玻璃。那个人立即站起来。约克让他把轮床推回窗前。那人照办。
我走到离佩雷斯太太更近的地方。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好像有点熟悉,但记不起在哪里闻到过。我站在他们身后大约三十厘米远的地方,从他们的脑袋之间看过去。
约克按下那个白色对讲按钮:“请把他的咯膊给他们看。”
那个留胡须的男人将床单向后拉拉,动作仍然很轻,值得敬佩。伤疤就在那里,是被感染过的刀伤留下的。佩雷斯太太脸上又浮现出笑容,但那是什么样的微笑啊?是痛苦,幸福,迷惑,虚伪,老练,还是自然的笑?我说不出来。
“左边。”她说。
“什么?”
她回头看着我,说:“伤疤在左臂上,吉尔的伤疤在右臂,而且吉尔的没那么长,也没那么深。”
佩雷斯太太还转过身来,把一只手放在我手臂上:“这不是他,科普兰先生。我明白你们为什么希望他是吉尔。何他不是。他不会回到我们身边了。你妹妹也不会。”
06
我回到家时,洛伦·缪斯正像狮子一样踱着步,仿佛附近有一头已经受伤的羚羊。卡拉在汽车后座上。她的舞蹈课再过一小时就开始了。我不会送她去。我们的保姆埃丝特尔今天已经回来了。她会开车送卡拉去上课。我付给埃丝特尔的工钱不低,我也不在乎。你能找到会开车的好保姆吗?她们想要多少薪水,你都会照付。
我把车停进自己的车位。这房子是错层式的,有三个卧室,具备停尸房那条走廊的所有特点。这本来是我们的“起步”房。简曾想过修一栋麦氏豪宅,也许在富兰克林湖。我却不在乎我们在哪里住。我对房子和汽车都不感兴趣,买车修房这样的事情都让简按她自己的意思办。
我怀念妻子。
洛伦·缪斯脸上浮现出一种马上就要吃掉别人的牌的惬意笑容。缪斯当然不玩扑克牌一这点我敢肯定。“我搞到全部账单了,还有电脑记录及其他资料。”然后,她转身看着我的女儿,“嘿,卡拉。”
“洛伦!”卡拉叫着从车上跳下来。卡拉喜欢缪斯。缪斯和孩子很合得来,但她从没结过婚,从没生过孩子。几个星期前,我见到了她最新的男友。那家伙根本配不上她,但这好像也是上了一定年纪的单身女人的普遍现象。
缪斯和我把那些东西全部铺在书房地板上一证人陈述、鹜方报告、电话记录,以及兄弟会的所有账单。我们从那些账单开始査。天哪,可真多。每一个手机拨打的电话,每一瓶订购的啤酒,每一笔线上购物都有记录。
“嗯,”缪斯说,“我们要找什么?”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我还以为你发现什么了呢。”
“只是一种感觉。”
“哎呀,饶了我吧。请别告诉我你只是预感会有好运气。”
“永远不会。”‘我说。
我们继续找。
“这么说来,”她说,“我们查看这些东西的目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在找一个标志:‘大线索在这里’?”
我说:“你是在找一种催化剂。”
“形容得不错。从哪个方面讲?”
“不知道,缪斯。但答案就在这里。我觉得几乎就在眼前。”
“好一一吧。”她故意拖长声音说,好不容易才抑制住自己没有向我翻白眼。
因此,我们继续找。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从Pizza…to…go店点八个外卖比萨饼,直接用信用卡记账。他们还有Netflix,可以经常租DVD电影碟。每次租三张,直接送到门口,好像叫HotFlixxx服务,也可以租色情影碟。他们还订购了有兄弟会会徽的高尔夫衬衫。还有许多高尔夫球,上面也有兄弟会会徽。
我们试着对那些资料进行归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拿起那张只服务账单,递给缪斯看。“租金不贵啊。”我说。
“互联网让人们能很方便地得到色情影碟,因此大众也消费得起了。”
“不错啊。”我说。
“但这可能是个突破口。”缪斯说。
“什么是突破口?”
“年轻小伙,热辣女人。不过,这个案子里只有一个女人。”
“解释一下。”我说。
“我想雇一个兼职人员。”
“谁?”
“一个私家侦探,叫辛格尔·谢克尔。听说过吗?”
我点点头。我听说过这个人。
“那你见过她吗?”她问。
“没见过。”
“但你听说过她?”
“对啊,”我说,“听说过。”
“嗯,毫不夸张地说,辛格尔·谢克尔的块头不仅会阻塞交通,还能堵塞道路,对高速公路中间的隔离带也是威胁。但她这个人很好。如果说有什么人可以让被起诉的兄弟会男孩子们说实话,那非辛格尔莫属。”
“太好啦!”我说。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一我甚至不知道有多少小时一一缪斯站起来:“科普,这里面什么也没有。”
“好像是这样,对吗?”
“你明天上午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讯问夏米克?”
“是。”
她严肃地看着我说:“你最好把时间花在这事上。”
我朝她的方向滑稽地敬了个军礼,好像在说“遵命,长官”。夏米克和我已经讨论过她出庭作证的问题,但可能不够详细。我不想让她表现出老练的样子。我另有计谋。
“我会尽力而为。”缪斯说。
她大步走出房门,好像可以征服世界的样子。
埃丝特尔已经把晚餐做好了^意大利式细面条和肉丸子。她的厨艺不佳,但还凑合。晚饭后,我带卡拉出去吃冰淇淋,作为特别款待。现在,她的话多起来了。我可以在后视镜中看到她被固定在后座上。我小的时候,小孩子是可以坐前排座位的。现在,你必须到可以饮酒的年龄后才能坐前排。
我想听听她在说些什么。但她喋喋不休地说着小孩子们的废话。好像布里塔妮对摩根不礼貌,凯尔便扔橡皮擦去打她;凯莉,不是凯莉·G,是凯利·N——她班上有两个凯莉一休息时间不想去荡秋千,除非基拉也去。我不时去看她那张生机勃勃的脸,有时严肃地板起,好像在模仿大人。我心里产生了那种不可抑制的感觉,而且慢慢溢过全身。做父母的人时不时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你正看着自己的孩子I而且是在那种非常普通的时刻,不是他们在台上表演或者参加什么比赛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那里,你看着他们。你知道,他们就是你生命的全部。那种感觉让你感动,也让你恐慌,很想让时间停止在那一刻。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妹妹,失去了妻子。不久前,我还失去了父亲。在三件事中,我都没被打垮。但当我看着卡拉,看到她大睁着眼睛对着两只小手说话的样子时,我知道,只需再一次打击,我将永远不可能再爬起来。
我想到了父亲。在树林中。拿着那把铁锹。他的心已经碎了。他在找他的女儿。我想到了母亲。她离家出走了。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有时,我还想去找她。但已经想得不那么频繁了。我曾恨过她很多年。也许现在还恨她。或者,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更能理解她经历过的痛苦了。
我们回到家时,电话响了。埃丝特尔把卡拉从我身边带走。我拿起电话说:“哈罗!”
“我们有麻烦了,科普。”
是格蕾塔的丈夫,我的姐夫,鲍勃打来的。他是JaneCare慈善基金会会长。妻子死后,鲍勃和我创立了这个基金会。我曾为此被媒体多次报道过。这是我对可爱、温柔、美丽的妻子的生动纪念,
天哪,我一定曾是个了不起的丈夫。
“出什么事了?”我问。
“你那个强奸案给我们惹出大麻烦了。爱德华·詹雷特的父亲让他的几个朋友退出基金会了。”
我闭上眼睛:“天哪。”
“更糟糕的是,他还四处说我们在盗用基金。F·J·詹雷特是出了名的龟孙子。我已经开始接到电话了。”
“那我们让他们查账吧。”我说,“他们査不出什么的。”
“科普,别傻了。我们正在与其他慈善基金会展开资金募集竞赛。哪怕有一丝丑闻,我们都完蛋了。”
“鲍勃,我们对此没有多大办法。”
“我知道,只是……科普,我们做了那么多好事。”
“我知道。”
“但开支总是很大。”
“你在暗示什么吗?”
“没什么。”鲍勃迟疑了一下。我可以听出他还有话想说。所以就等着。“不过,科普,你们这些人总是可以进行辨析交易,是吗?”
“是的。”
“你们可以不去追究不是那么公正的事情,以便去抓更大的罪犯。”
“必要的时候会这样。”
“这两个男孩子。我听说他们是好孩子。”
“你听错了。”
“你瞧,我不是说他们不该受到惩罚。但为了做更大的善事,有时你必须进行交易。JaneCare基金会的发展势头很好。这可能就是更大的善事。我就说这些。”
“晚安,鲍勃。”
“科普,我无意冒犯你,只想帮忙。”
“我知道。晚安,鲍勃。”
我挂上电话。我的双手在颤抖,那个龟孙子詹雷特没来刁难我,却跑去骚扰我给妻子的纪念品去了。我往楼梯上走,心里怒火直胃。我得把这怒火压下去。我坐到办公桌前。桌上只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女儿卡拉最近在学校照的,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正中。
第二张照片是一张粒面照片,是外公外婆在那个老国家俄罗斯拍的。或者说,当他们死在古拉格集中营时,那个国家还叫苏联。他们去世时,我还很小,我们还住在列宁格勒。但我模糊地记得他们,特别是外公的满头白发。
我经常觉得奇怪:我为什么会把这张照片摆出来?
他们的女儿,也就是我母亲,已经抛弃了我。不是吗?想到这点,你也会觉得奇怪吧。但不知怎么回事,尽管有这些显然纠缠不清的痛苦,
我却发现这张照片奇怪地与我的生活密切相关。我经常看照片,看外公外婆,会想到生活中的波澜和家庭诅咒,想到这一切可能是从哪里开始的。
以前,我桌上摆的是简和卡米尔的照片。我喜欢随时看到她们。她们让我感到安慰。但并不因为我能在死人身上找到安慰,我女儿也能。对一个年仅六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很难找到的平衡。我想谈论她的母亲。我想让她了解简,了解简的精神,知道简可能会多么爱自己的女儿。我也想给她一践安慰,想让她知道她的母亲正在天国看着她。但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倒是想相信。我想相信人有灿烂的来生,想相信妻了、妹妹和父亲都在天国里向我们微笑。但我却无法让自己相信。而且,每当我向女儿说起这些时,就感觉自己好像在向她撒谎。不过,我仍然会说。也许现在她会觉得这就像圣诞老人或复活节兔子一样,是暂时性的、让人安慰的东西,但最终,她会像所有孩子一样,知道这是父母向他们撒的另一个无伤大雅的谎。或者,也许我错了,他们真的在天国看着我们也未可知。也许,卡拉某一天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夜半时分,我终于让自己的心去了它想去的地方一去找妹妹卡米尔、吉尔·佩雷斯,回到那个可怕的神秘夏天。营地的画面闪回脑中。我想到了卡米尔,想到了那个夜晚。几年来,我第一次让自己想到了露西。
我脸上浮现出一个痛苦的微笑。露西·西尔弗斯坦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女朋友。在那个夜晚之前,我们那段夏日浪漫史像童话故事一般,美妙极了。我们从来没得到过分手的机会。相反,我们俩是被血腥的谋杀案活生生地撕裂开的。在我们仍然紧紧缠住对方,在我们的爱一尽管那么愚蠢,那么不成熟——还在升温,还在高涨的时候,我们就被撕裂开了。
露西巳经成为过去。我已经给自己下了最后通牒,将她永远排除在我的生活之外。但人的心是不懂得什么最后通牒的。多年来,我一直想知道露西在做什么,还在Google上捜索过她的名字,想知道她的近况。不过,我怀疑自己永远不会有勇气联系她。可惜,我什么收获也没有。我猜,发生那些事情之后,她可能已经明智地改名换姓。露西现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