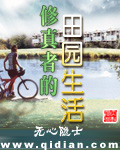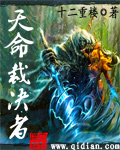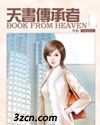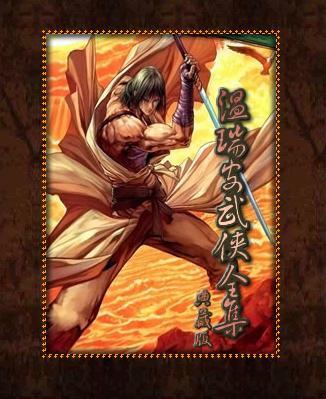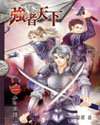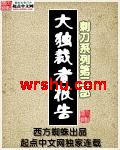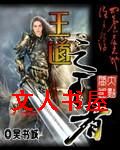奠基者-第7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说过,连他最亲近的人有的也不知道。
“还有余秋里”的意义很深刻吧?就论这一点,毛泽东仍然同样功不可没。因为是他在关键时刻说了这样的话。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的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转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38页)
历朝历代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但毛泽东作为一代旷世大政治家,他即便在做错事时,也还留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巴”。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有今天,这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没有彻底地断“尾巴”有关。“还有余秋里”是一例,邓小平的命运更属此举。当然,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革”运动,中国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局面。但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难免犯错误。毛泽东也是人,而不是神。
历史之所以让人回味和令人读后充满着惊心动魄,那便是因为它不平庸枯燥、不死水一潭。我们都愿望能够有永远的莺歌燕舞、一路春光的美好时代,可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责备先人的缺陷与遗憾时,其实自己已经在犯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缺陷与遗憾了。
新中国的“三五计划”始于将军之手,却毁于“文革”之中,但因周恩来、李先念和将军、谷牧等领导人的苦苦支撑,除了1967、1968年全国性的混乱实在无法维持外,其余年份生产形势尚有发展。1969年,国民经济出现扭转下滑的局面,工农业总产值为261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8郾1%。1970年形势更好一些,比1969年增长20郾1%。“三五”期间安排的三线建设和其他重点项目,也有些突出表现。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9年宝成铁路广元到马角坝段电气化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营;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同年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上马兴建……将军曾经感叹:如果没有“文革”破坏,“三五”将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国家的经济面貌将是十分可观的。
但感叹挽救不了历史,有罪的是林彪、“四人帮”,有错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将军和总理他们已经尽力了。
我记得将军的后任秘书雷厉同志给我讲起一个情节:那是“文革”最乱的一个时期的1968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好不容易召来的各省市区军管会代表及群众组织代表,本来是讨论年度计划的,结果代表们吵吵嚷嚷的还是大批判内容。会议开到12月25日晚,周恩来接见会议代表,将军也参加了。周恩来原准备通过这次接见,想把全国的计划盘子大体定下,可他的话正题还未提及,一些代表又吵嚷起来,互不相让。直闹到26日凌晨也没个结果。周恩来朝将军痛苦地摇摇头,然后站起来对代表们说:今天是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我指挥大家唱个《大海航行靠舵手》,再请大家吃顿寿面。吃完后上午大家就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吵得精疲力竭的代表们这回才叫好。计划会议就这样毫无结果地散会了。将军无精打采地刚踏进家门已经凌晨两点多了,红头电话铃突然响起。“总理?!是我啊!马上到你那儿去?好。我马上到。”周总理让将军立即赶到中南海。将军走进西花厅,总理身体斜仰在沙发上,疲倦不堪地连连长叹一阵后对将军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都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个计划怎么成嘛?这几亿人口的大国……将军的内心何尝不是这般焦虑?“总理,我马上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周恩来深情地点点头:拜托了。将军当即赶回办公室,拼命摇响电话,叫来几个信得过的同志,不分日夜地加班加点提出了一个临时方案交给总理,总理随即报毛泽东审批并获通过。
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新年第一天就是这样开的门……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第十章
十月又来临,秋里景正好!
几个“跳梁小丑”被抓,将军听后“哈哈”大笑:今天我就上班!
开拓进取,那些得罪人的事也非做不可。
公心在天,昭然若揭。
中华大地上留下一个永不消失的国魂、军魂、石油魂……
这个秋里好景象。
那一天是10月7日。住在西山的将军,突然接到李先念的电话:那几个“跳梁小丑”给抓起来啦!
“抓起来啦?!”将军万分意外,但又立即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忍不住在电话里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这样的笑声已经多年没有了。
“秋里,你的病怎么样了?能上班吗?”李先念问。
“好了。今天就可以上班!”将军豪气冲天。
真是太值得高兴了。将军当天跑到301医院——这一年将军因受“四人帮”的迫害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相继去世的打击,身心极度不佳,已有几个月住在解放军总医院,有时则回西山疗养。当从李先念那儿得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后,兴奋得直奔301医院办出院手续。
“我看到爸那天在走廊里,把拐棍一甩,嚎着嗓门,喊着:‘找你们院长来,我要出院!’”女儿晓霞这样说。
随即将军回到家,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将夫人叫到内屋,然后关上门。一会儿,又匆匆出来,夹着皮包就往外走,那脸上挂满了抑掩不住的喜气,步子也变得轻盈无比。
儿女们追不上爸爸,也知道他是家里有名的“保密专家”。于是缠着母亲让她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回母亲向孩子透露了“机密”:那几个坏蛋给抓起来啦!
“好——”儿女们顿时欢呼起来。儿子个高,一蹦头撞在了木梁上,可他一点不感到疼,心里甜水如潮。因为他们都知道“坏蛋”指的是谁。
关于1970年后的将军情况,我缩写了,是因为这段时间“四人帮”横行,将军只能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与谷牧、纪登奎等人苦苦地支撑着国家生产和经济的那只破漏的船在风雨中飘摇。虽然有一阵子邓小平重新出山使他看到了希望,但很快“四人帮”又借“右倾翻案风”把更大的灾难嫁祸给了苦难深重的共和国。
粉碎“四人帮”,使一心想把国家经济搞上去的将军欣喜若狂。多年积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病也随即一挥而去,他要工作,要像当年大庆会战那样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
将军这一年62岁。而这个年龄已经不再可能像毛泽东当年点将他上石油部当部长时那样朝气蓬勃,也不可能像毛泽东第二次点将让他上“小计委”那样年富力强。但听得妖孽一除,将军仿佛又一下恢复了当年那个精神头。在这之前的一年多,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从1970年至1976年秋,将军虽然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可经历的风风雨雨仍然不计其数。这中间有欣慰的事:比如他主持了自与苏联断绝合作关系后的第一批引进项目,这些项目对日后邓小平全面启动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基础作用;比如恢复和组织了外贸出口工作;等等。也经历了电影《创业》风波等政治事件。然而纵观这几年,将军总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和政治上喘不过气的痛苦。这种压抑和痛苦,使素有“猛打猛冲”、喜欢干惊天动地事业的将军身心备受创伤。
现在好了,“四人帮”垮台,将军顿感昔日雄风重振,大有愿望再领导一回大庆会战那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战役。1977年的党的十一大上,将军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次年春天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推荐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之职。两年后的1980年中央在设立书记处书记时,将军又任书记处书记。这样的职务,对老百姓来说,是登上天的大官了。事实上,将军也确实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党和国家核心领导层的政治生涯。
但将军就是将军,与其让他天天坐在办公室开会和在文件上画圈,还不如去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大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这是他的性格:见不着老百姓,他心里不踏实;不是挑战性的工作,他总感不过瘾。
将军这么大的官了,可他还是用着一辆公务车,而且一直是老司机贾师傅开着。现在不少地方上“七品”芝麻官出行都是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的。将军这么大的官则不,他平时出行从不要这种“气派”。专用“座车”既是警卫车又是工作车,需要时车上坐四个人:将军自己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参谋一个,外加开车的贾师傅。不需要时,就将军和贾师傅俩人。贾师傅虽比将军小一二十岁,但他们像是“老哥儿俩”,车子内的方尺小天地里无话不说——当然除机密外。将军平时一有空就喜欢出去跟老百姓聊天、上基层单位调查私访。开始贾师傅劝他说你年岁大了,别那么累,有空也休息休息。将军立马板着脸:“共产党员,哪有什么休息?”贾师傅再也不敢阻拦了。两个“老头”单独出行总是有些不安全吧?将军又嘴一撇,说:“我做事对得起老百姓,给他们办事,老百姓怎么会害我呢?”将军的为人哲学非常朴素,但里面却折射着很深刻的道理。现今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执政为民”,不也是这个道理嘛!
将军官大了,但小事上依然不含糊。他最恨那些官当得不大,却大事小事都把手伸得特长。他不,就连抽烟这样的细节也都十分注意:他烟瘾大,一天都在两三包水平上。口袋里又总不能塞得鼓鼓囊囊的,可是经常一开会就是半天,他的烟就会“断档”。这时将军就会抬头朝坐在某个旮旯里的贾师傅使个眼神,贾师傅马上悄悄走过去塞上一两包烟——俩人有默契,因为将军有一条自律:不抽公家的“招待烟”。
李先念曾有话评价将军:粗中有细,一心为公。
“为公”两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易事,而要一心为公,怕是难上难。有人可以一时为公,却难能做到一辈子为公;有人可以在某些容易做到的事上为公,却不能在所有事情上特别是涉及到错综复杂、尤其影响到自己切身利益和个人形象时就再也做不到了。
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也常有衡量他为人处世的品质问题。
将军在任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时就奉命做过两件“得罪人”的事——而这又是必须有人去做的影响国家和军队改革的大事。
一件事是80年代初国务院所属的工业部门的机构改革。
积五六十年代中国计划经济时机构庞杂的惯性和“文革”十余年留下的干部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机构的臃肿和人浮于事的现象极其突出,政府部长级干部中“一多二老三不专”的情况非常严重。一多,即有的部正副部长多达20人,少的也有十几人。一份文件传阅、画圈有时一个月还没有转过来;二老,即正副部长年龄都在六七十岁左右,部长会一开起来围了一大会议室,真正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却并没有几个人。三不专,即文化水平普遍低,大部分部长只有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对专业知识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更加缺乏。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把精简机构的意义提高到“一场革命”的高度。他说:“精简这个事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的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
机构改革的这场“革命”,革的大部分都是为建立新中国和在新中国建设中立过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他们大多又是在“文革”中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多年失去工作机会的老干部。“四人帮”垮台,他们才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可现在精简机构又要他们退位。许多人想不通,抵触情绪自然非同一般。谁去做这得罪人的事?一些“聪明人”躲到一边去了,将军没有躲,并主动承担了他分管的那些部委的精简任务。
难哪!既然精简,就得有硬性的“杠杠”:年龄杠杠、编制人数杠杠,这都是要了那些想留任的老同志的“命”。
将军为此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跑;一个人、一个人地找谈话;谈了部长,谈副部长,谈了留任的再谈退位的;谈了正副部长,再谈司局长……谈得通的可以过关,